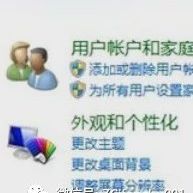星期五责任编辑刘君电话:(0531)85193407Email:liujun@
丰收
15
知食分子
□李海燕
我打江南走过,六月的江南细雨迷蒙,跫音不响。
夜晚,栀子花的香气从雨雾中荡上来,像一壶陈年的花雕,人倒成了爱甜的小飞虫儿,一下子跌在那黏稠的淡金色的香气里,半晌爬不出来。
花开时节,人是否格外多情?连开出租车的粗线条大叔也把两朵白兰细线穿了挂在后视镜上,香气就那么一悠一悠地仿佛坐在秋千上。
这样的江南,大概适合定格在画里,装饰在梦里。
可是因为有杨梅,六月的江南,到底最适合“夜深一口嚼红霞”,在唇齿之间酸酸甜甜地记取。
我与杨梅的初见,自然是在北方的超市里,装了盒薄膜封着。
当时只觉深紫的颜色,和因为没有果皮需轻拿轻放的果子让人惊奇,入口,却是酸涩为主,尝了一两个就有了结论———太不好吃了。
直到十多年前在杭州,梅雨时节再逢君,才有机会见识杨梅的本来面目。
那次采访的间隙,杭州的同行们带我领略本地人才晓得的美食。
一天晚饭后,一群人在 故园无此味 著名的青藤茶馆坐下。
茶未起,先上些时令鲜果,一盘托在白瓷素碟里的杨梅施施然摆在桌上。
我下意识皱了一下眉,酸涩的记忆涌起,都能感觉到口中唾液分泌了。
同行的人忙让:“快尝尝。
”我心下迟疑,又觉不便拂了主人美意,问道:“酸吧?
”主人但笑:“尝一个嘛。
”一颗入口,意外到不能自持:满口清甜,果肉虽然是浆果的软,又有明显的颗粒感和韧性。
也不是一味地甜,清香和微酸不时从甜里若隐若现地浮出来,像“和羞走、倚门回首”的神秘少女,你一颗又一颗地入口,只想把那惊艳的感觉留住。
说起在北方吃到的杨梅,主人笑说,杨梅很娇贵,有“一日味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的说法。
杨梅熟透了根本无法保存,更别说运输了。
你吃的杨梅一定是半生摘下来,喷上保鲜剂,到了再催熟,哎呀,吃不得的。
那日我的表现毫无淑女风范,一盘杨梅几乎被我一个人吃掉,再上的我实在无力再战,其他人才吃到了。
第二天早饭时才惊觉,一口牙都打了软腿儿,嚼面食都觉无力。
原来那隐在甜中的一点微酸,竟 是这样蚀骨铭心。
其实杨梅的盛名,早在我了解它之 前。
南北朝人江淹是有记录的将杨梅入诗 的第一人,他的四言诗《杨梅颂》称赞“珍过荔枝,香超木兰”,并将杨梅的色、香、 味、形及生长环境、装盘品尝写得极为形象而优美。
宋朝人对杨梅是真爱,陆游、杨万里都有赞杨梅的诗。
诗人平可正更直言,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
味比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
最有意思的还是苏东坡,先是大赞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后来却又认为:“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这一评价,出自这位美食家之口,吴越杨梅自然就身价百倍了,故有“吴越杨梅冠天下”之誉。
明人徐玠更写了两句特别逗的诗: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
听上去是为杨梅拈酸,其实各美其美,杨梅大概不在乎荔枝到不到长安。
古人吃杨梅已经很讲究了。
杨梅因有微酸,古人食用时常常会加少许食盐浸渍片刻,一可杀菌,二则减少酸味。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梁园吟》,玉盘杨梅 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玉盘杨梅的搭配,美不胜收。
明末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写过杨梅的另一种包装方式———漆盘。
“杨梅,吴中佳果,与荔枝并擅高名,各不相上下。
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盘盛之,色与漆等……”盛放杨梅的包装盒是上等的漆盘,颜色与杨梅一样紫乌发亮,想想也是赏心悦目。
不过在我心里,始终不及白玉、白瓷的素盘,更衬杨梅的“玉肌半醉红生粟,墨晕微深染紫裳”。
因为杨梅不耐储存,江南人习惯把上等的杨梅浸泡在优质白酒中制成杨梅酒。
杨梅酒色艳如石榴汁,可媲美粉红香槟,更妙可养阴益气,清热除湿,梅雨天气的一盏杨梅酒,任何形容词都太苍白了。
此番沪上之行,比记忆中梅子成熟的时节稍早,未料到有杨梅吃的。
晚间与同行诸友行散,说到杨梅,又一阵齿颊间唾液疯狂地分泌,却是馋得了。
及至杨梅终于入口,记忆的苏醒与加深,倒让人惆怅了。
江南,我们终究是过客,诗人说“满口酸甜不思归”,我心里却明白他的意思:奈何,故园无此味。
也由人事也由“天” □傅绍万 手头有一本小册子,是某某大师的大预言精选。
自然界如汶川、玉树地震,人世间如东西方政要上台下台,其早有预言。
其言之凿凿,我却怎么也信不起来。
人、事早由天定,还能早看明白,人还有什么必要去奋斗、去忙碌呢? 中国是一个占卜的古国,方士辈出、术数繁荣。
《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七略《术数略》,列出了六种术数,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也就是看相术和风水术。
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术数时起时落。
至今日,涂上了科学的色彩,又大行其道。
如今的术数虽新,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传统文化”有了新包装。
那么,我们还是看看古人是怎么对待的吧。
中国商朝时的占卜法是烧灼甲骨,根据这些甲骨的裂纹,断定所问事情的吉凶。
到了西周,又辅之另一种方法,就是揲蓍草的茎,形成各种组合,产生偶数、奇数。
这些组合的数目有限,可以用固定的公式解释。
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阳爻、阴爻,就是这些组合的图像。
占卜者用这种揲蓍的方法,得出各爻,然后对照《易经》,读出它的卦辞爻辞,断定所卜的吉凶。
殷商时期,周要起兵讨伐殷,出现了许多吉兆,如苍鹰群飞,白鱼入于王舟。
殷以白为尊,预示殷要被周所俘获,所以更感觉大吉大利。
但周军分析形势,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兵。
一年后,准备正式发兵,但占卜得到的却是大凶兆。
怎么办?这时,姜太公丢掉蓍草,把龟壳踩到地上,说:枯骨死草,焉知吉凶!大兵进发,摧枯拉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同一种现象,不同的解释,可以得出吉和凶完全不同的结论。
明朝有个和尚道衍,是帮助朱棣造反夺天下的第一智囊。
他的师傅也是个世外高人。
洪武十五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朱元璋的马皇后入葬,突然下起大雨,葬礼无法举行。
朱元璋十分恼火,相关官员难辞其咎。
龙颜大怒,一些人就得人头落地。
这时候,道衍的师傅高僧宗泐上前说了四句偈语: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 哀。
西方诸佛子,齐送马如来。
朱元璋转怒为喜。
名师出高徒,道衍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不凡。
建文元年七月六日夜,朱棣举行誓师大会,正式举起造反的大旗,突然起了狂风暴雨,刮得房瓦掉地,这太不吉利,人人大惊失色。
这时候,道衍和尚站了出来,说道: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落,这预示大王要换黄瓦了,也就是要做皇帝了。
一句话,使士气大振。
大智大慧之人,凡占凡卜,总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化凶为吉。
那些愚昧迷信之人,做事就荒唐了。
1841年,中英虎门之战,出了一出闹剧。
清朝大将杨芳,在前线观察敌情,发现敌人的舰艇在运动中射击,百发百中。
他惊讶异常,认为敌人用了魔法。
回去备战,他让士兵到处搜集臭粪桶,因为迷信说法,秽物可以破魔法。
第二天,双方开战,他先让士兵用木船往敌舰上扔粪桶。
法国人先是迷惑不解,继之一片哄笑声。
清军自然大败。
这杨芳可不是草包,是久经战阵的猛将,可惜太不了解西方科技,闹出如此笑话。
悲哉大清! 我们的孔圣人,对待占卜、命运,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做法。
孔子一生都在推行自己的道,为此而周游列国,但是,他的道却很难为统治者所接受。
孔子就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他尽了一切努力,又归之于命。
他说的“命”,是告诉我们,人的活动要取得成功,总需要宇宙间的条件和力量相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应该做的事,而不计较成败。
这样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面对如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大师,面对神仙、神算对我们未来命运的预卜,面对那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异兆,应当怎么对待,历史和智者告诉我们的,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读史札记 心灵小品 绿眼睛 □雨兰 那时,我经常想象,她就是小村里的一只绿色的大眼睛。
我经常去看看她。
当我看着她时,她也用绿色的大眼睛看我,看得我的心清澈起来。
她的绿眼睛那么美,那么安静,而我的小小身影,也在她的绿眼睛里轻轻荡漾。
更多的时候,她的绿眼睛是在望着天空。
天空也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眼睛深处,蓝蓝的,很遥远,也很神秘。
她的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她是不是要记着云朵在蓝天上的悠闲漫步,有多少次走远了,有多少次又悄悄走回来;她是不是要记着飞来飞去的燕子,有多少次在她的眼前欢快地飞舞,优雅地展翅,羽衣闪亮;她是不是要记下岸边俏立的垂柳,一天里有多少次临水照影慢梳妆;甚至,记着悄悄跑来喝水的小田鼠,掠过水面的蜻蜓……也许,她什么都记不住,什么也不想记住。
她只是任凭那些天上的云朵、俏丽的燕子、娇小的麻雀……来的轻轻来了,走的轻轻走了,无牵无挂,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是的,她不像我那么敏感,那么小气,我会在心里默默记下生命里的暖与疼,记下一天里的笑与泪,记下妈妈的盈盈笑脸,爸爸的严肃目光,祖母的絮叨。
她只是安安然然地睁着眼睛,微风吹过时,她的大眼睛就绿波荡漾起来,就笑纹细密起来,这时,她看我的眼神就朦胧起来,就波动起来。
下着小雨的时候,我也偷偷地去看她。
一滴一滴的雨点儿排着长队,飞向她的大眼睛,她都微笑着接纳,笑纹儿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数也数不清。
晴朗的下午,倾斜的阳光照到她的时候,她清凉的眸子里,就开始盛着金色的光芒了,美得让人惊艳,美得让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喜欢静静地看着她,村里有些皮小子经常拿小石子,在她平静的水面上打水漂。
这是不是经常要吓她一跳呢,但她只是眨巴眨巴眼睛:嗨,那些小伎俩,我见得多了呢。
她在小村的南面,称它为湖,实在是,唉,实在是她太小了,她只是一个人工挖的池塘。
如今,她安静地泊在我的记忆深处,也泊在我的心底。
我轻易不去惊扰她,我也不会舍得惊扰她。
强词有理 □韩浩月 假期时,去野外闲走,路过一片麦地,快到丰收的时候,麦穗沉重,风中微微晃动,麦地深处有虫鸣鸟叫,麦地远处有农人吆喝的声音,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小视频,收录眼见耳听的这一切,发了朋友圈。
瞬间点赞者众,评论者纷纷,一条不过十秒钟的麦子小视频,震惊了朋友圈。
有人立刻发来消息,索要高清原图,换成了自己的头像,有人则拿去当了朋友圈封面;有人则询问麦地在哪里,打算亲往拜访;有人可能是故意开玩笑,问这是麦子还是水稻?这个问题把我气笑了。
城里人五谷不分,遇到有关庄稼的事大惊小怪,并不为过。
说真的,就算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这样的图片或视频,也会忍不住点开看看,然后点个赞,留个言,评个论。
朋友圈里天天高大上,多是咖啡馆里谈的内容,立项啊、开机啊、首轮啊、上市啊等等,偶尔有麦子出现,大家难免围观看个稀奇。
我留恋麦子、晒麦子的影像,并非是在这移动互联网时代,卖弄什么农耕时代的浪漫。
实则相反,看到麦地最先想到的是烈日下割麦子的痛苦,麦芒穿过裤腿衣袖亲吻皮肤的刺痛。
现在和过去的麦子 麦子从麦地到麦仓,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割麦子是先要闯过的第一道关。
熟透的麦子需要第一时间割下来,否则有“熟掉头”的风险———沉甸甸的麦穗等不到收割它的农人,径直地掉进了田里,成为野外鸟类的食品了。
割麦子需要穿上长裤,裤子最好是厚一点的,还要带上套袖,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阻止麦芒。
但就算全副武装,割完麦子晚上回家洗澡的时候,全身都还依稀可见被麦芒刺出的红点。
一整天麦子割下来,腰酸背痛。
把麦子运出田地后,下一个去处是打麦场。
童年的打麦场,是爷爷赶着牛拉的石碾,缓慢地在场上转动,一圈又一圈,直到把麦子全部碾出来,那是一个人的劳动,不太用别人怎么帮忙。
后来为了提高效率,普遍开始使用脱粒机,约两米长的脱粒机后面站着三四个人,把麦捆打开,分成一小把一小把地塞进去,麦粒和麦秸便会被机器分开,脱出的麦粒直接进了装粮食的口袋。
脱粒的时候要分外小心,不小心的话手臂很有可能被卷进机器,丢掉一只手或一只胳膊。
我在脱粒的时候不担心手臂的安全,因为我始终保持着敏捷的本性,不会与机器较劲。
最为揪心的是打麦场四处飞扬的灰尘,简陋的口罩根本阻挡不住肮 脏的空气进入鼻孔,混杂了各种奇怪物质的麦场空气通过呼吸道进入肺管,要咳嗽好多天才能彻底清理掉。
装进袋子的麦子,要在麦场被清理干净之后晾晒,通常需要晾晒三五天的时间。
夏天的骄阳在加快麦子的成熟度,把最后一丝水分从麦子的身体里驱赶出来。
下午到傍晚的那段时间,是一天当中起风的时候,也是到了扬场的时候,扬场的人用一把大大的木锨,把麦子高高抛向天空,抛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麦子在空中飞扬,掺进粮食的碎麦秸等等会随风飘走,只留下干净的麦子。
我喜欢这个场景,常呆在麦场边看扬麦子很长时间,这是整个麦子收获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意味着残酷的劳动彻底结束,是尽可以享受丰收喜悦的时刻。
喜欢麦子装进粮仓时的那种踏实感,但确实不爱割麦子。
我上班能挣工资之后,就再也没下过麦地。
每年麦收季节都是花钱雇用收割机。
轰鸣的收割机,咆哮着闯进麦地,几个来回就把几亩地麦子收光了,比以前能节约很长时间,劳动强度自然也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真是太好了。
为了逃避一辈子割麦子,我跑得远远的,一跑就是二三十年。
可如同哲人所说,幸福的感受总是短暂且易忘,唯有苦痛能在生命里留下深刻的痕迹。
如今我用手掌 抚摸麦田,已经没有了如芒在背的不适感,取而代之的是无法形容的愉悦。
时间果然有美化过往的功能。
我想,朋友圈里那些为麦地和麦子点赞的朋友,也想当然地联想到了许多美好的景象。
比如他们的隐居梦、农耕梦、田园梦。
可是他们(包括我自己)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
甚至连梦都算不上,顶多算个臆想。
要是真这么热爱粮食、庄稼与土地,从北京三环任一方向开出个十几二十公里,都能找到各种时兴的瓜果蔬菜、玉米小麦。
可很少有人这么做———找一块农田,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在地头呆上几个小时。
无论从文学层面还是从生活层面,“麦子”都是一个重要的意象。
中学时候写诗,最爱的组合就是把“麦子”与“黄金”组合在一起,根本不管它风马牛不相及。
搓几粒还未成熟的麦粒放在口中,嚼几口之后口腔便充满清香,这才是土地和风的结合催生出的粮食清香,这才是生活的滋味。
我的朋友们,希望你能抽个空在夏天寻一块麦田,搓几粒麦粒尝尝,或能唤醒你那百毒不侵的味蕾,体会一下舌尖上的乡愁。
哪怕拍个图发个朋友圈转身就走呢,那也是好的。
城市生活太单调无味没有想象力了,需要点泥土的气息。
坊间纪事 少的胜利 □董改正 一家特味店新出一种“秘制”熟食,店堂大屏幕上隆重地做着广告,说武则天渐感容颜衰老,派人到民间四处搜罗养颜高手,但这些人所用材料也无非枸杞、何首乌、燕窝之属,既无创意,口感也差,女皇恼怒之余,除了一位的“作品”因为验证还需时日外,其余的通通逐出宫去。
留下来的这位,烹制的是秘制猪手。
此味以流水浸三天,洗七七四十九遍,再用当归、藏红花、葛根、甘草等二十多种中草药熬制了九个时辰。
食用当日便有效用,一个月后,可以生肌活肤,犹春风化雨。
一辈子食用,可以永葆青春。
女皇用后不到一月,便肤白如处子,肤下隐隐晶莹有光。
女皇大喜,这道菜便成为了皇家秘制。
千百年后,出现我的眼前,与有荣焉。
这个故事所要强调的是那二十多味中草药,尤其是“二十多味”。
当我们要表示一种地位时,习惯的思维就是用数词,数词后面加量词,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优势。
大到一个国家的介绍,小到一个人的名片,微到一本书的推介人数,都用数量来展示,数量是硬性指标,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
所以我们习惯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堆积这些“数量”,以抬高人生的高度,拓宽人生的维度。
参加各类考证以积累证书,参加各个协会以累积头衔,参加各种比赛以积攒奖牌,拍摄各地照片以酷炫游历等等,这种加法且不说是否有益于人生,其间必是焦虑和负累,生活的乐趣定然少了很多。
我看过许多选秀节目,选手在展示才艺时,往往令评委瞠目结舌:他们会的太多了。
我们在培养孩子或自修时,都喜欢往“多”的上面发展,所谓“技多不压身”。
当所有的人都奔“多”而来时,那就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了。
这让我想起张学友来,当时他才出道时,不但不会舞蹈、乐器之类,甚至连乐谱也 不认识,但是他有一点:专爱唱歌,痴迷唱歌,一心一意地唱歌。
会很多才艺的人有很多,但张学友只有一个。
“多”与“少”孰优孰劣?答案是辩证的。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多”,便往往会陷入了泛泛。
你可能会认为会的越多,选择的机会越多,但是却忘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比的往往不是会多少,而是在某一个领域,你是不是高手;而别的领域,自有别人去做,社会自有分工,用不着你一个人包揽。
用人者缺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如果一万个都会舞蹈、乐器、英语,而用人单位需要的只是一个会藏语的,那么“一万”和“一”是相同的。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控力,“多”很难让人静心定性,很难专注,而不专注是很难成就事业的。
所以,做切合自己天赋的减法是必须的,就像一棵白杨树,它的天赋是笔直向上的刚性,而不是旁逸斜出的婆娑,那么就必须剪枝,以促其向上。
一个足球运动员,他需要掌控球场的技术,而会不会弹吉他并不重要,是不是某个协会的理事更不重要。
直到剪得生命的枝条疏朗时,可以看到星空时,心里才不会焦灼,才能深呼吸,专注于一件事,只要选择正确,鲜有不成的。
脱颖而出中“颖”指的就是“尖子”,尖是以“小”和“少”而突出的。
诗作为文学的冠冕,是以少胜多的艺术,她的意义在于以有限达无穷,以平淡而致深味,以一瞬而通恒久。
卞之琳的《断章》、庞德的《在地铁站》,皆是如此。
诗意人生也当如此,能有一种深到骨髓的幸福,有一份爱着享受着的工作,有一个情趣相投的爱人,有一两个可爱健康的孩子,有一群谈心喝酒的朋友,不就够了吗?就像祖咏到长安应试,规定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他写了四句,就“纳于有司”了。
有人惊讶,他回答说“意尽”。
好一个意尽啊! 时尚辞典 垂杨风影 □张期鹏 一个地方,倘能让人记住,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
或风景,或人物,或永难湮灭的遗迹,或流传久远的故事……这些,都会构成许许多多非同一般的传奇。
垂杨,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在陌生人眼里,它又实在太普通不过了:一个小村,百多户人家,都是平凡的民居和平常的街巷。
它就那么静静地居于莱芜北部新城的一隅,好像村东河边随处生长的垂柳一样,默默地面对大地长空,悄然迎接着一年四季。
只有清风拂来、鸟雀飞来的时候,它才微微摆动长发,似乎透露出了一点深不可测的秘密。
如若时光倒流两千多年,我们穿越无数的历史烟云,深情回望中华大地上那个诞生了诸多思想巨人和伟大思想的时代,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神奇和不凡。
这是孔子曾经到过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孔子当年求学问礼的一个生动课堂。
史载,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回国途中其长子病死。
因路途遥远难以归葬,只好沿途择地葬焉。
当时尚且年轻的孔丘听说后,即不辞辛苦跋涉数百里前来观看、学习吴国葬礼,并且留下了“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的感叹。
只可惜,这段夫子重礼践学的佳话,因岁月漫漫,遗迹不存,后人只能怅惘空怀了。
直到明代隆庆四年(1570),江西临川人傅国璧任莱芜县令,深为孔子观礼之事湮没无考可惜,于是费心搜集古籍旧志记载,四处请教有学问有研究的长者,最终查明当年孔子观礼之处即在垂杨一带。
为彰明先贤圣迹,续延莱芜文脉,他又在此地构房筑屋,建成了莱芜历史上著名的“垂杨书院”(亦称“观礼书院”)。
同时,树“孔子观礼处”碑、作《观礼书院记》以为纪念。
傅国璧在《观礼书院记》中说,书院建成之后,远近学子纷纷而来,“争欲从观礼处诵习圣贤之书,以助化成天下之志”,可谓学风文气盛极一时。
如今,四百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那方历尽风雨剥蚀和某些时代文化戕害的石碑仍在,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古韵悠悠、文风徐徐。
它让人们回首历史,神往先贤;让人们似乎看到了灵魂的源头,思想的来处。
它像细细抚过柳枝的轻风一样,从远古吹来,向未来拂去,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据说,“孔子观礼处”碑的对面,就是当年“垂杨书院”的旧址。
虽然原有的建筑几经岁月轮回,早已风流不在,但站在遗址门前,思绪依然牵扯不住地往前、往前、再往前延伸,耳边仿佛回旋起古老悠远的弦歌之声,空气中也缭绕着似浓似淡、若有若无的书香、纸香和墨香。
这一切与垂杨的风影交织、融合在一起,浸润了莱芜的山川草木,让这方土地慢慢变得宽厚、博大、深邃起来了。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明清两朝从莱芜大地上走出的近三十位进士的身影。
他们或政绩卓著,或文采斐然;或为国捐躯,或执教乡里,成为莱芜数百年间的光荣和骄傲。
历史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在“垂杨书院”建成之前,莱芜进士仅有一人而已。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堪称“莱芜现代三贤”的著名散文家吴伯箫、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著名诗人吕剑的身影。
他们都用自己的出众才华,让莱芜不“芜”成为现实。
文脉千年,就像插入泥土的柳枝一样,扎根于大地,不断地分生,旺盛地生长。
垂杨小村,就那么静静地坐落在那里;“孔子观礼处”石碑,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但这方土地上的杨柳,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风姿。
夜晚,栀子花的香气从雨雾中荡上来,像一壶陈年的花雕,人倒成了爱甜的小飞虫儿,一下子跌在那黏稠的淡金色的香气里,半晌爬不出来。
花开时节,人是否格外多情?连开出租车的粗线条大叔也把两朵白兰细线穿了挂在后视镜上,香气就那么一悠一悠地仿佛坐在秋千上。
这样的江南,大概适合定格在画里,装饰在梦里。
可是因为有杨梅,六月的江南,到底最适合“夜深一口嚼红霞”,在唇齿之间酸酸甜甜地记取。
我与杨梅的初见,自然是在北方的超市里,装了盒薄膜封着。
当时只觉深紫的颜色,和因为没有果皮需轻拿轻放的果子让人惊奇,入口,却是酸涩为主,尝了一两个就有了结论———太不好吃了。
直到十多年前在杭州,梅雨时节再逢君,才有机会见识杨梅的本来面目。
那次采访的间隙,杭州的同行们带我领略本地人才晓得的美食。
一天晚饭后,一群人在 故园无此味 著名的青藤茶馆坐下。
茶未起,先上些时令鲜果,一盘托在白瓷素碟里的杨梅施施然摆在桌上。
我下意识皱了一下眉,酸涩的记忆涌起,都能感觉到口中唾液分泌了。
同行的人忙让:“快尝尝。
”我心下迟疑,又觉不便拂了主人美意,问道:“酸吧?
”主人但笑:“尝一个嘛。
”一颗入口,意外到不能自持:满口清甜,果肉虽然是浆果的软,又有明显的颗粒感和韧性。
也不是一味地甜,清香和微酸不时从甜里若隐若现地浮出来,像“和羞走、倚门回首”的神秘少女,你一颗又一颗地入口,只想把那惊艳的感觉留住。
说起在北方吃到的杨梅,主人笑说,杨梅很娇贵,有“一日味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的说法。
杨梅熟透了根本无法保存,更别说运输了。
你吃的杨梅一定是半生摘下来,喷上保鲜剂,到了再催熟,哎呀,吃不得的。
那日我的表现毫无淑女风范,一盘杨梅几乎被我一个人吃掉,再上的我实在无力再战,其他人才吃到了。
第二天早饭时才惊觉,一口牙都打了软腿儿,嚼面食都觉无力。
原来那隐在甜中的一点微酸,竟 是这样蚀骨铭心。
其实杨梅的盛名,早在我了解它之 前。
南北朝人江淹是有记录的将杨梅入诗 的第一人,他的四言诗《杨梅颂》称赞“珍过荔枝,香超木兰”,并将杨梅的色、香、 味、形及生长环境、装盘品尝写得极为形象而优美。
宋朝人对杨梅是真爱,陆游、杨万里都有赞杨梅的诗。
诗人平可正更直言,五月杨梅已满林,初疑一颗值千金。
味比河朔葡萄重,色比泸南荔枝深。
最有意思的还是苏东坡,先是大赞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后来却又认为:“闽广荔枝、西凉葡萄,未若吴越杨梅”。
这一评价,出自这位美食家之口,吴越杨梅自然就身价百倍了,故有“吴越杨梅冠天下”之誉。
明人徐玠更写了两句特别逗的诗:若使太真知此味,荔枝焉得到长安。
听上去是为杨梅拈酸,其实各美其美,杨梅大概不在乎荔枝到不到长安。
古人吃杨梅已经很讲究了。
杨梅因有微酸,古人食用时常常会加少许食盐浸渍片刻,一可杀菌,二则减少酸味。
唐代大诗人李白写过一首《梁园吟》,玉盘杨梅 为君设,吴盐如花皎白雪。
玉盘杨梅的搭配,美不胜收。
明末文人文震亨在《长物志》里写过杨梅的另一种包装方式———漆盘。
“杨梅,吴中佳果,与荔枝并擅高名,各不相上下。
出光福山中者最美,彼中人以漆盘盛之,色与漆等……”盛放杨梅的包装盒是上等的漆盘,颜色与杨梅一样紫乌发亮,想想也是赏心悦目。
不过在我心里,始终不及白玉、白瓷的素盘,更衬杨梅的“玉肌半醉红生粟,墨晕微深染紫裳”。
因为杨梅不耐储存,江南人习惯把上等的杨梅浸泡在优质白酒中制成杨梅酒。
杨梅酒色艳如石榴汁,可媲美粉红香槟,更妙可养阴益气,清热除湿,梅雨天气的一盏杨梅酒,任何形容词都太苍白了。
此番沪上之行,比记忆中梅子成熟的时节稍早,未料到有杨梅吃的。
晚间与同行诸友行散,说到杨梅,又一阵齿颊间唾液疯狂地分泌,却是馋得了。
及至杨梅终于入口,记忆的苏醒与加深,倒让人惆怅了。
江南,我们终究是过客,诗人说“满口酸甜不思归”,我心里却明白他的意思:奈何,故园无此味。
也由人事也由“天” □傅绍万 手头有一本小册子,是某某大师的大预言精选。
自然界如汶川、玉树地震,人世间如东西方政要上台下台,其早有预言。
其言之凿凿,我却怎么也信不起来。
人、事早由天定,还能早看明白,人还有什么必要去奋斗、去忙碌呢? 中国是一个占卜的古国,方士辈出、术数繁荣。
《汉书·艺文志》中就有七略《术数略》,列出了六种术数,即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也就是看相术和风水术。
上下五千年,纵横数万里,术数时起时落。
至今日,涂上了科学的色彩,又大行其道。
如今的术数虽新,但万变不离其宗,不过是“传统文化”有了新包装。
那么,我们还是看看古人是怎么对待的吧。
中国商朝时的占卜法是烧灼甲骨,根据这些甲骨的裂纹,断定所问事情的吉凶。
到了西周,又辅之另一种方法,就是揲蓍草的茎,形成各种组合,产生偶数、奇数。
这些组合的数目有限,可以用固定的公式解释。
八卦和六十四卦的阳爻、阴爻,就是这些组合的图像。
占卜者用这种揲蓍的方法,得出各爻,然后对照《易经》,读出它的卦辞爻辞,断定所卜的吉凶。
殷商时期,周要起兵讨伐殷,出现了许多吉兆,如苍鹰群飞,白鱼入于王舟。
殷以白为尊,预示殷要被周所俘获,所以更感觉大吉大利。
但周军分析形势,认为条件不成熟,没有出兵。
一年后,准备正式发兵,但占卜得到的却是大凶兆。
怎么办?这时,姜太公丢掉蓍草,把龟壳踩到地上,说:枯骨死草,焉知吉凶!大兵进发,摧枯拉朽,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同一种现象,不同的解释,可以得出吉和凶完全不同的结论。
明朝有个和尚道衍,是帮助朱棣造反夺天下的第一智囊。
他的师傅也是个世外高人。
洪武十五年,旧历九月二十四日,朱元璋的马皇后入葬,突然下起大雨,葬礼无法举行。
朱元璋十分恼火,相关官员难辞其咎。
龙颜大怒,一些人就得人头落地。
这时候,道衍的师傅高僧宗泐上前说了四句偈语:雨落天垂泪,雷鸣地举 哀。
西方诸佛子,齐送马如来。
朱元璋转怒为喜。
名师出高徒,道衍在这方面的表现更为不凡。
建文元年七月六日夜,朱棣举行誓师大会,正式举起造反的大旗,突然起了狂风暴雨,刮得房瓦掉地,这太不吉利,人人大惊失色。
这时候,道衍和尚站了出来,说道:飞龙在天,从以风雨,殿瓦坠落,这预示大王要换黄瓦了,也就是要做皇帝了。
一句话,使士气大振。
大智大慧之人,凡占凡卜,总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化凶为吉。
那些愚昧迷信之人,做事就荒唐了。
1841年,中英虎门之战,出了一出闹剧。
清朝大将杨芳,在前线观察敌情,发现敌人的舰艇在运动中射击,百发百中。
他惊讶异常,认为敌人用了魔法。
回去备战,他让士兵到处搜集臭粪桶,因为迷信说法,秽物可以破魔法。
第二天,双方开战,他先让士兵用木船往敌舰上扔粪桶。
法国人先是迷惑不解,继之一片哄笑声。
清军自然大败。
这杨芳可不是草包,是久经战阵的猛将,可惜太不了解西方科技,闹出如此笑话。
悲哉大清! 我们的孔圣人,对待占卜、命运,又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做法。
孔子一生都在推行自己的道,为此而周游列国,但是,他的道却很难为统治者所接受。
孔子就说:“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他尽了一切努力,又归之于命。
他说的“命”,是告诉我们,人的活动要取得成功,总需要宇宙间的条件和力量相配合,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应该做的事,而不计较成败。
这样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所谓“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面对如今出现的形形色色的大师,面对神仙、神算对我们未来命运的预卜,面对那些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异兆,应当怎么对待,历史和智者告诉我们的,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 读史札记 心灵小品 绿眼睛 □雨兰 那时,我经常想象,她就是小村里的一只绿色的大眼睛。
我经常去看看她。
当我看着她时,她也用绿色的大眼睛看我,看得我的心清澈起来。
她的绿眼睛那么美,那么安静,而我的小小身影,也在她的绿眼睛里轻轻荡漾。
更多的时候,她的绿眼睛是在望着天空。
天空也在她的眼睛里,在她的眼睛深处,蓝蓝的,很遥远,也很神秘。
她的心里是不是也装着一个小小的记事本?她是不是要记着云朵在蓝天上的悠闲漫步,有多少次走远了,有多少次又悄悄走回来;她是不是要记着飞来飞去的燕子,有多少次在她的眼前欢快地飞舞,优雅地展翅,羽衣闪亮;她是不是要记下岸边俏立的垂柳,一天里有多少次临水照影慢梳妆;甚至,记着悄悄跑来喝水的小田鼠,掠过水面的蜻蜓……也许,她什么都记不住,什么也不想记住。
她只是任凭那些天上的云朵、俏丽的燕子、娇小的麻雀……来的轻轻来了,走的轻轻走了,无牵无挂,无忧无虑,自由自在。
是的,她不像我那么敏感,那么小气,我会在心里默默记下生命里的暖与疼,记下一天里的笑与泪,记下妈妈的盈盈笑脸,爸爸的严肃目光,祖母的絮叨。
她只是安安然然地睁着眼睛,微风吹过时,她的大眼睛就绿波荡漾起来,就笑纹细密起来,这时,她看我的眼神就朦胧起来,就波动起来。
下着小雨的时候,我也偷偷地去看她。
一滴一滴的雨点儿排着长队,飞向她的大眼睛,她都微笑着接纳,笑纹儿密密麻麻,重重叠叠,数也数不清。
晴朗的下午,倾斜的阳光照到她的时候,她清凉的眸子里,就开始盛着金色的光芒了,美得让人惊艳,美得让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喜欢静静地看着她,村里有些皮小子经常拿小石子,在她平静的水面上打水漂。
这是不是经常要吓她一跳呢,但她只是眨巴眨巴眼睛:嗨,那些小伎俩,我见得多了呢。
她在小村的南面,称它为湖,实在是,唉,实在是她太小了,她只是一个人工挖的池塘。
如今,她安静地泊在我的记忆深处,也泊在我的心底。
我轻易不去惊扰她,我也不会舍得惊扰她。
强词有理 □韩浩月 假期时,去野外闲走,路过一片麦地,快到丰收的时候,麦穗沉重,风中微微晃动,麦地深处有虫鸣鸟叫,麦地远处有农人吆喝的声音,忍不住拿出手机,拍了小视频,收录眼见耳听的这一切,发了朋友圈。
瞬间点赞者众,评论者纷纷,一条不过十秒钟的麦子小视频,震惊了朋友圈。
有人立刻发来消息,索要高清原图,换成了自己的头像,有人则拿去当了朋友圈封面;有人则询问麦地在哪里,打算亲往拜访;有人可能是故意开玩笑,问这是麦子还是水稻?这个问题把我气笑了。
城里人五谷不分,遇到有关庄稼的事大惊小怪,并不为过。
说真的,就算我在朋友圈看到别人发这样的图片或视频,也会忍不住点开看看,然后点个赞,留个言,评个论。
朋友圈里天天高大上,多是咖啡馆里谈的内容,立项啊、开机啊、首轮啊、上市啊等等,偶尔有麦子出现,大家难免围观看个稀奇。
我留恋麦子、晒麦子的影像,并非是在这移动互联网时代,卖弄什么农耕时代的浪漫。
实则相反,看到麦地最先想到的是烈日下割麦子的痛苦,麦芒穿过裤腿衣袖亲吻皮肤的刺痛。
现在和过去的麦子 麦子从麦地到麦仓,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过程。
割麦子是先要闯过的第一道关。
熟透的麦子需要第一时间割下来,否则有“熟掉头”的风险———沉甸甸的麦穗等不到收割它的农人,径直地掉进了田里,成为野外鸟类的食品了。
割麦子需要穿上长裤,裤子最好是厚一点的,还要带上套袖,这么做的好处是可以阻止麦芒。
但就算全副武装,割完麦子晚上回家洗澡的时候,全身都还依稀可见被麦芒刺出的红点。
一整天麦子割下来,腰酸背痛。
把麦子运出田地后,下一个去处是打麦场。
童年的打麦场,是爷爷赶着牛拉的石碾,缓慢地在场上转动,一圈又一圈,直到把麦子全部碾出来,那是一个人的劳动,不太用别人怎么帮忙。
后来为了提高效率,普遍开始使用脱粒机,约两米长的脱粒机后面站着三四个人,把麦捆打开,分成一小把一小把地塞进去,麦粒和麦秸便会被机器分开,脱出的麦粒直接进了装粮食的口袋。
脱粒的时候要分外小心,不小心的话手臂很有可能被卷进机器,丢掉一只手或一只胳膊。
我在脱粒的时候不担心手臂的安全,因为我始终保持着敏捷的本性,不会与机器较劲。
最为揪心的是打麦场四处飞扬的灰尘,简陋的口罩根本阻挡不住肮 脏的空气进入鼻孔,混杂了各种奇怪物质的麦场空气通过呼吸道进入肺管,要咳嗽好多天才能彻底清理掉。
装进袋子的麦子,要在麦场被清理干净之后晾晒,通常需要晾晒三五天的时间。
夏天的骄阳在加快麦子的成熟度,把最后一丝水分从麦子的身体里驱赶出来。
下午到傍晚的那段时间,是一天当中起风的时候,也是到了扬场的时候,扬场的人用一把大大的木锨,把麦子高高抛向天空,抛出一道优美的弧线,麦子在空中飞扬,掺进粮食的碎麦秸等等会随风飘走,只留下干净的麦子。
我喜欢这个场景,常呆在麦场边看扬麦子很长时间,这是整个麦子收获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它意味着残酷的劳动彻底结束,是尽可以享受丰收喜悦的时刻。
喜欢麦子装进粮仓时的那种踏实感,但确实不爱割麦子。
我上班能挣工资之后,就再也没下过麦地。
每年麦收季节都是花钱雇用收割机。
轰鸣的收割机,咆哮着闯进麦地,几个来回就把几亩地麦子收光了,比以前能节约很长时间,劳动强度自然也降低到可以忽略不计。
这真是太好了。
为了逃避一辈子割麦子,我跑得远远的,一跑就是二三十年。
可如同哲人所说,幸福的感受总是短暂且易忘,唯有苦痛能在生命里留下深刻的痕迹。
如今我用手掌 抚摸麦田,已经没有了如芒在背的不适感,取而代之的是无法形容的愉悦。
时间果然有美化过往的功能。
我想,朋友圈里那些为麦地和麦子点赞的朋友,也想当然地联想到了许多美好的景象。
比如他们的隐居梦、农耕梦、田园梦。
可是他们(包括我自己)都知道,这仅仅是一个梦而已。
甚至连梦都算不上,顶多算个臆想。
要是真这么热爱粮食、庄稼与土地,从北京三环任一方向开出个十几二十公里,都能找到各种时兴的瓜果蔬菜、玉米小麦。
可很少有人这么做———找一块农田,默默地什么也不说,什么也不做,只在地头呆上几个小时。
无论从文学层面还是从生活层面,“麦子”都是一个重要的意象。
中学时候写诗,最爱的组合就是把“麦子”与“黄金”组合在一起,根本不管它风马牛不相及。
搓几粒还未成熟的麦粒放在口中,嚼几口之后口腔便充满清香,这才是土地和风的结合催生出的粮食清香,这才是生活的滋味。
我的朋友们,希望你能抽个空在夏天寻一块麦田,搓几粒麦粒尝尝,或能唤醒你那百毒不侵的味蕾,体会一下舌尖上的乡愁。
哪怕拍个图发个朋友圈转身就走呢,那也是好的。
城市生活太单调无味没有想象力了,需要点泥土的气息。
坊间纪事 少的胜利 □董改正 一家特味店新出一种“秘制”熟食,店堂大屏幕上隆重地做着广告,说武则天渐感容颜衰老,派人到民间四处搜罗养颜高手,但这些人所用材料也无非枸杞、何首乌、燕窝之属,既无创意,口感也差,女皇恼怒之余,除了一位的“作品”因为验证还需时日外,其余的通通逐出宫去。
留下来的这位,烹制的是秘制猪手。
此味以流水浸三天,洗七七四十九遍,再用当归、藏红花、葛根、甘草等二十多种中草药熬制了九个时辰。
食用当日便有效用,一个月后,可以生肌活肤,犹春风化雨。
一辈子食用,可以永葆青春。
女皇用后不到一月,便肤白如处子,肤下隐隐晶莹有光。
女皇大喜,这道菜便成为了皇家秘制。
千百年后,出现我的眼前,与有荣焉。
这个故事所要强调的是那二十多味中草药,尤其是“二十多味”。
当我们要表示一种地位时,习惯的思维就是用数词,数词后面加量词,它们一起构成了一种优势。
大到一个国家的介绍,小到一个人的名片,微到一本书的推介人数,都用数量来展示,数量是硬性指标,具有毋庸置疑的说服力。
所以我们习惯了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堆积这些“数量”,以抬高人生的高度,拓宽人生的维度。
参加各类考证以积累证书,参加各个协会以累积头衔,参加各种比赛以积攒奖牌,拍摄各地照片以酷炫游历等等,这种加法且不说是否有益于人生,其间必是焦虑和负累,生活的乐趣定然少了很多。
我看过许多选秀节目,选手在展示才艺时,往往令评委瞠目结舌:他们会的太多了。
我们在培养孩子或自修时,都喜欢往“多”的上面发展,所谓“技多不压身”。
当所有的人都奔“多”而来时,那就没有最多,只有更多了。
这让我想起张学友来,当时他才出道时,不但不会舞蹈、乐器之类,甚至连乐谱也 不认识,但是他有一点:专爱唱歌,痴迷唱歌,一心一意地唱歌。
会很多才艺的人有很多,但张学友只有一个。
“多”与“少”孰优孰劣?答案是辩证的。
一个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一味追求“多”,便往往会陷入了泛泛。
你可能会认为会的越多,选择的机会越多,但是却忘了,在激烈的竞争中,比的往往不是会多少,而是在某一个领域,你是不是高手;而别的领域,自有别人去做,社会自有分工,用不着你一个人包揽。
用人者缺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如果一万个都会舞蹈、乐器、英语,而用人单位需要的只是一个会藏语的,那么“一万”和“一”是相同的。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如果没有强大的自控力,“多”很难让人静心定性,很难专注,而不专注是很难成就事业的。
所以,做切合自己天赋的减法是必须的,就像一棵白杨树,它的天赋是笔直向上的刚性,而不是旁逸斜出的婆娑,那么就必须剪枝,以促其向上。
一个足球运动员,他需要掌控球场的技术,而会不会弹吉他并不重要,是不是某个协会的理事更不重要。
直到剪得生命的枝条疏朗时,可以看到星空时,心里才不会焦灼,才能深呼吸,专注于一件事,只要选择正确,鲜有不成的。
脱颖而出中“颖”指的就是“尖子”,尖是以“小”和“少”而突出的。
诗作为文学的冠冕,是以少胜多的艺术,她的意义在于以有限达无穷,以平淡而致深味,以一瞬而通恒久。
卞之琳的《断章》、庞德的《在地铁站》,皆是如此。
诗意人生也当如此,能有一种深到骨髓的幸福,有一份爱着享受着的工作,有一个情趣相投的爱人,有一两个可爱健康的孩子,有一群谈心喝酒的朋友,不就够了吗?就像祖咏到长安应试,规定写六韵十二句的五言长律,他写了四句,就“纳于有司”了。
有人惊讶,他回答说“意尽”。
好一个意尽啊! 时尚辞典 垂杨风影 □张期鹏 一个地方,倘能让人记住,一定有它的特殊之处。
或风景,或人物,或永难湮灭的遗迹,或流传久远的故事……这些,都会构成许许多多非同一般的传奇。
垂杨,便是这样一个地方。
但在陌生人眼里,它又实在太普通不过了:一个小村,百多户人家,都是平凡的民居和平常的街巷。
它就那么静静地居于莱芜北部新城的一隅,好像村东河边随处生长的垂柳一样,默默地面对大地长空,悄然迎接着一年四季。
只有清风拂来、鸟雀飞来的时候,它才微微摆动长发,似乎透露出了一点深不可测的秘密。
如若时光倒流两千多年,我们穿越无数的历史烟云,深情回望中华大地上那个诞生了诸多思想巨人和伟大思想的时代,就会慢慢感觉到这个地方的神奇和不凡。
这是孔子曾经到过的地方。
甚至可以说,这里是孔子当年求学问礼的一个生动课堂。
史载,春秋时期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齐国,回国途中其长子病死。
因路途遥远难以归葬,只好沿途择地葬焉。
当时尚且年轻的孔丘听说后,即不辞辛苦跋涉数百里前来观看、学习吴国葬礼,并且留下了“延陵季子之于礼也,其合矣乎”的感叹。
只可惜,这段夫子重礼践学的佳话,因岁月漫漫,遗迹不存,后人只能怅惘空怀了。
直到明代隆庆四年(1570),江西临川人傅国璧任莱芜县令,深为孔子观礼之事湮没无考可惜,于是费心搜集古籍旧志记载,四处请教有学问有研究的长者,最终查明当年孔子观礼之处即在垂杨一带。
为彰明先贤圣迹,续延莱芜文脉,他又在此地构房筑屋,建成了莱芜历史上著名的“垂杨书院”(亦称“观礼书院”)。
同时,树“孔子观礼处”碑、作《观礼书院记》以为纪念。
傅国璧在《观礼书院记》中说,书院建成之后,远近学子纷纷而来,“争欲从观礼处诵习圣贤之书,以助化成天下之志”,可谓学风文气盛极一时。
如今,四百四十多年时光倏忽而过,那方历尽风雨剥蚀和某些时代文化戕害的石碑仍在,让这个不起眼的小村古韵悠悠、文风徐徐。
它让人们回首历史,神往先贤;让人们似乎看到了灵魂的源头,思想的来处。
它像细细抚过柳枝的轻风一样,从远古吹来,向未来拂去,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据说,“孔子观礼处”碑的对面,就是当年“垂杨书院”的旧址。
虽然原有的建筑几经岁月轮回,早已风流不在,但站在遗址门前,思绪依然牵扯不住地往前、往前、再往前延伸,耳边仿佛回旋起古老悠远的弦歌之声,空气中也缭绕着似浓似淡、若有若无的书香、纸香和墨香。
这一切与垂杨的风影交织、融合在一起,浸润了莱芜的山川草木,让这方土地慢慢变得宽厚、博大、深邃起来了。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明清两朝从莱芜大地上走出的近三十位进士的身影。
他们或政绩卓著,或文采斐然;或为国捐躯,或执教乡里,成为莱芜数百年间的光荣和骄傲。
历史的神奇之处还在于,在“垂杨书院”建成之前,莱芜进士仅有一人而已。
于是,在这垂杨风影之中,我看到了堪称“莱芜现代三贤”的著名散文家吴伯箫、著名历史学家王毓铨、著名诗人吕剑的身影。
他们都用自己的出众才华,让莱芜不“芜”成为现实。
文脉千年,就像插入泥土的柳枝一样,扎根于大地,不断地分生,旺盛地生长。
垂杨小村,就那么静静地坐落在那里;“孔子观礼处”石碑,就那么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但这方土地上的杨柳,似乎总有那么一点不同寻常的风姿。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