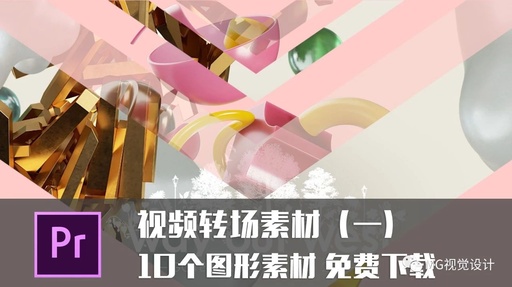B4青阅读
2022年4月22日星期
五 电影是否非得讲故事?这是可争议的话题。
导演是否该写小说?不必争议:导演就是导演,多少编剧和小说家等着导演找他们呢。
嗜好文学而终于去拍电影的个例,却是有的,眼前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好导演。
在他手里,文学如何走向电影,电影如何脱胎于文学,可以是个话题。
我喜欢万玛的每部电影,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质朴的作品,内地电影好像早就忘了质朴的美学。
什么是质朴呢?譬如阿巴斯。
谁会说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吗?可是谁能拍出他那种无可言说的质朴感? 而“质朴”在万玛那里是天然的,虽然他的每部电影故事各异。
是因为藏族人才有的那种质朴吗?没有简单的答案。
宗教,绝对是渊源之
一,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
当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够给出、应该给出的悬念、惊奇、无数细节,就像内地一流导演做到的那样,但他的每部电影都被他天然赋予了质朴的美学。
彼此启发?书写早期小说的万玛,并不知道还要 过二十年才会去拍电影,那时,他的夙愿是当个作家——相对于内地梦想当导演的小子,一个藏区青年的电影梦,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他聪明而勤奋,同时用藏汉语写小说,并彼此翻译,二十多岁就出版了小说集。
他不知道,这些小说悄悄孕育着他的电影。
有趣的是,当新世纪初,万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拍处女作,他还认真写了剧本,并未意识到先前的某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
而觉醒的电影意识告诉他,必须添加影像语言。
《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说,并在电影中丰满了故事的羽翼。
现在,当万玛推出这批新小说时,他已是个获得肯定的导演,经验丰富,深知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热衷于写小说。
问题来了:理论上,从此他的每篇小说——文字的编织物——都有可能成为 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 ◎陈丹青 藏语,是万玛的母语,他实现了语言跨越,用汉语写小说。
在万玛的汉语小说里,质朴呈现为“本色的写作”。
这不是对他行文的贬抑,而是,小说自身的魅力、说服力、生命力,亦即,说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
万玛早期的若干小说,我读过,有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难以忘怀,这就是 小说家的天分。
换句话说,什么能进入小说,成为小说,万玛异常敏锐。
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想象力,还是写作的野心。
眼前这批万玛的新小说,展示了进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
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长,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进入诗人的日记……原先的乡村主题也增添了叙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节更离奇——当然,他再次尝试了类乎神话和寓言。
但我读着万玛的小说,很难忘记他的电影。
在他手里,电影与小说是两件平行的、愉悦的事,还是未必交叉,却又 电影剧本。
我无法知道当万玛继续写小说,他内心是否会掂量:这篇小说能不能变成电影?而我,他的读者,因此被万玛感染了一种微妙的意识:他使我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电影。
最近他写了些什么呢?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亲。
她的头胎日后成长为理科优等生,
十 多年后,第二个孩子被发现是位活佛。
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这两兄弟跨越了藏地的过去和今日,这伟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实,我也愿意将这篇小说看作万玛的又一个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亲。
《故事只讲了一半》回应了万玛的早期电影《寻找智美更登》。
那是找寻传奇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万玛的主题中,他的故乡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记忆,而在这篇故事中,讲述者的亡故,将记忆带走了。
《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再一次,万玛采用了叙述中的叙述。
那是他格外擅长的本事——他的两部电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
《寻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车里一路讲述恋爱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着失恋的姑娘,跟车去找恋人讨个说法;《气球》中那条次要的线索,动人极了:因失恋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发现他俩的爱与分手,已被男友写成小说。
这位尼姑多么想读到那小说,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进炉膛烧了。
《特邀演员》的焦点,是那位老牧民与少妻的关系,第一次,万玛的小说出现了电影摄制组。
那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与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结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种关系。
万玛似乎从未忘记在他的视野中双向地触及“过去”与“今天”。
少年同学的斗殴、寻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获得生动泼辣的描 写,直到出现那只硅胶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
斯文寡言的万玛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从暴力的景观中看到喜剧感,而他对暴力的观察与描写,在我看来,多么纯真。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逸出了万玛惯常描写的空间,进入咖啡馆,出现两个人兴味盎然的漫长对话。
我不知道现代短篇小说的思维是否影响了万玛,而“背景音乐”这一话题,似乎又来自电影思维。
“咖啡馆”生活让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藏区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个西藏啊——而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觉得是万玛用他的小说与电影带来的。
万玛套用民间故事结构创作的《尸说新语:枪》,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
阴阳转世、鬼魅托尸、人兽变异、起死回生……原是各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老生常谈”,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绝——我相信,万玛是个酷爱倾听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将西藏的民间传说译成汉语,出版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万玛重构并发掘了新的可能。
在这篇小说中,他抓住了“故事”这一观念:“讲述”与“聆听”的双方都愿付出生死代价,换取“故事”。
而成为导演后的万玛不肯止步于老调,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 一把枪!枪,可说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经万玛这一转换,人们百年之后读到这个故事,将会知道在我们的世纪,人对付鬼魅时,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诗人之死》似乎能够成为电影的脚本——很难说这是个悲剧故事,但在万玛的小说和电影中,爱情总是纠结的、反复的、忽而闪现希望,终究归于失败。
“坟地”,是诗句,也是诗人的结局,又成为小说的意象。
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万玛这样看待爱情与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
那像是一组电影镜头,然而主角“我”的一连串内心活动,完全属于“小说”。
当“洛总”大叫“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小说到此刹住——万玛却给出了电影画面般的震撼(我会想象镜头掠过所有惊恐的脸),然而,却不很像电影的结尾。
我从未试着谈论小说,不确定以上解读是否切当、有趣。
能确定的是,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
他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一篇接一篇地写小说,带动了一群藏地文艺才俊。
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瞿瑞 在《书籍秘史》的序章,作者伊莲内·巴列霍将我们带回遥远的古希腊时代:一队人在荒凉的道路上跋山涉水,千辛万苦,为了执行秘密的任务——为埃及国王寻找世界上的所有书籍(当时的稀缺珍宝),来填充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而得名,亚历山大南征北战,常年随身带着一本《伊利亚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受到了书中阿喀琉斯的影响,亚历山大才萌生了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建立起地跨欧亚非大陆的辽阔帝国。
然而,战争带来的荣光非常短暂,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离世,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历史开了个玩笑,使马其顿人托勒密成为埃及的国王,这个流落异乡的统治者不了解埃及习俗,听不懂埃及语言,于是将首都迁移到一块飞地上——地中海的法罗岛,建立了标志人类文明曙光的城市亚历山大港。
接下来的两百年,托勒密国王(及其历代的继承者们)建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命令收集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想要让这个地跨欧亚非的小岛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座灯塔,一座守护哲人智者的家园,一座接纳所有异国文化的避风港,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世界主义梦想,来自一位因权力而世代流放在异乡的国王。
今天的我们大概不会想到,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座由祭司主持的寺庙,当时的人们几乎是以一种朝圣的心情,进入书籍的世界。
在世界三大宗教诞生之前,文明本身曾发挥着一种宗教作用。
对此,伊莲内·巴列霍写道:“想想那些古希腊人梦想捧着书卷去敲开天堂的大门,着实令人感动。
” 《书籍秘史》并没有探索书籍作为“物品”的技术进化史,而是讲述书籍诞 生的历史,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以书籍为象征的人类文明诞生了。
它从野蛮地带中生长出来,并且生根发芽。
伊莲内·巴列霍散点式的叙述,带领读者游弋在遥远历史的碎片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碎片更为真实可靠,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像一条时间的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
它更像宇宙大爆炸后,朝着四面八方放射开去的星云。
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至今仍然隐秘地影响着现代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苏格拉底虽然反对书写文字,他的智慧言辞仍然在今天的世界回响;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被追溯为文学源头,至今仍然被无数人阅读;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对于时间的思考今天仍然有效;女诗人萨福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然而那些诗句中抒发的情感至今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最初游历世界之人,他站在本民族之外的视点观察世界的方式,对充满民粹主义的当代世界仍然有所启发。
幸亏有了书籍,我们才能听到这些古老声音的回响。
然而,伊莲内·巴列霍提醒我们,保留这些声音并不容易——一代代人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正如人类自身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创造出文明的火种,书籍的诞生也伴随着漫长的进化史:从口语文字到书面文字的转化、字母表的创造、书写材料的不断革新、印刷术的发明……它是无数美妙的偶然性、无数个体的渴望,以及无数人类的智慧的共同结果。
人类之所以需要书籍,是需要保存文明的声音,来纠正人类的野蛮行径。
这些古老的声音并没有因遥远而显得过时,是因为人类文明,并没有随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进化,在文明薄薄的涂层下,依旧填充着野蛮的土壤。
而书籍诞生的 历史,从来都是文明和野蛮的交战史。
西方最早的史诗是描述特洛伊战争 的《荷马史诗》,存世的最早戏剧是描述波希战争的《波斯人》(埃斯库罗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这一切并非偶然,人类的战争从未停止。
伊莲内·巴列霍在《书籍秘史》中也描述了其中一次:古罗马人通过抢占土地来建造家园、通过抢夺女人来繁衍后代、通过买卖奴隶变得富裕,最终,发动野蛮的战争替代了文明的古希腊——这些事迹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它们在后来的两千年里不断上演。
每一次战争都毁灭了无数重要的事物,而当和平到来,人们又开始重建属于新的“文明”。
有时,首要考虑的是民族“自尊心”。
伊莲内·巴列霍详细讲述了新文明如何取代旧文明的过程。
书籍被烧毁——或者当作战利品被私人掠夺;擅长书写的文明人沦落为野蛮人的奴隶;曾经的图书馆被遗弃,又改造成新的形式:“罗马人建造了双子图书馆,就像世贸中心双子塔,用来强调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的同源性。
”正如所有的“当代人”都希图为自己创造的“文明”正名,而把过往时代的文明推到不重要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从遥远的过往、从被遗忘的文明中寻找答案。
伊莲内·巴列霍的文字充满了反讽精神,她耐心地观察着充满矛盾的人类行为:人们崇拜暴力,人们制造伤害,人们暗中学习,人们渴望变得文明和高贵——并藏起了野蛮暴力的那一面。
人类的文明进化遵循着这一模式,每一个时代里,文明和野蛮都在相互角逐,而每一本书籍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禁止什么样的书籍,人们又在守护什么样的书籍——就像是无数微型的文明之战。
每个身处历史的人仍然能够作出他们的选择。
有时,守护一本 书,就是守护理想的世界形态。
也许只有被书籍拯救过的人才能写 下这样一部作品,在后记中,伊莲内·巴列霍写道,她是在个人境遇一片灰暗中写作了这本书。
也许正是这种灰暗构成了这本书耀眼的能量,伊莲内·巴列霍怀着对于书籍的激情,旁征博引,又不失感性。
因此,那些遥远的知识并不冰冷,而是转化为鲜活的情感,回应着人们心中的问题。
比如,当看到描述古希腊人读书的画卷,她回忆起童年时对于听故事的依恋:“我把牙齿放在手掌上看:童年正在破碎,在身体上留下几个洞,沿途扔下一些白色的碎片,听故事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 了。
”——两千年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人在阅读时感受到的幸福都是相似的。
比如,作为一个作家,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写作面对的困难,以及写一本书意味着什么:“如同感受到大地正在脚下裂开。
说到底,写作跟那些我们没学会就开始做的事没什么两样,比如说外语、开车、当妈妈、活着。
”——两千年来,无论技术工具如何演化,人们在写作时交付生命的感受亦是相通的。
又比如,出于女性经验,伊莲内·巴列霍勇敢地批判文明的盲视和偏见:父权制度建造的文明中,对于女性创造力的束缚与偏见。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只有混入男作家的作品,才能偶然留存到后世。
而今天的女性,能够阅读和写作——但她们仍然遭受着传统偏见和忽视。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愤怒、痛苦以及热爱。
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人们靠不断地抄写一本书并小心保存,才能使之幸运地流传到后代,而毁灭一本书却只需要划一根火柴。
这就像是人类文明的整体隐喻:创造如此艰难,毁灭却如此轻易。
正是这永恒的不等式使人们永远感觉“境遇灰暗”,而只有体会过这种灰暗的人,才能够在灵魂上相互理解。
正如只有体会过书籍带来的安慰,才会变成守护书籍的人。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同样令人难忘,也许可以借用伊莲内·巴列霍写在这本书里的话来形容这种感觉:“拥有图书相当于在钢丝上走平衡步;相当于努力捡起宇宙散落的碎片,拼成有意义的图像;相当于面对混乱,搭建出和谐的建筑物;相当于聚沙成塔;相当于将我们害怕遗忘的一切找个地方守护起来;相当于拥有世界的记忆;相当于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
” 编辑/罗皓菱美编/路虓辉责校/方立杨波
五 电影是否非得讲故事?这是可争议的话题。
导演是否该写小说?不必争议:导演就是导演,多少编剧和小说家等着导演找他们呢。
嗜好文学而终于去拍电影的个例,却是有的,眼前的万玛才旦,又是小说家,又是好导演。
在他手里,文学如何走向电影,电影如何脱胎于文学,可以是个话题。
我喜欢万玛的每部电影,好久好久没看过这么质朴的作品,内地电影好像早就忘了质朴的美学。
什么是质朴呢?譬如阿巴斯。
谁会说阿巴斯的作品不好吗?可是谁能拍出他那种无可言说的质朴感? 而“质朴”在万玛那里是天然的,虽然他的每部电影故事各异。
是因为藏族人才有的那种质朴吗?没有简单的答案。
宗教,绝对是渊源之
一,然而万玛的影像故事处处是我们时代的日常生活。
当然,他十分懂得影片能够给出、应该给出的悬念、惊奇、无数细节,就像内地一流导演做到的那样,但他的每部电影都被他天然赋予了质朴的美学。
彼此启发?书写早期小说的万玛,并不知道还要 过二十年才会去拍电影,那时,他的夙愿是当个作家——相对于内地梦想当导演的小子,一个藏区青年的电影梦,不知要艰难多少倍——他聪明而勤奋,同时用藏汉语写小说,并彼此翻译,二十多岁就出版了小说集。
他不知道,这些小说悄悄孕育着他的电影。
有趣的是,当新世纪初,万玛进入北京电影学院,开始拍处女作,他还认真写了剧本,并未意识到先前的某些小说可以“变成”电影。
而觉醒的电影意识告诉他,必须添加影像语言。
《塔洛》《撞死一只羊》全部采用了他的小说,并在电影中丰满了故事的羽翼。
现在,当万玛推出这批新小说时,他已是个获得肯定的导演,经验丰富,深知构成一部电影的所有秘密,但他仍然热衷于写小说。
问题来了:理论上,从此他的每篇小说——文字的编织物——都有可能成为 在小说中呈现的万玛才旦 ◎陈丹青 藏语,是万玛的母语,他实现了语言跨越,用汉语写小说。
在万玛的汉语小说里,质朴呈现为“本色的写作”。
这不是对他行文的贬抑,而是,小说自身的魅力、说服力、生命力,亦即,说故事的能量,尤其是想象力,生动活泼地被他有限的词语建构起来。
万玛早期的若干小说,我读过,有位“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难以忘怀,这就是 小说家的天分。
换句话说,什么能进入小说,成为小说,万玛异常敏锐。
他的写作还活跃着另一种想象力,指向藏地的神话与民间故事传统,讲说奇幻故事,而其中的人物似乎个个活在今天的藏地。
我不知道这是出于想象力,还是写作的野心。
眼前这批万玛的新小说,展示了进一步的雄心,而且更自信了。
他的篇幅比早先加长,扩大了故事的跨度,人物、情节,主题,更显复杂,不再框限于乡村素材,小说人物开始进入城市,进入摄制组,进入咖啡馆,进入诗人的日记……原先的乡村主题也增添了叙事的幅度,故事更抓人,情节更离奇——当然,他再次尝试了类乎神话和寓言。
但我读着万玛的小说,很难忘记他的电影。
在他手里,电影与小说是两件平行的、愉悦的事,还是未必交叉,却又 电影剧本。
我无法知道当万玛继续写小说,他内心是否会掂量:这篇小说能不能变成电影?而我,他的读者,因此被万玛感染了一种微妙的意识:他使我在他的小说中,想象电影。
最近他写了些什么呢?譬如《水果硬糖》里那位神奇的母亲。
她的头胎日后成长为理科优等生,
十 多年后,第二个孩子被发现是位活佛。
可能吗?为什么不可能!我愿相信这两兄弟跨越了藏地的过去和今日,这伟大的生育如草根般真实,我也愿意将这篇小说看作万玛的又一个寓言:藏地,就是那位母亲。
《故事只讲了一半》回应了万玛的早期电影《寻找智美更登》。
那是找寻传奇的故事,换句话说,在万玛的主题中,他的故乡一再被拉回高原的记忆,而在这篇故事中,讲述者的亡故,将记忆带走了。
《切忠和她的儿子罗丹》,再一次,万玛采用了叙述中的叙述。
那是他格外擅长的本事——他的两部电影嵌入了故事中的故事。
《寻找智美更登》的中年人在车里一路讲述恋爱往事,不知道他身后坐着失恋的姑娘,跟车去找恋人讨个说法;《气球》中那条次要的线索,动人极了:因失恋出家的姑娘意外碰到前男友,发现他俩的爱与分手,已被男友写成小说。
这位尼姑多么想读到那小说,然而被她的姐姐,女主角,一把扔进炉膛烧了。
《特邀演员》的焦点,是那位老牧民与少妻的关系,第一次,万玛的小说出现了电影摄制组。
那是二十世纪的新事物,与故事中以古老方式结合的草原夫妻,遭遇了另一种关系。
万玛似乎从未忘记在他的视野中双向地触及“过去”与“今天”。
少年同学的斗殴、寻仇、扯平、和解,在《一只金耳朵》里获得生动泼辣的描 写,直到出现那只硅胶假耳,那只金制的耳朵。
斯文寡言的万玛令我看到他的另一面:他从暴力的景观中看到喜剧感,而他对暴力的观察与描写,在我看来,多么纯真。
《你的生活里有没有背景音乐》逸出了万玛惯常描写的空间,进入咖啡馆,出现两个人兴味盎然的漫长对话。
我不知道现代短篇小说的思维是否影响了万玛,而“背景音乐”这一话题,似乎又来自电影思维。
“咖啡馆”生活让我看到一个现代的藏区文化——多么不同于四十多年前我去到的那个西藏啊——而这种现代性的一部分,我有理由觉得是万玛用他的小说与电影带来的。
万玛套用民间故事结构创作的《尸说新语:枪》,可能是最令我信服的一篇。
阴阳转世、鬼魅托尸、人兽变异、起死回生……原是各国各地区民间传说的“老生常谈”,而在西藏“故事”竟被假托于“尸”,也算一绝——我相信,万玛是个酷爱倾听故事的男孩,他甚至将西藏的民间传说译成汉语,出版了《西藏:说不完的故事》,在这些古老的故事素材中,万玛重构并发掘了新的可能。
在这篇小说中,他抓住了“故事”这一观念:“讲述”与“聆听”的双方都愿付出生死代价,换取“故事”。
而成为导演后的万玛不肯止步于老调,他擅自在故事里塞了 一把枪!枪,可说是电影不可或缺的元素,经万玛这一转换,人们百年之后读到这个故事,将会知道在我们的世纪,人对付鬼魅时,手里多了一件武器。
《诗人之死》似乎能够成为电影的脚本——很难说这是个悲剧故事,但在万玛的小说和电影中,爱情总是纠结的、反复的、忽而闪现希望,终究归于失败。
“坟地”,是诗句,也是诗人的结局,又成为小说的意象。
我想知道:是什么使万玛这样看待爱情与婚姻? 《猜猜我在想什么》可能是我格外偏爱的一篇。
那像是一组电影镜头,然而主角“我”的一连串内心活动,完全属于“小说”。
当“洛总”大叫“这些人当中随便杀一个就行”——小说到此刹住——万玛却给出了电影画面般的震撼(我会想象镜头掠过所有惊恐的脸),然而,却不很像电影的结尾。
我从未试着谈论小说,不确定以上解读是否切当、有趣。
能确定的是,万玛以他难以捉摸而充满人文意识的才华,令人对今日藏地的文艺活力,刮目相看。
他一部接一部地拍电影,一篇接一篇地写小说,带动了一群藏地文艺才俊。
在内地的电影与文学景观中,藏地创作者的介入,已是清新的潜流,这股潜流,我以为始于万玛才旦,而且,始于他泉水般涌动的小说。
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瞿瑞 在《书籍秘史》的序章,作者伊莲内·巴列霍将我们带回遥远的古希腊时代:一队人在荒凉的道路上跋山涉水,千辛万苦,为了执行秘密的任务——为埃及国王寻找世界上的所有书籍(当时的稀缺珍宝),来填充世界上第一座图书馆。
这座图书馆因马其顿的亚历山大而得名,亚历山大南征北战,常年随身带着一本《伊利亚特》。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正是因为受到了书中阿喀琉斯的影响,亚历山大才萌生了建功立业的英雄梦想,建立起地跨欧亚非大陆的辽阔帝国。
然而,战争带来的荣光非常短暂,随着亚历山大的突然离世,他建立的帝国也随之分崩离析。
历史开了个玩笑,使马其顿人托勒密成为埃及的国王,这个流落异乡的统治者不了解埃及习俗,听不懂埃及语言,于是将首都迁移到一块飞地上——地中海的法罗岛,建立了标志人类文明曙光的城市亚历山大港。
接下来的两百年,托勒密国王(及其历代的继承者们)建造了亚历山大图书馆,命令收集世界上所有的书籍,想要让这个地跨欧亚非的小岛成为人类文明的一座灯塔,一座守护哲人智者的家园,一座接纳所有异国文化的避风港,这大概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世界主义梦想,来自一位因权力而世代流放在异乡的国王。
今天的我们大概不会想到,对于古希腊人而言,亚历山大图书馆是一座由祭司主持的寺庙,当时的人们几乎是以一种朝圣的心情,进入书籍的世界。
在世界三大宗教诞生之前,文明本身曾发挥着一种宗教作用。
对此,伊莲内·巴列霍写道:“想想那些古希腊人梦想捧着书卷去敲开天堂的大门,着实令人感动。
” 《书籍秘史》并没有探索书籍作为“物品”的技术进化史,而是讲述书籍诞 生的历史,在距今两千多年的古希腊、罗马时代,以书籍为象征的人类文明诞生了。
它从野蛮地带中生长出来,并且生根发芽。
伊莲内·巴列霍散点式的叙述,带领读者游弋在遥远历史的碎片中。
从某种程度上讲,碎片更为真实可靠,因为真正的历史,并不是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像一条时间的河流,从过去流向未来。
它更像宇宙大爆炸后,朝着四面八方放射开去的星云。
作为西方文明的开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至今仍然隐秘地影响着现代人对于世界的看法:苏格拉底虽然反对书写文字,他的智慧言辞仍然在今天的世界回响;盲诗人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被追溯为文学源头,至今仍然被无数人阅读;哲学家赫拉克里特对于时间的思考今天仍然有效;女诗人萨福只留下一些断简残篇,然而那些诗句中抒发的情感至今引起读者的共鸣;而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最初游历世界之人,他站在本民族之外的视点观察世界的方式,对充满民粹主义的当代世界仍然有所启发。
幸亏有了书籍,我们才能听到这些古老声音的回响。
然而,伊莲内·巴列霍提醒我们,保留这些声音并不容易——一代代人为之付出了难以想象的努力。
正如人类自身经历了漫长的进化才创造出文明的火种,书籍的诞生也伴随着漫长的进化史:从口语文字到书面文字的转化、字母表的创造、书写材料的不断革新、印刷术的发明……它是无数美妙的偶然性、无数个体的渴望,以及无数人类的智慧的共同结果。
人类之所以需要书籍,是需要保存文明的声音,来纠正人类的野蛮行径。
这些古老的声音并没有因遥远而显得过时,是因为人类文明,并没有随技术的日新月异,共同进化,在文明薄薄的涂层下,依旧填充着野蛮的土壤。
而书籍诞生的 历史,从来都是文明和野蛮的交战史。
西方最早的史诗是描述特洛伊战争 的《荷马史诗》,存世的最早戏剧是描述波希战争的《波斯人》(埃斯库罗斯站在敌人的立场上,反思战争给人们带来的伤害)——这一切并非偶然,人类的战争从未停止。
伊莲内·巴列霍在《书籍秘史》中也描述了其中一次:古罗马人通过抢占土地来建造家园、通过抢夺女人来繁衍后代、通过买卖奴隶变得富裕,最终,发动野蛮的战争替代了文明的古希腊——这些事迹离我们并不遥远,因为它们在后来的两千年里不断上演。
每一次战争都毁灭了无数重要的事物,而当和平到来,人们又开始重建属于新的“文明”。
有时,首要考虑的是民族“自尊心”。
伊莲内·巴列霍详细讲述了新文明如何取代旧文明的过程。
书籍被烧毁——或者当作战利品被私人掠夺;擅长书写的文明人沦落为野蛮人的奴隶;曾经的图书馆被遗弃,又改造成新的形式:“罗马人建造了双子图书馆,就像世贸中心双子塔,用来强调古希腊文学和古罗马文学的同源性。
”正如所有的“当代人”都希图为自己创造的“文明”正名,而把过往时代的文明推到不重要的位置——也正因如此,我们才需要从遥远的过往、从被遗忘的文明中寻找答案。
伊莲内·巴列霍的文字充满了反讽精神,她耐心地观察着充满矛盾的人类行为:人们崇拜暴力,人们制造伤害,人们暗中学习,人们渴望变得文明和高贵——并藏起了野蛮暴力的那一面。
人类的文明进化遵循着这一模式,每一个时代里,文明和野蛮都在相互角逐,而每一本书籍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人们禁止什么样的书籍,人们又在守护什么样的书籍——就像是无数微型的文明之战。
每个身处历史的人仍然能够作出他们的选择。
有时,守护一本 书,就是守护理想的世界形态。
也许只有被书籍拯救过的人才能写 下这样一部作品,在后记中,伊莲内·巴列霍写道,她是在个人境遇一片灰暗中写作了这本书。
也许正是这种灰暗构成了这本书耀眼的能量,伊莲内·巴列霍怀着对于书籍的激情,旁征博引,又不失感性。
因此,那些遥远的知识并不冰冷,而是转化为鲜活的情感,回应着人们心中的问题。
比如,当看到描述古希腊人读书的画卷,她回忆起童年时对于听故事的依恋:“我把牙齿放在手掌上看:童年正在破碎,在身体上留下几个洞,沿途扔下一些白色的碎片,听故事的日子很快就要结束 了。
”——两千年来,不管世界如何变化,人在阅读时感受到的幸福都是相似的。
比如,作为一个作家,她比任何人都清楚写作面对的困难,以及写一本书意味着什么:“如同感受到大地正在脚下裂开。
说到底,写作跟那些我们没学会就开始做的事没什么两样,比如说外语、开车、当妈妈、活着。
”——两千年来,无论技术工具如何演化,人们在写作时交付生命的感受亦是相通的。
又比如,出于女性经验,伊莲内·巴列霍勇敢地批判文明的盲视和偏见:父权制度建造的文明中,对于女性创造力的束缚与偏见。
在古希腊罗马时代,女作家的作品只有混入男作家的作品,才能偶然留存到后世。
而今天的女性,能够阅读和写作——但她们仍然遭受着传统偏见和忽视。
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愤怒、痛苦以及热爱。
在没有印刷术的年代,人们靠不断地抄写一本书并小心保存,才能使之幸运地流传到后代,而毁灭一本书却只需要划一根火柴。
这就像是人类文明的整体隐喻:创造如此艰难,毁灭却如此轻易。
正是这永恒的不等式使人们永远感觉“境遇灰暗”,而只有体会过这种灰暗的人,才能够在灵魂上相互理解。
正如只有体会过书籍带来的安慰,才会变成守护书籍的人。
阅读这本书的过程同样令人难忘,也许可以借用伊莲内·巴列霍写在这本书里的话来形容这种感觉:“拥有图书相当于在钢丝上走平衡步;相当于努力捡起宇宙散落的碎片,拼成有意义的图像;相当于面对混乱,搭建出和谐的建筑物;相当于聚沙成塔;相当于将我们害怕遗忘的一切找个地方守护起来;相当于拥有世界的记忆;相当于筑一道堤坝,抵挡时间的海啸。
” 编辑/罗皓菱美编/路虓辉责校/方立杨波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