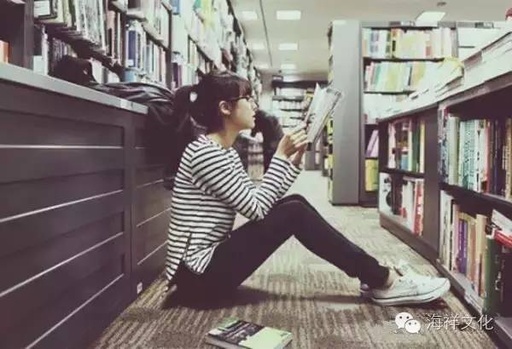http押//www.chaozhoudaily.com
2009年9月23日星期
三 副刊部主编责任编辑:杨树彬电话:2356773邮箱:juhang8899@传真:2265261 文艺评论 文学是少数人的精品创作 许民彤 9月4日的《京华时报》“张洁称害怕作品被多数人喜欢”的一篇文化报道说:在为期五天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张洁与西班牙女作家帕乌拉和文学批评家路易斯举行了对话。
当西班牙同行询问张洁的书在国内畅销程度时,张洁讳莫如深:“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
”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
9月5日的《广州日报》“作协主席不及网络写手”的文化新闻说:盛大文学去年推出的“30省作协主席小说巡展”近日公布了结果,吉林省作协主席张笑天凭《沉沦与觉醒》获得一等奖,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屈居亚军,不过,这些传统作家在网上的魅力远不及一些网络写手,作协主席们的大作在网上的点击率,平均下来明显不及网络写手,点击率最高的张笑天也只有200多万,与动辄上千万点击率的网络小说相比,差距仍然不小。
这样两条文化消息告诉了我们什么?这就是,在如今的文学写作、文学阅读中,是存在着两种文学的阅读写作追求和趣味的。
这就是作家张洁说的,“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
这 是一种,坚持文学和阅读的独立、个性的原则和价值。
还有一种是,“动辄上千万点击率的网络小说”的写作和阅读现象,这是以文学的阅读写作趋向于时尚、流行和畅销为趣味标准和价值尺度,通过所谓的“点击率”等这样的技术手段来获得市场和大众的认同,“点击率”的数量,成了一个衡量文学阅读和写作的依据和标准。
这种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现象,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萨特在评价文学阅读和写作现象时的一句名言———人类文化阅读历史上出现了两类文学:一类是虽不值一读,但拥有大量读者的文学;一类是无人去读的优秀文学……这种文学阅读写作的现象,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是“少数喜欢的”与“点击率”为王,那么,这是否也是未来的人们文学阅读写作的情形呢?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张洁所说是大有深意的,作为一个作家,她应该是知道美国著名作家塞林格的创作生活的。
作为拥有数万年轻读者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在声誉日隆之后,他并没有继续投读者所好,一本一本地频繁出版他的著作。
出版商知道他下笔成金,吁求他多多发表,他也不理。
他的唯一嗜好与乐趣便是写作,但不一定发表。
他曾解释,“不发表给了我可贵的安宁,使 我深感平静。
发表就会侵犯了我的私生则无意于这种自己的作品收获多少物质 活。
我爱好写作,但是我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繁华,内心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 的乐趣而写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的本性是 塞林格是不为时尚、为畅销、为“搏点击不容扰乱的……这样的对文学阅读写作 率”写作。
说到底,这是需要有自己的文学的风格和精神,我们在莫言、苏童、韩寒, 的理想、写作的定力和精神信仰的。
此外,当然还有张洁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坚守。
我们熟知的米兰·昆德拉,在几十年写作“90后”在向“80后”成名作家讨教文学经 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他除验时也发问“出书是为了出名还是因为对 了钓鱼和看书,就是写作,这不仅是高调文学的热爱?”可见,文学的理想和热爱, 低调的问题。
《百年孤独》的作者阿西亚·仍是一些人的一种信念精神。
马尔克斯,已经82岁了,一辈子坚持在宁 所以,文学的阅读写作,是为了“少数 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他的作品也因喜欢的”,做“少数人的事情”,还是相信 此有一种宁静的内心力量,由宁静和寂寞“点击率”为王?这是一个问题。
这时,我 汇聚成的力量沉淀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 让我们阅读时常怀感动……这些世界著《读书与书籍》中所说,“无论什么时代, 名作家的为文学而安静写作的行为,不是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似乎各不相悖地进 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行着。
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只不过是貌 的事情”? 似的东西。
前者成为不朽的文艺,作者纯 的确,在当今的消费主义文化占据人粹为文学而写作,他们的进行是严肃而静 们文化、精神生活的时代,文学的阅读和默的,然而非常缓慢。
在欧洲一世纪中所 写作,似乎都会受到这个时代精神和趣味产生的作品不过半打。
另一类作者,文章 的影响。
因此,对文学阅读写作,读者尤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它们却能狂奔疾 是一个作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驰,受旁观者的欢呼鼓噪,每年送出无数 有的追求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流行、畅的作品于市场上。
但在数年之后,不免令 销,作家自己成财富符号,上“富豪榜”。
人发生疑问:它们在哪里呢?它们以前那 至于有些网络文学写手,则毫不讳言相信煊赫的声誉在哪里呢?因此,我们可称后 “点击率”为王,自己的写作、收益和生者为流动性的文艺,前者为持久性的文 存,是为了“刷票”,为了“点击率”。
有的艺”,或许会得到一些启发吧! 说枫桥诗碑 韩望舒 到江苏苏州市,如不到寒山寺,则不算苏州客。
因为,寒山寺诗碑、钟声和苏州园林一样,那是姑苏的象征、苏州人的骄傲。
千年古刹寒山寺在苏州城西七里许的枫桥镇,始建于梁代天监初,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因唐贞观年间著名诗僧寒山子云游至此并主持,后人改名寒山寺。
这座寺曾多次毁于战火,现存景观为清末重建。
寺外,曲槛回廊,绿树黄墙,颇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寒山寺成为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大有关系。
唐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人张继在兵荒马乱中南下避乱,夜泊于寒山寺,触景生情,写下《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有限文字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钟声组成一幅远近有序、动静分明、色彩逼真的江南风景画。
张继诗之书于碑,从北宋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及战火等原因,在寒山寺内保存最完好的仅为晚清俞樾所书之碑。
据清代叶昌炽《寒山寺志》载,北宋王书张继诗石刻,史称寒山寺张继诗碑第一石。
王(1019-1085),成都华阳人,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在40岁左右刻此诗碑,然而这块石刻不知何时已亡佚。
为弥补这一缺憾,枫桥史迹陈列馆于1996年从台湾省傅斯年图书馆找到王书《宋赠太师魏国公韩公神道碑》,集字重刻王 所书《枫桥夜泊》诗碑,字体为正楷,介于颜柳书体之间,结构完美,字体雄健。
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1470-1559)书张继诗碑是第二石。
《寒山寺志》说“:文征明书张继诗残石,无年月,四行,行字不等,大草书,张继诗第二石也。
”文征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
他的字结构端正方整,笔法秀雅和劲,用笔挺健,天真烂漫,独步千古,可惜原碑残存仅有“落、啼、姑苏、征明”等“不及十字”。
寒山寺于1994年集文征明遗墨重刻诗碑,其风采几近原碑。
晚清大学者、书法家俞樾(1821—1907),号曲园,是现代作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著有276卷《春在堂全书》,博学工诗文书法,有江左之风。
光绪32年(1906),86岁的俞樾受江苏抚巡陈夔龙之命补书张继诗,刻成碑为张继诗碑第三石。
其章法稳贴,笔意圆浑,行书稳重端正,用笔顿挫沉着,字里行间无一字相连,但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是张继诗石刻原碑的代表作,它的拓迹流传很广。
影波依水话江南 徐志宏摄 评庄秋水新作《风入罗衣》 伊北 在70后一代醉心于俗世之物的女作家中,庄秋水应该算是把祖师奶奶张爱玲的单项爱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了吧。
一本同题散文集《更衣记》,成功演绎了张爱玲在单篇散文中未尽的传奇。
书出来之后,读者喜爱万分,大觉意犹未尽。
庄女士见此情状,不便负读者盼望,遂再接再厉,很快写出《风入罗衣》,重续服饰传奇。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入罗衣》也可以算是《更衣记》的续集。
庄秋水的服饰文化评点系列书,作为古典文化热潮中独特的一部分,可谓搔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女人的痒处。
自从流水线上的成衣,统治了全球大部分人的外包装后,人们就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特权。
即便是以光鲜靓丽为职业的女明星们,也经常会有撞衫的苦恼。
《红楼梦》里眼花缭乱的布绸缎绢,别说没见过,现代人估计听都没听过,轻烟罗和雀金裘这种纯手工的活计,早已成了绝响,电视剧上呈现的触目而 又俗艳的服饰,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于精致古代贵族生活的想象。
于是,庄秋水出现了。
庄女士把潘金莲称作“潘·包法利夫人”,侦探般地分析小说人物身上的一纱一布:沉香水纬罗的衫儿、白碾光绢挑纱裙儿、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儿,古典的繁复,她竟能抽丝剥茧般细细道来;《红楼梦》里的诡异绚烂的色彩,雨过天青、秋香色、松绿、银红,她也都能辨识得当。
她还懂得看衣识人:衣食住行,衣最重要,事关面子,影响人际外交,当年身穿毛青布大袖衫儿的潘金莲,一招能迷住西门庆,纯靠美色乎?庄女士拎得清,一语点破天机,毛青布不是普通布料呀,它从明代才有,而且是最好的蓝靛染料染就的,非常时尚呢。
经过庄女士这么一点拨,我等读者茅塞顿开,忽然想起张爱玲在《半生缘》中,也是特意安排第二女主角石翠芝,穿一身浆洗得非常独特的蓝布衫子,这才一把抓住了许叔惠的眼球———蓝靛色衬得人脱俗。
古代中国是最懂得享受的国度,也只有古代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为什么要在鞋垫上绣花、鞋帮子上绘图、在袄裤上无数道的滚边。
而身处浮躁而繁华的当代社会,能用一种近乎恋物的姿态,手握放大镜似地捧着古代服饰玩赏,发现一些颇有意趣的细节,并且能成功地向人们解释这样那样的花头都是什么,那这“玩家”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有品味的闲人了。
更难得是,她还能读出心得,没玩物丧志。
毕竟,玩赏所有的“古典”,都太需要静气,需要一种摩挲的耐性。
无法静下来现代人,格外需要庄女士这样的解读者了———她自有一种盛世人的雍容姿态,在一片呻吟的小女人散文群中突围出来,独出机杼。
就因为此,我很讨厌出版社为庄秋水做的介绍:这是一位曾与李欧梵、梁文道、王受之同版开栏的女专栏作家———根本不是一路文风,有什么好并列的呢?庄女士大概也不会以同这些知名人士并列为荣吧。
小说的字数 仲利民 有人曾以鲁迅先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为名,借此否定他的文学成就。
不过,这样的话题,除了让有识之士茶余饭后添了笑资外,没有半点撼动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位。
长篇小说固然可以洋洋洒洒地宏观描绘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由于字数的广阔,因而也写得更加波澜壮阔,然而,优秀的长篇 小说能否PK优秀的短篇小说是个伪命题,因为它们仅仅是字数的不同,完全没有谁比谁更站得更高的优势,何况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含量丰富,是现在许多所谓长篇小说巨大的容量也难以涵盖的事实。
倘若用字数多寡去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岂不让方家笑掉大牙? 不过,这样的伪命题还是有不少作家从内心里默认了。
写长篇小说的看不起写短篇小说的,认为那些短篇小说就像文学儿科一样有点幼稚,而写短篇小说的人不从作品的质量角度考虚,让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出彩,却有点直不起腰的感觉,发誓也要弄部长篇给别人看看。
我想起一位青年作家说的话:把踢足球的弄到篮球场上去打比赛,固然都是球赛,实在没有PK优劣的可能。
虽然长篇短篇都是小说,可长篇与短篇各有各的技术,写作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如果短篇小说写得尚且捉襟见肘,为了满足一点虚荣心去写长篇,那也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来。
吴昌硕画梅 包光潜 吴昌硕出身书香门弟,8岁作骈句,10岁持刀刻石。
后来家道败落,便发愤读书,中了秀才。
因喜欢文艺,如金石、书法、绘画等,决然放弃功名,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29岁居苏州,结识诸多海派艺林名宿,如饥似渴地阅历了大量名人墨迹,艺事大进。
50岁后在乡人的举荐下做了一月有余的江苏安东县令,后学五柳先生,弃官挂印而去。
吴昌硕说自己“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事实上他学画在而立之后。
之所以如此说来,只是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不甚满意而已。
其实也是客观评价。
他的优秀作品多为后三十年所作,恰如他画的老梅,大器晚成。
吴昌硕的画以泼墨花卉和蔬果为主要题材,兼顾人物山水。
他的作品公认为“重、拙、大”。
用笔沉着有力,没有浮滑轻飘之意,是为重;自然无巧却无斧斫之痕,稚气洋溢,天真一派,是为拙;气势磅礴,浑然大家,是为大。
吴昌硕画得最多的是梅花。
宋以降,画梅大家代有人出,如王冕、陈宪章、金农、汪士慎等,他们所画梅花各具特色,极尽梅花的清韵、艳丽、傲然、孤绝,寄托了画家的精神。
吴昌硕画梅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喜欢表现老梅,而且将老梅的铮铮铁骨与清香欲放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产生强烈视觉效果,有一种唤春归来、挣破冬的牢笼的感觉。
无论是《梅石图》、《梅花图》,还是《梅兰》、《红梅》等,无不如是。
吴昌硕画梅少有全树,也非千枝万蕊,他总是把环境和气氛省略到不能再添置一笔,有如特写镜头,既细致,又逼真,得梅花之真性灵,简直是划金刻石的杰作。
《梅石图》等多作于吴昌硕古稀之年,不止一幅。
其中一幅作于七十五岁,梅为主,石为客,交相辉映。
运用篆法,疏阔纵放,气势捭阖。
点点梅花,疏密有致,极富节奏之变。
焦墨枯笔,顺来逆去。
枝桠纵横,曲中求直,苍劲之极。
花以焦墨圈勾,精细而怒张,仿佛想要从枝上挣脱,凌空而去。
观者仿佛置身于月色轻笼、花影横斜的意境之中。
诗曰:“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
月明乱峰西,有客泛孤艇。
除却数卷书,尽载梅花影。
” 诗画珠联璧合,互补其境,令人悠然忘返。
题有此诗的《梅石图》、《梅花图》不下十幅,件件不同,各有千秋,充分体现了吴昌硕的爱梅情结和梅之精神。
从题画诗文也可以看出吴昌硕的文笔修养非同一般。
列举几例: 《梅花》题曰:寒香风吹下东碧,山虚水深人绝迹。
石壁矗天回千尺,梅花一枝和雪白。
和羹调鼎非救饥,置身高处犹待时。
冰心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 《月下梅花图》题曰:春夜梅花下看月,花瓣皆含月光,碎玉横空,香沁肌骨,但恨无翠羽啁啾和予新咏。
《梅花图》题曰:人遗纸数幅,光厚如茧,云得之东瀛。
或曰:此苔纸也。
醉后为梅花写照。
梅之状不一:秀丽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强如诤臣,离奇如侠,清逸如仙,寒瘦枯寂如不求闻达之匹士。
笔端欲具此众相亦大难事,唯任天机外行,似兴酣落笔,物我两忘,工拙不暇计及也。
不知大某山民挥之门外否?引为同调否?安得起而问之。
不论诗文,无不精神饱满,文气盎然,想象丰富,读来酣畅淋漓,充分地体现了吴昌硕的旧学功底、文学涵养和艺术才华。
文化的“浮躁” 杜浩 对美和善的价值、真实性、深刻性的要求,对高雅和创造的追求,因为具有了历史的情感、共同的记忆、公民的参与、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而体现出来的生活的宁静品质和精神氛围……这应该是文化的本质,但从目前我们的学术文化界、读书界和娱乐界所折射的一些现象来看,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浸染上或带上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病———浮躁。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钱文忠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商纣王”“翻案”的观点,是最近学术文化界争议的焦点。
不久前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中,钱文忠教授在解读《三字经》时,讲到殷商文化一节时语出惊人: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并自信而肯定地说,对“商纣王”的“翻案”,“我绝没有哗众取宠,我的观点言之有据”。
如此对我们传统中已经形成的历史认同、历史道德观和历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偏离、反抗和颠覆,自然引起众多的文化批评。
有的说,这严重地造成了历史人物评判标准的混乱,搞得纣王不像纣王,学术不像学术。
更有人尖锐指出,这种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在学术娱乐精神指导下对历史上的暴君的美化……所以,不论批评的是错误的历史认识也好,还是批评把娱乐化作为历史批评也好,反映出来的都是当今很是流行的一种学术文化浮躁风气。
作为一位研究历史文化的知识精英,他需要具有独特的、深刻的历史批判的眼光,但还更应该坚守文化精神和积极探索真理的精神,更应该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精神,可贵的求知的精神,更多一些求真务实的学术品质,更应该在文化心态上戒浮躁、少功利心,这既是对他的身份的要求,也是对历史、对传统、对文化的负责,对支持他的读者、观众的负责。
读书界的“浮躁”,让人必然要想到《中国不高兴》和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两部书。
《中国不高兴》出版以 后,对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倾向,也是充满了很多争议,但更多的批评者几乎一致地点到了这部书写作者的心态,书中思想观点,缺乏事实根据、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思辨,以及已经败坏了人们胃口的商业炒作手段等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作者自己浮躁,钻的又是社会上浮躁情绪的空子。
继港台先后出版了张爱玲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后,该书也在全国各地同步上市,首印量即达到了6位数,而在张爱玲的《小团圆》在内地尚未面世前,媒体上便评论说张爱玲《小团圆》是一部巅峰与麻烦之作,大谈性事争议不输《色戒》,而抢先读到小说的那些“张迷”更是直呼《小团圆》“好看得惊人”、“坦率得吓人”……结果,围绕着《小团圆》的出版,将读者再一次席卷进“张爱玲热”之中,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的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以张爱玲为核心的文化消费热。
这不是一种当今非常典型的、流行的图书出版和阅读的“浮躁”风吗! 文化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在一个文化厚实底蕴深沉的社会里,文化的所有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代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应该是社会和个人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道德、智能的积累的总和。
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
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但在流行的“浮躁”病的影响下,文化可以被炒作,被制作,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被当成了感性、欲望、官能之乐,变成了时尚流行的“消费品”,这在娱乐界几乎司空见惯。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因此,对我们目前文化中流行的“浮躁”,该是引起各方疗治的警觉了。
三 副刊部主编责任编辑:杨树彬电话:2356773邮箱:juhang8899@传真:2265261 文艺评论 文学是少数人的精品创作 许民彤 9月4日的《京华时报》“张洁称害怕作品被多数人喜欢”的一篇文化报道说:在为期五天的第十六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上,中国作家张洁与西班牙女作家帕乌拉和文学批评家路易斯举行了对话。
当西班牙同行询问张洁的书在国内畅销程度时,张洁讳莫如深:“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
”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
9月5日的《广州日报》“作协主席不及网络写手”的文化新闻说:盛大文学去年推出的“30省作协主席小说巡展”近日公布了结果,吉林省作协主席张笑天凭《沉沦与觉醒》获得一等奖,河南省作协副主席郑彦英屈居亚军,不过,这些传统作家在网上的魅力远不及一些网络写手,作协主席们的大作在网上的点击率,平均下来明显不及网络写手,点击率最高的张笑天也只有200多万,与动辄上千万点击率的网络小说相比,差距仍然不小。
这样两条文化消息告诉了我们什么?这就是,在如今的文学写作、文学阅读中,是存在着两种文学的阅读写作追求和趣味的。
这就是作家张洁说的,“我的书只给少数喜欢的人看,喜欢的人太多,我就害怕,这说明它是畅销书,而不是文学”。
这 是一种,坚持文学和阅读的独立、个性的原则和价值。
还有一种是,“动辄上千万点击率的网络小说”的写作和阅读现象,这是以文学的阅读写作趋向于时尚、流行和畅销为趣味标准和价值尺度,通过所谓的“点击率”等这样的技术手段来获得市场和大众的认同,“点击率”的数量,成了一个衡量文学阅读和写作的依据和标准。
这种文学阅读和写作的现象,让人很自然地想起萨特在评价文学阅读和写作现象时的一句名言———人类文化阅读历史上出现了两类文学:一类是虽不值一读,但拥有大量读者的文学;一类是无人去读的优秀文学……这种文学阅读写作的现象,过去存在,现在也存在,是“少数喜欢的”与“点击率”为王,那么,这是否也是未来的人们文学阅读写作的情形呢?张洁认为,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情,艺术家和匠人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张洁所说是大有深意的,作为一个作家,她应该是知道美国著名作家塞林格的创作生活的。
作为拥有数万年轻读者的《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作者塞林格,在声誉日隆之后,他并没有继续投读者所好,一本一本地频繁出版他的著作。
出版商知道他下笔成金,吁求他多多发表,他也不理。
他的唯一嗜好与乐趣便是写作,但不一定发表。
他曾解释,“不发表给了我可贵的安宁,使 我深感平静。
发表就会侵犯了我的私生则无意于这种自己的作品收获多少物质 活。
我爱好写作,但是我是为自己,为自己的繁华,内心唯一要紧的就是灵魂的意 的乐趣而写作”……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向、灵魂的内在态度,这种内在的本性是 塞林格是不为时尚、为畅销、为“搏点击不容扰乱的……这样的对文学阅读写作 率”写作。
说到底,这是需要有自己的文学的风格和精神,我们在莫言、苏童、韩寒, 的理想、写作的定力和精神信仰的。
此外,当然还有张洁等人身上看到了这种坚守。
我们熟知的米兰·昆德拉,在几十年写作“90后”在向“80后”成名作家讨教文学经 生涯中,只接受过一两次采访,平时,他除验时也发问“出书是为了出名还是因为对 了钓鱼和看书,就是写作,这不仅是高调文学的热爱?”可见,文学的理想和热爱, 低调的问题。
《百年孤独》的作者阿西亚·仍是一些人的一种信念精神。
马尔克斯,已经82岁了,一辈子坚持在宁 所以,文学的阅读写作,是为了“少数 静中生活、在宁静中写作,他的作品也因喜欢的”,做“少数人的事情”,还是相信 此有一种宁静的内心力量,由宁静和寂寞“点击率”为王?这是一个问题。
这时,我 汇聚成的力量沉淀在这些作家的作品中,们有必要重温一下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在 让我们阅读时常怀感动……这些世界著《读书与书籍》中所说,“无论什么时代, 名作家的为文学而安静写作的行为,不是都有两种不同的文艺,似乎各不相悖地进 真正诠释了什么是“文学从来都是少数人行着。
一种是真实的,另一种只不过是貌 的事情”? 似的东西。
前者成为不朽的文艺,作者纯 的确,在当今的消费主义文化占据人粹为文学而写作,他们的进行是严肃而静 们文化、精神生活的时代,文学的阅读和默的,然而非常缓慢。
在欧洲一世纪中所 写作,似乎都会受到这个时代精神和趣味产生的作品不过半打。
另一类作者,文章 的影响。
因此,对文学阅读写作,读者尤其是他们的衣食父母,但它们却能狂奔疾 是一个作家,必然要做出自己的选择的。
驰,受旁观者的欢呼鼓噪,每年送出无数 有的追求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的流行、畅的作品于市场上。
但在数年之后,不免令 销,作家自己成财富符号,上“富豪榜”。
人发生疑问:它们在哪里呢?它们以前那 至于有些网络文学写手,则毫不讳言相信煊赫的声誉在哪里呢?因此,我们可称后 “点击率”为王,自己的写作、收益和生者为流动性的文艺,前者为持久性的文 存,是为了“刷票”,为了“点击率”。
有的艺”,或许会得到一些启发吧! 说枫桥诗碑 韩望舒 到江苏苏州市,如不到寒山寺,则不算苏州客。
因为,寒山寺诗碑、钟声和苏州园林一样,那是姑苏的象征、苏州人的骄傲。
千年古刹寒山寺在苏州城西七里许的枫桥镇,始建于梁代天监初,原名妙利普明塔院,因唐贞观年间著名诗僧寒山子云游至此并主持,后人改名寒山寺。
这座寺曾多次毁于战火,现存景观为清末重建。
寺外,曲槛回廊,绿树黄墙,颇有“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寒山寺成为闻名中外的游览胜地,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诗大有关系。
唐天宝14年,安史之乱爆发,襄州(今湖北襄樊市)人张继在兵荒马乱中南下避乱,夜泊于寒山寺,触景生情,写下《枫桥夜泊》诗“: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有限文字将月落、乌啼、江枫、渔火、钟声组成一幅远近有序、动静分明、色彩逼真的江南风景画。
张继诗之书于碑,从北宋开始几乎每个朝代都有,然而由于年代久远及战火等原因,在寒山寺内保存最完好的仅为晚清俞樾所书之碑。
据清代叶昌炽《寒山寺志》载,北宋王书张继诗石刻,史称寒山寺张继诗碑第一石。
王(1019-1085),成都华阳人,官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他在40岁左右刻此诗碑,然而这块石刻不知何时已亡佚。
为弥补这一缺憾,枫桥史迹陈列馆于1996年从台湾省傅斯年图书馆找到王书《宋赠太师魏国公韩公神道碑》,集字重刻王 所书《枫桥夜泊》诗碑,字体为正楷,介于颜柳书体之间,结构完美,字体雄健。
明代大书画家文征明(1470-1559)书张继诗碑是第二石。
《寒山寺志》说“:文征明书张继诗残石,无年月,四行,行字不等,大草书,张继诗第二石也。
”文征明与沈周、唐寅、仇英合称“明四家”。
他的字结构端正方整,笔法秀雅和劲,用笔挺健,天真烂漫,独步千古,可惜原碑残存仅有“落、啼、姑苏、征明”等“不及十字”。
寒山寺于1994年集文征明遗墨重刻诗碑,其风采几近原碑。
晚清大学者、书法家俞樾(1821—1907),号曲园,是现代作家俞平伯的曾祖父,著有276卷《春在堂全书》,博学工诗文书法,有江左之风。
光绪32年(1906),86岁的俞樾受江苏抚巡陈夔龙之命补书张继诗,刻成碑为张继诗碑第三石。
其章法稳贴,笔意圆浑,行书稳重端正,用笔顿挫沉着,字里行间无一字相连,但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是张继诗石刻原碑的代表作,它的拓迹流传很广。
影波依水话江南 徐志宏摄 评庄秋水新作《风入罗衣》 伊北 在70后一代醉心于俗世之物的女作家中,庄秋水应该算是把祖师奶奶张爱玲的单项爱好,发挥到极致的一个了吧。
一本同题散文集《更衣记》,成功演绎了张爱玲在单篇散文中未尽的传奇。
书出来之后,读者喜爱万分,大觉意犹未尽。
庄女士见此情状,不便负读者盼望,遂再接再厉,很快写出《风入罗衣》,重续服饰传奇。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风入罗衣》也可以算是《更衣记》的续集。
庄秋水的服饰文化评点系列书,作为古典文化热潮中独特的一部分,可谓搔到了现代人,尤其是女人的痒处。
自从流水线上的成衣,统治了全球大部分人的外包装后,人们就失去了独一无二的特权。
即便是以光鲜靓丽为职业的女明星们,也经常会有撞衫的苦恼。
《红楼梦》里眼花缭乱的布绸缎绢,别说没见过,现代人估计听都没听过,轻烟罗和雀金裘这种纯手工的活计,早已成了绝响,电视剧上呈现的触目而 又俗艳的服饰,已经不能满足现代人对于精致古代贵族生活的想象。
于是,庄秋水出现了。
庄女士把潘金莲称作“潘·包法利夫人”,侦探般地分析小说人物身上的一纱一布:沉香水纬罗的衫儿、白碾光绢挑纱裙儿、大红缎子白绫高底鞋儿,古典的繁复,她竟能抽丝剥茧般细细道来;《红楼梦》里的诡异绚烂的色彩,雨过天青、秋香色、松绿、银红,她也都能辨识得当。
她还懂得看衣识人:衣食住行,衣最重要,事关面子,影响人际外交,当年身穿毛青布大袖衫儿的潘金莲,一招能迷住西门庆,纯靠美色乎?庄女士拎得清,一语点破天机,毛青布不是普通布料呀,它从明代才有,而且是最好的蓝靛染料染就的,非常时尚呢。
经过庄女士这么一点拨,我等读者茅塞顿开,忽然想起张爱玲在《半生缘》中,也是特意安排第二女主角石翠芝,穿一身浆洗得非常独特的蓝布衫子,这才一把抓住了许叔惠的眼球———蓝靛色衬得人脱俗。
古代中国是最懂得享受的国度,也只有古代的中国人,才能懂得为什么要在鞋垫上绣花、鞋帮子上绘图、在袄裤上无数道的滚边。
而身处浮躁而繁华的当代社会,能用一种近乎恋物的姿态,手握放大镜似地捧着古代服饰玩赏,发现一些颇有意趣的细节,并且能成功地向人们解释这样那样的花头都是什么,那这“玩家”一定是位了不起的、有品味的闲人了。
更难得是,她还能读出心得,没玩物丧志。
毕竟,玩赏所有的“古典”,都太需要静气,需要一种摩挲的耐性。
无法静下来现代人,格外需要庄女士这样的解读者了———她自有一种盛世人的雍容姿态,在一片呻吟的小女人散文群中突围出来,独出机杼。
就因为此,我很讨厌出版社为庄秋水做的介绍:这是一位曾与李欧梵、梁文道、王受之同版开栏的女专栏作家———根本不是一路文风,有什么好并列的呢?庄女士大概也不会以同这些知名人士并列为荣吧。
小说的字数 仲利民 有人曾以鲁迅先生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为名,借此否定他的文学成就。
不过,这样的话题,除了让有识之士茶余饭后添了笑资外,没有半点撼动鲁迅先生在中国文学的地位。
长篇小说固然可以洋洋洒洒地宏观描绘大千世界的形形色色,由于字数的广阔,因而也写得更加波澜壮阔,然而,优秀的长篇 小说能否PK优秀的短篇小说是个伪命题,因为它们仅仅是字数的不同,完全没有谁比谁更站得更高的优势,何况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含量丰富,是现在许多所谓长篇小说巨大的容量也难以涵盖的事实。
倘若用字数多寡去否定鲁迅的文学成就,岂不让方家笑掉大牙? 不过,这样的伪命题还是有不少作家从内心里默认了。
写长篇小说的看不起写短篇小说的,认为那些短篇小说就像文学儿科一样有点幼稚,而写短篇小说的人不从作品的质量角度考虚,让自己的作品越写越出彩,却有点直不起腰的感觉,发誓也要弄部长篇给别人看看。
我想起一位青年作家说的话:把踢足球的弄到篮球场上去打比赛,固然都是球赛,实在没有PK优劣的可能。
虽然长篇短篇都是小说,可长篇与短篇各有各的技术,写作的表现方式也不尽相同。
如果短篇小说写得尚且捉襟见肘,为了满足一点虚荣心去写长篇,那也不会写出什么好作品来。
吴昌硕画梅 包光潜 吴昌硕出身书香门弟,8岁作骈句,10岁持刀刻石。
后来家道败落,便发愤读书,中了秀才。
因喜欢文艺,如金石、书法、绘画等,决然放弃功名,不再参加科举考试。
29岁居苏州,结识诸多海派艺林名宿,如饥似渴地阅历了大量名人墨迹,艺事大进。
50岁后在乡人的举荐下做了一月有余的江苏安东县令,后学五柳先生,弃官挂印而去。
吴昌硕说自己“三十学诗,五十学画”,但事实上他学画在而立之后。
之所以如此说来,只是对自己的早期作品不甚满意而已。
其实也是客观评价。
他的优秀作品多为后三十年所作,恰如他画的老梅,大器晚成。
吴昌硕的画以泼墨花卉和蔬果为主要题材,兼顾人物山水。
他的作品公认为“重、拙、大”。
用笔沉着有力,没有浮滑轻飘之意,是为重;自然无巧却无斧斫之痕,稚气洋溢,天真一派,是为拙;气势磅礴,浑然大家,是为大。
吴昌硕画得最多的是梅花。
宋以降,画梅大家代有人出,如王冕、陈宪章、金农、汪士慎等,他们所画梅花各具特色,极尽梅花的清韵、艳丽、傲然、孤绝,寄托了画家的精神。
吴昌硕画梅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喜欢表现老梅,而且将老梅的铮铮铁骨与清香欲放的花朵形成鲜明对比,产生强烈视觉效果,有一种唤春归来、挣破冬的牢笼的感觉。
无论是《梅石图》、《梅花图》,还是《梅兰》、《红梅》等,无不如是。
吴昌硕画梅少有全树,也非千枝万蕊,他总是把环境和气氛省略到不能再添置一笔,有如特写镜头,既细致,又逼真,得梅花之真性灵,简直是划金刻石的杰作。
《梅石图》等多作于吴昌硕古稀之年,不止一幅。
其中一幅作于七十五岁,梅为主,石为客,交相辉映。
运用篆法,疏阔纵放,气势捭阖。
点点梅花,疏密有致,极富节奏之变。
焦墨枯笔,顺来逆去。
枝桠纵横,曲中求直,苍劲之极。
花以焦墨圈勾,精细而怒张,仿佛想要从枝上挣脱,凌空而去。
观者仿佛置身于月色轻笼、花影横斜的意境之中。
诗曰:“梅溪水平桥,乌山睡初醒。
月明乱峰西,有客泛孤艇。
除却数卷书,尽载梅花影。
” 诗画珠联璧合,互补其境,令人悠然忘返。
题有此诗的《梅石图》、《梅花图》不下十幅,件件不同,各有千秋,充分体现了吴昌硕的爱梅情结和梅之精神。
从题画诗文也可以看出吴昌硕的文笔修养非同一般。
列举几例: 《梅花》题曰:寒香风吹下东碧,山虚水深人绝迹。
石壁矗天回千尺,梅花一枝和雪白。
和羹调鼎非救饥,置身高处犹待时。
冰心铁骨绝世姿,世间桃李安得知? 《月下梅花图》题曰:春夜梅花下看月,花瓣皆含月光,碎玉横空,香沁肌骨,但恨无翠羽啁啾和予新咏。
《梅花图》题曰:人遗纸数幅,光厚如茧,云得之东瀛。
或曰:此苔纸也。
醉后为梅花写照。
梅之状不一:秀丽如美人,孤冷如老衲,屈强如诤臣,离奇如侠,清逸如仙,寒瘦枯寂如不求闻达之匹士。
笔端欲具此众相亦大难事,唯任天机外行,似兴酣落笔,物我两忘,工拙不暇计及也。
不知大某山民挥之门外否?引为同调否?安得起而问之。
不论诗文,无不精神饱满,文气盎然,想象丰富,读来酣畅淋漓,充分地体现了吴昌硕的旧学功底、文学涵养和艺术才华。
文化的“浮躁” 杜浩 对美和善的价值、真实性、深刻性的要求,对高雅和创造的追求,因为具有了历史的情感、共同的记忆、公民的参与、人文的细致、哲学的深思、文明世界人与人之间不能或缺的婉转和体贴而体现出来的生活的宁静品质和精神氛围……这应该是文化的本质,但从目前我们的学术文化界、读书界和娱乐界所折射的一些现象来看,我们的文化正在被浸染上或带上这个时代的一种流行病———浮躁。
复旦大学历史教授钱文忠的最新研究成果为“商纣王”“翻案”的观点,是最近学术文化界争议的焦点。
不久前播出的《百家讲坛》节目中,钱文忠教授在解读《三字经》时,讲到殷商文化一节时语出惊人:两千多年来被冠以“暴君”的商纣王属于历史最悠久的“冤案”,实际上商纣王绝对文武双全、功勋卓著……并自信而肯定地说,对“商纣王”的“翻案”,“我绝没有哗众取宠,我的观点言之有据”。
如此对我们传统中已经形成的历史认同、历史道德观和历史文化所表现出来的偏离、反抗和颠覆,自然引起众多的文化批评。
有的说,这严重地造成了历史人物评判标准的混乱,搞得纣王不像纣王,学术不像学术。
更有人尖锐指出,这种学术观点的提出,是在学术娱乐精神指导下对历史上的暴君的美化……所以,不论批评的是错误的历史认识也好,还是批评把娱乐化作为历史批评也好,反映出来的都是当今很是流行的一种学术文化浮躁风气。
作为一位研究历史文化的知识精英,他需要具有独特的、深刻的历史批判的眼光,但还更应该坚守文化精神和积极探索真理的精神,更应该表现出严谨的学术精神,可贵的求知的精神,更多一些求真务实的学术品质,更应该在文化心态上戒浮躁、少功利心,这既是对他的身份的要求,也是对历史、对传统、对文化的负责,对支持他的读者、观众的负责。
读书界的“浮躁”,让人必然要想到《中国不高兴》和张爱玲的《小团圆》这两部书。
《中国不高兴》出版以 后,对其所表现的“民族主义”情绪倾向,也是充满了很多争议,但更多的批评者几乎一致地点到了这部书写作者的心态,书中思想观点,缺乏事实根据、理性思维和严密的逻辑思辨,以及已经败坏了人们胃口的商业炒作手段等表现出来的问题,是作者自己浮躁,钻的又是社会上浮躁情绪的空子。
继港台先后出版了张爱玲带有自传性质的长篇小说遗作《小团圆》后,该书也在全国各地同步上市,首印量即达到了6位数,而在张爱玲的《小团圆》在内地尚未面世前,媒体上便评论说张爱玲《小团圆》是一部巅峰与麻烦之作,大谈性事争议不输《色戒》,而抢先读到小说的那些“张迷”更是直呼《小团圆》“好看得惊人”、“坦率得吓人”……结果,围绕着《小团圆》的出版,将读者再一次席卷进“张爱玲热”之中,而且,这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文学研究与文学欣赏的范围,成为了一场较大规模的以张爱玲为核心的文化消费热。
这不是一种当今非常典型的、流行的图书出版和阅读的“浮躁”风吗! 文化的本质精神是什么?在一个文化厚实底蕴深沉的社会里,文化的所有的表现形式,应该是代代累积沉淀下来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应该是社会和个人激发的创造力和想像力,思想的内涵和美学的品位,道德、智能的积累的总和。
真正的文化,应该是对“价值”和“秩序”有所坚持。
抵抗的力量所源,就是文化。
但在流行的“浮躁”病的影响下,文化可以被炒作,被制作,文化带上了浓厚的商业色彩,被当成了感性、欲望、官能之乐,变成了时尚流行的“消费品”,这在娱乐界几乎司空见惯。
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心灵和大脑,它的思想有多么深厚、它的想像力有多么活泼、创意有多么灿烂奔放、它自我挑战、自我超越的企图心有多么旺盛,彻底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真实国力和它的未来。
因此,对我们目前文化中流行的“浮躁”,该是引起各方疗治的警觉了。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下一篇学生用课件,葛华才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