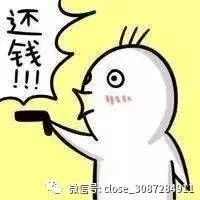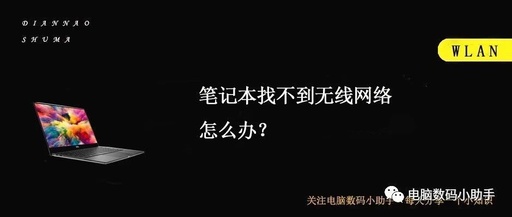2022年6月26日星期日
笔会
策划/舒明责任编辑/吴东昆谢娟whbhb@
7 禅心不起捧花归 徐建融 群芳谱上,百花争艳。
所争者,无非形、色、香,得一即为名品,或有兼二者,却罕有三美并称的。
栀子花形如拳而玲珑,花色如玉而皎洁,花香如冽而馥郁,正是难能稀有地集三美 色为空,不如见色受色、见空受空,于栀子专赏其今日之清纯靓丽,无论其明日之芜秽萎绝。
就像越是彻悟到“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就越应该加倍 我之留意保存自己的诗稿,应该是在1993年为谢老搜集、编辑《壮暮堂诗钞》之后。
凭记忆回想了之前的所作,只能到七八十年代;此后的吟诵也尽可能留下了底稿。
这阕《满庭芳· 止了。
古人咏栀子的诗词甚多且美,但 画栀子的图绘相对而言却并不多见。
我最早见到的以栀子为画材,是谢老写“芭蕉叶大栀子肥”的诗意,觉得花 太阳转到西山窗下,土屋里浮起几道晃眼的光,映得墙上的旧报纸也摇动起来。
天越发暗了。
我趴在窗台上,望着半开的院门,默默流泪。
姥姥上炕来,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拍着背,哼哼呀呀地唱起来。
一直唱到我迷迷糊糊,姥姥才低声对旁边的小舅妈说,这孩子看来是真想家了,明天送她回吧。
多年前,一个春日的黄昏,我牵着姥姥的手,穿行在刚刚长出小苗的田野。
姥姥穿着灰布褂子,侧襟盘扣,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用柔软的黑丝网包住,身上传来好闻的米糠的气息。
田野空荡荡的,白杨树在风中轻轻摆动,空气中传来土地新鲜的芳香,一两个农人赶着马车经过,留下一串单调缓慢的车轮声。
以后无数次,我穿过这片田野去往姥 穿过田野 于一身的珍葩之
一。
但它在众香国中的席位,却远不及梅花、牡丹、芍药、海棠、兰花、荷花、桂花、菊花、芙蓉、水仙等。
原因何在呢?我想,当与它开放后衰萎也速而且狼藉也甚有相当的关系。
当梅雨方生,一片江南霏暗之中,油绿浓翠的栀子叶丛中,一夜之间绽放出朵朵琼瑶般的花头,上面还带着露珠,晶莹剔透,香气袭人,令人神清气爽,烦闷涤尽。
然而,不过两天的时间,清纯的靓丽,忽然便成了一坨坨污秽的形色,佛头着粪般颓废委顿地散落在葱碧的枝头叶间,夹杂在新放的荳蔻年华中,久久不落。
相比于其他花卉凋谢时的香消玉殒之美,不免大煞风景。
栀子有好几个别名,其中最典雅的一个叫“薝蔔”,系梵文的音译;亦作旃簛迦、赡博迦,一看便是外来语,远没有薝蔔来得“信、达、雅”。
据《一切经音义》,佛教以十万香花作供养,尤以五树六花中的薝蔔香色殊胜,无比稀有,不可思议。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东晋人便把原产我国的栀子认作是西域的薝蔔。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木”有云:“陶贞白言,栀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
相传即西域薝蔔花也。
”至明方以智《通雅》,始以为非是。
今天的植物学家进一步考证出薝蔔实为木兰科的黄兰,与茜草科的栀子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作诗作画,于栀子仍喜欢以“薝蔔”名之而知错不改。
这不仅是为 了承续前贤千百年来的诗画传统,更因为栀子的从绽放到凋谢,使我联想起《释迦谱》中所讲到的一则故事:释迦修道将成,魔王波旬惧其成道后的法力,便派鬼卒明火执仗向其发动进攻,释迦不为所动,武力尽化灰烬;又遣三个美貌的女儿前往引诱,欲以姿容颜色“乱其净行”: 女诣菩萨(释迦),绮语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嫈嫇细视,现其陛脚,露其手臂,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
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术,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逾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
”菩萨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体虽好,而行为不端,革囊盛臭。
尔来何为?去!吾不用。
”其魔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
这一故事,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的壁画、浮雕中多有表现,名为“降魔变”。
以莫高窟428窟的北周壁画为例,释迦结跏趺坐于画面中央,结降魔印,安忍不动,默如雷霆;上方为群魔乱舞,张弓、搭箭、持枪、抡斧、执蛇,气势汹汹地向佛扑去;下方左侧为三魔女青春靓丽向佛献媚,右侧已变成三个丑婆,“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削骨立,腹大如鼓”,自惭形秽。
这刹那之间的美丑衰变,与栀子花的由极清纯而极污秽,不正相吻合吗?则即使栀子不是薝蔔花,也应是天魔女,与佛教的说教是脱不了干系的。
有了这一认识,再来审美栀子的香馥。
恍然回味到它有别于其他花卉,包括同样浓烈的桂花的香而清,而有一种类似于巴黎香水般香而腻的异域风情。
我曾于星洲观赏洋兰,惊艳之余,以为国兰之美如窈窕淑女而妩媚动人,洋兰之美则如浪荡胡姬而狐媚迷人。
栀子的形色,清真雅正,所体认的是典型的中华审美,但它的香馥,浓烈郁腻,总使人觉得像是异域的浪漫风情。
“花气熏人欲破禅”。
栀子还有一个别名叫“禅友”,它的含义,应该正是“破禅最是栀子花”吧?栀子的玲珑之形、冰玉之色、馥郁之香,兼清纯与狐媚,“我见犹怜”;则即使它明日便狼藉地凋零委顿,“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曲江》),又何妨我今天及时的赏心悦目呢? 佛教的一切“受想行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至“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所以,释迦视魔女的美色为老妪的污秽而“去”之“不用”。
但我辈凡夫俗子,执 地珍惜眼前的“欢乐”、“少壮”一样。
自古以来的诗人、画家,于栀子的 歌咏、描绘,无不着眼于它的明丽而无视其芜秽,盖可以概见之矣。
我于栀子的受想行识,始于少年时代。
当时的农村,基本上没有种植观赏花卉的,但远村有一座老宅,天井的墙角有一株几十年的栀子,高达2米,茂密得很。
每到梅雨季节,便绽放出冰花朵朵,给闷湿的空气带来清新凉爽。
今天,每一个花园社区的绿化多有以栀子为主要植花的,而且有高株、矮株、重瓣、单瓣的多个品种,成为海棠、紫藤等春花以后主要的赏花景观。
接下来,便是赏荷了;之后,赏桂、赏菊、赏梅、赏山茶,一年四季,花事无有间断。
任一小区的空间,简直“空即是色”。
观花寻诗,读诗识花,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栀子的别名叫薝蔔,尤对宋朱淑真的“一根曾寄小峰峦,薝蔔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向月中看”印象深刻,诚所谓“色空空色,明月前身”。
同时也学着自己做,不过率汰胡诌,打油自喜,覆酱嫌粗。
上世纪70年代后知道了一点格律的知识,慢慢地开始进入诗词的门户,但随写随弃,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的。
因为,当时的写诗只是为了一时的兴趣,包括咏栀子在内,犹如“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所以乘兴而写,兴尽而弃,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来会同诗画打交道并被人误认为小有成就。
就像樱花并不是为了凋谢时的美丽而绽放,栀子更不会因为凋谢时的委顿而不绽放。
每有研究齐白石的专家讲到,白石老人的阔笔花卉配以工细草虫,是因为预见到晚年后会享大名,而届时画不出工细的形象了,所以趁年轻时画了许多虫子却不配景,留待晚年后补成。
但大多数人,事实上是很难预测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和成就的,所以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为几十年后的“大成”保存今天的“少作”资料。
不仅卑微如我,当年在农村种地时根本没有妄想过有一天会跳出“农门”,涉事高雅的文艺,就是谢稚柳先生,从小生活在诗人圈里,他早年所写的诗词,也多没有保存下来。
众所周知,谢老的诗词是从李义山、李长吉起手入门的。
但今天所见,纯粹是宋人的平实风格,于二李的谲丽几乎毫无瓜葛。
原来,我们所见之诗都是抗战避兵重庆之后,尤其是维新以来的作品,谢老因沈尹默先生的规劝而转向了宋人。
然而,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部分散佚民间的谢老《词稿》,以陈老莲体的小行楷誊录于“调啸阁”诗笺上,多为40年代之前的作品。
一种呕心沥血、迷离瑰丽的穷工极妍,与后来的“不耐细究”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当年的谢老并没有“敝帚自珍”,以致后来陆续整理《鱼饮诗稿》《甲丁诗词》《壮暮堂诗词》《壮暮堂诗钞》时,都没能收集到这部分真正体现其学二李风格的佳作。
自题栀子写生小卷》,应该便是在这前后所填: 一片江南,绵绵昼夜,梅雨看洗青黄。
更谁知有,薝蔔出银潢。
暑色霪霪搓白,三六出、弄玉斯降。
凝香雪,鼻端消息,渐冽愈迷茫。
琳琅。
初霁后,天凉如水,月影东墙。
照空色无形,馥起浪浪。
且向旃檀海里,快参透、抛却皮囊。
花微笑,何须煮酒,自在渡慈航。
词中的“三六出”,缘于古诗词中的“六出灵葩”。
刚读到时,颇有疑惑。
因为,“六出”的花朵,通常为球根类的草本,如水仙、萱草、百合等;栀子为常绿灌木,花瓣甚夥,虽未曾细数,但当不止六出。
后来一数,为十八瓣,乃暗讥古人格物的粗疏。
转念一想,或许不是为花写实,而是因其花色如雪,以雪花六出故拟之。
又后来,见到矮株单瓣的栀子,果然是六出!再检重瓣者,原来十八瓣分为三层,逐层绽放,每层为六出!乃知古人审物不苟,反是我走马观花、浅尝辄 头之美如荷花,于是也开始画栀子。
但当时的栀子种植并不普遍,连远村老宅中的那一株也被砍了,所以对花写生是要多方寻访、骑自行车前往的。
后来又见到宋人的、钱选的、陈淳的栀子,尽管图片印得很不清晰,还是认真地作对本临摹。
新世纪后,搬入园林化的小区,年年梅雨,都浸淫在薝蔔香中;古画的印刷,更仅“下真迹一等”,画栀子才渐入佳境。
双勾的,点厾的,设色的,水墨的,绢本的,纸本的,熟宣的,生宣的……不拘一格,体会日深而境界稍进,致使栀子,成了我最常画的花卉素材之
一。
庶使冰清玉洁的空色生香,破禅、悟禅,损亦友,益亦友,随缘而无执。
包括栀子在内,我的画上多题有诗文,倒不是因为志存风雅,而是因为性之所好,欲听还看两无厌,故将颜色染香音。
而唐释皎然的《答李季兰》诗,尤得我于栀子的画胆诗心: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
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国画)徐建融 姥家。
可在姥姥去世后的二十年间,我再也没有走上这条路。
但姥姥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有时是委托我照顾她的女儿,有时是喊我过去吃饭,更多时,她像生前一样朦朦胧胧微笑着不说话。
我一阵惊喜,以为她还在世,醒来后却陷入恍惚。
我去年春节才终于知道她的名字——凤芹。
若是有文化的大户人家,这名字应写作凤琴,凤落琴弦,抑或风芩,风中芩草,然而姥姥只是苦出身,自然也只能写作凤芹。
这名字在故乡东大荒,野草一样遍地都是。
姥姥没读过书,一字不识,后来却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在村里也颇有威望。
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兄弟反目,人们习惯来找她。
“老李大姑”到场,一通情理摆下来,人人服气,怨气、怒气也就平息了大半。
村里有一地痞,常年在外偷盗勒索、打架斗殴。
这年地痞从外乡回来,不时在夜里挨家挨户上门讨钱,村里人既恨且惧,不敢得罪,只好给钱免灾。
姥姥却坚决不肯。
她将一柄小斧头磨得锋利,入夜便塞在枕下。
一夜,地痞果然上门。
未等姥姥手中斧头举起,地痞抢先一步上前,屋内空气瞬间凝滞。
不想地痞却递上礼物,脸上堆笑说,我来看看老李大姑,你是我最敬重的人。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姥姥却冷下一张脸,让他马上走,别弄脏了地。
地痞讪讪离开,姥姥随之把他带来的糕点盒子直接扔出门外。
姥姥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1947年,通辽暴发鼠疫,死了上万人,有的甚至全家死绝。
在那场巨大的灾难中,姥姥的父母也双双感染,没几天就撒手人寰。
姥姥有两个哥哥,已经成家立户。
姥姥那时只有十七岁,放到现在才读高
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在那个饥荒遍地瘟疫横行的年月,养大了五个弟妹。
那时她最小的妹妹才三岁,最小的弟弟也不过五岁。
那段岁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苦熬,姥姥从不说及。
我也不过听母亲说起零星的只言片语。
说是缺吃少穿,姥姥把旧袜子上的绒线拆下来,捻成线绳,给小弟弟做了一双鞋。
小弟弟有一次去河边,舍不得把鞋弄脏,就脱下来藏进芦苇丛。
没想到,回来时怎么也找不到,这双珍贵的鞋丢了。
小弟弟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抱住姐姐,两个人一起哭。
我惟一一次见到姥姥流泪,是有一回小姨姥跟姥姥闹别扭。
姥姥说,你怎么还跟姐姐记仇呢,咱们从小没妈,你是姐姐抱着长大的,就差吃姐姐的奶了呀!小姨姥闻言搂住姥姥,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哭了许久。
姥姥二十岁时嫁给姥爷。
姥爷国高毕业,读了许多线装书,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有着读书人的耿直与不谙世道。
姥爷家是一个大家族,姥姥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妈出生时,因是女孩,按家规不分口粮,男丁才可以。
姥姥抱着孩子去找当家人,据理力争,终于在年底多分了一袋高粱。
姥姥奶水不足,我妈饿得面黄肌瘦。
姥姥把高粱米用水煮至半熟,在嘴里反复嚼出米浆,然后用纱布过滤出汤汁,喂给 周 静,去姥姥家 我妈。
高粱米不能完全煮熟,否则嚼不出浆来。
姥姥在月子里天天嚼着半熟的硬米粒,极大地损害了牙齿,以至于后来她不到四十岁,满口牙就掉光了。
可能是幼小时候的遭际,我妈成年后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情,严谨内向,五十岁之前从不对我们拥抱、亲吻,耻于表达爱意。
当年爷爷派我爸前去姥姥家给我妈下聘礼时,据说我爸一眼看中了活泼开朗的二姨,隐隐露出后悔之意。
可是姥姥干脆挑明,一句话镇住了我爸——老大没出阁,没可能考虑老
二。
一物降一物。
爷爷和姥姥,是我那骄傲的爸爸在这世上仅有的两个敬畏的人。
我常常想起姥姥,她小个儿,微丰的身材,哪里就有那么多的能量?姥姥有四个女婿,我爸和二姨父是村干部,能说会道,三姨父是农民,只知干活,性情木讷,小姨父在镇里做工,家境也很艰难。
姥姥从不对我爸和二姨父特殊招待,反倒是对三姨父和小姨父格外高看一眼,从不让他俩在家族聚会时有丝毫冷落。
几个女婿过年聚在一起打牌时,姥姥悄悄塞给三姨父和小姨父零钱,以免他们当众难堪。
姥姥一生,赢得了她所有儿女的敬重。
姥姥共有十五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奇怪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姥姥最疼爱的那个。
这是属于姥姥独有的慈祥,她总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哪怕是一个顽劣的孩子。
至今我还记得,冬天的夜晚,姥姥把火炕烧得暖暖的,让我趴在热被窝里看电视,我总会在被窝里发现一两个平日难得吃到的苹果,有时是桔子…… 多年后我常常想起姥姥,每每不自觉对比,姥姥在我这个年龄时,已经做过哪些事情,如果姥姥遇到我眼前的困境,会怎么办?姥姥多么有智慧啊,她是我的榜样,有时甚至是我冥冥之中的人生导师。
是的,我觉得姥姥一定还在,在这世上虚无的一角,在扯不断的时空深处。
然而我这一生,再也回不到多年前那个黄昏,我满心欢喜地跟在她身后,穿过春天的田野,目睹整个春天带着慈悲,给一个孩子留下她后来苦苦追寻而再也不可得的,酸楚的甜蜜。
1993年夏天,我在常州一家服装厂打工。
常州《翠苑》杂志社开了一个作家培训班,对,就是这么牛皮哄哄,一帮并不会写作的家伙发一个广告,把文学爱好者们召集到一起,每个人交80块钱,来学习如何写作,或者学习如何做一个作家。
培训班有二十多人,有医生,京剧爱好者,中学教师……以及像我这样的打工人。
头一天报到,在一间会议室,沙发上坐着一个姑娘,皮肤略黑,小脸略扁,眉梢吊起来,是典型的丹凤眼,乌黑的长发,穿一件V领花色连衣裙,露出两块锁骨。
她在写收据,登记学员名单。
她叫周洁茹。
有一些人,天生是冷淡的,第一次见,她没笑;后来见,她也没有笑过,所以我不记得她笑的样子,如果让我寻找一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是如何的格格不入,指的大约是她,虽然在我许多朋友那里,格格不入的是我,事实也是,这二十多个人后来一直走 微 ﹃文 信公 汇 众 笔会 号﹄ 可是再没有见过。
后来听说她离 我们的青春 开了常州。
2000年的时候,文化宫地下广场摆 着《小妖的网》《糖》和《上海宝贝》,那时的书,可以随便翻,不像现在的书,大多用薄膜套住,除了皮,你什么也看不 到。
我对她的故事感到陌生,也感到不 李凤群 陌生。
她就是这样的。
她的1993年的姿势已经预言了她的文学和生活。
那 时“美女作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办 公室阅览室几本周刊上都有那一拨人 动,但大家并不十分喜欢我,一则,因为在我初中同学家的客厅里,我看到她的的访问,大幅照片和她们的作品。
我鲁莽,好出风头,喜欢与人争辩,另海报,觉得她没有所谓的瓜子脸,双眼 她给人感觉很疼痛,很别扭,不自 则,因为我穷,请不起大家吃茶点。
大皮,大眼睛,但我盯着海报上她的脸,那在地活着,但这种疼痛别扭不自在的姿 约有这个因素。
么美,我久久地看着,迷惑不解。
态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呆呆地摩 但周洁茹的格格不入,则不是语 大家当面或是私下里都对周洁茹挲着她的书,我没有买。
那天下午我回 言能形容的。
外面请专家来讲课,或十分客气,几乎算是宠溺,不光是我,其到单位,告诉一个同事我认识周洁茹。
者组织讨论的时候,她也会在那里。
他人也不曾与她有过多的接触,我想可那是一个满脸痘印的文学男青年,他掩 但她几乎不说话,不是不与我说话,也能因为她当时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
饰着他的不信任,说,那你也可以写
一 不与其他人说话。
她坐在那里,仿佛 再次见面是1996年,那时我已经部啊,像她一样出名。
人在那里,但心不知道在哪里。
有时在常州教育学院完成学业,交往了一个 我真的开始写。
如果没有她,以及 候也会抬头,露出眼梢,但她的眼神很帅气的男朋友。
有一次,我和男朋友“美女作家”们在常州文化宫集体亮相 从不落在某处,尤其不与人对视,即逛新华书店,也是常州仅有的几家书店的震撼,我也许不会写下第一部小说。
使她与你对视了,也仿佛没有在看之
一。
几乎可说是毫不意外地,我们在所以于我,她和她的《小妖的网》有不
一 你,简直是目空一切。
她的下颌骨略小说书区域碰到了。
她戴一副吊着链般的意义。
我觉得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宽,下巴像张爱玲那张经典的相片一子的眼镜,头发扎在脑后,比我第一次如果有一座桥梁,或者有一个前方,那 样略略抬起来,也是那样的不可冒见到她时成熟太多了。
我很震惊。
我她就是。
犯。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但喊了她的名字。
她已经不记得我了。
又过了一两年,我们培训班这一拨 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相信她我提醒了她培训班的事,她表示认出来人在我家聚会。
有人提到她的近况,说 不知道我是谁,我也相信她不记得其了。
她说,难怪在这里遇到你。
这几乎她回来了。
其实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人是谁。
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就是她的特色。
她的特色在1993年就又从哪里回来了,但我们趁机给她打 个人就算没有善意,也没有一丝恶意,定住了。
如果我遇到了故人,通常我们电话。
电话接通了。
我告诉她,我已 虽然十分的有距离感,但她的模样和会更夸张,更热烈,更缅怀,或者更冷经开始写长篇。
那很好啊,她说,继 个性在我看来,是十分的非凡,桀骜不淡。
但周洁茹就是这样。
她的方式在续。
不热情不坚持,如果你见过1993 驯到脱离了常规。
1993年就是这样,所以1996年也是这年的她,就不能说她过于冷淡,她让电 就如当年我看到山口百惠的年代,样。
我们说了再见。
话里的时间像水一样,任它淌过去。
然后我们说了再见。
我开始写我的小说,过了两年,小 说出版,可是从来没有摆到过文化宫地下广场的摊位上,直到文化宫地下广场消失不见也没有。
后来我听说过她。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告诉我,周洁茹在香港。
她过得很不容易。
大意是她每天要搭很长时间的车送儿女去上学。
那不像她,我于是怀疑地看着那个朋友,但没有追根究底。
我不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相反,我是喜欢不懂装懂的人。
又过去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在微信上我接到一个好友邀请:周洁茹,作为《香港文学》的主编,来约稿。
我以为她来跟我叙旧,可是她完全想不起来——她因为戴瑶琴教授的推荐加我,她就是来约稿的。
然后就是朋友圈里的周洁茹。
我偶尔看她的小说,她养了一双可爱、阳光的儿女,她编《香港文学》,还勤奋地写,清单拉出来,吓我一跳,她一年写三十个短篇。
坦白说,她的小说似乎不是我的菜,我碰到就读一些,不碰到也就算了,但我对她这个人,充满了,充满了旧情。
充满了敬意,充满了怜爱。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2020年,我回南京,在家里翻旧照片,翻到一张,她坐在沙发上,我如获至宝,立刻发给她,她认出了自己,然后问我:哪个是你? 那个背影。
穿着白色T恤的背影。
那件衣服我记得,料子厚而不透气,我因为年轻壮实而时常在流汗……但那是我们的青春,被好心人定格在那里,它使我酸楚。
7 禅心不起捧花归 徐建融 群芳谱上,百花争艳。
所争者,无非形、色、香,得一即为名品,或有兼二者,却罕有三美并称的。
栀子花形如拳而玲珑,花色如玉而皎洁,花香如冽而馥郁,正是难能稀有地集三美 色为空,不如见色受色、见空受空,于栀子专赏其今日之清纯靓丽,无论其明日之芜秽萎绝。
就像越是彻悟到“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汉武帝《秋风辞》),就越应该加倍 我之留意保存自己的诗稿,应该是在1993年为谢老搜集、编辑《壮暮堂诗钞》之后。
凭记忆回想了之前的所作,只能到七八十年代;此后的吟诵也尽可能留下了底稿。
这阕《满庭芳· 止了。
古人咏栀子的诗词甚多且美,但 画栀子的图绘相对而言却并不多见。
我最早见到的以栀子为画材,是谢老写“芭蕉叶大栀子肥”的诗意,觉得花 太阳转到西山窗下,土屋里浮起几道晃眼的光,映得墙上的旧报纸也摇动起来。
天越发暗了。
我趴在窗台上,望着半开的院门,默默流泪。
姥姥上炕来,把我抱在怀里,轻轻拍着背,哼哼呀呀地唱起来。
一直唱到我迷迷糊糊,姥姥才低声对旁边的小舅妈说,这孩子看来是真想家了,明天送她回吧。
多年前,一个春日的黄昏,我牵着姥姥的手,穿行在刚刚长出小苗的田野。
姥姥穿着灰布褂子,侧襟盘扣,头发在脑后挽成一个髻,用柔软的黑丝网包住,身上传来好闻的米糠的气息。
田野空荡荡的,白杨树在风中轻轻摆动,空气中传来土地新鲜的芳香,一两个农人赶着马车经过,留下一串单调缓慢的车轮声。
以后无数次,我穿过这片田野去往姥 穿过田野 于一身的珍葩之
一。
但它在众香国中的席位,却远不及梅花、牡丹、芍药、海棠、兰花、荷花、桂花、菊花、芙蓉、水仙等。
原因何在呢?我想,当与它开放后衰萎也速而且狼藉也甚有相当的关系。
当梅雨方生,一片江南霏暗之中,油绿浓翠的栀子叶丛中,一夜之间绽放出朵朵琼瑶般的花头,上面还带着露珠,晶莹剔透,香气袭人,令人神清气爽,烦闷涤尽。
然而,不过两天的时间,清纯的靓丽,忽然便成了一坨坨污秽的形色,佛头着粪般颓废委顿地散落在葱碧的枝头叶间,夹杂在新放的荳蔻年华中,久久不落。
相比于其他花卉凋谢时的香消玉殒之美,不免大煞风景。
栀子有好几个别名,其中最典雅的一个叫“薝蔔”,系梵文的音译;亦作旃簛迦、赡博迦,一看便是外来语,远没有薝蔔来得“信、达、雅”。
据《一切经音义》,佛教以十万香花作供养,尤以五树六花中的薝蔔香色殊胜,无比稀有,不可思议。
所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后,东晋人便把原产我国的栀子认作是西域的薝蔔。
唐段成式《酉阳杂俎》“广动植木”有云:“陶贞白言,栀子翦花六出,刻房七道,其花香甚。
相传即西域薝蔔花也。
”至明方以智《通雅》,始以为非是。
今天的植物学家进一步考证出薝蔔实为木兰科的黄兰,与茜草科的栀子实在是风马牛不相及。
但我作诗作画,于栀子仍喜欢以“薝蔔”名之而知错不改。
这不仅是为 了承续前贤千百年来的诗画传统,更因为栀子的从绽放到凋谢,使我联想起《释迦谱》中所讲到的一则故事:释迦修道将成,魔王波旬惧其成道后的法力,便派鬼卒明火执仗向其发动进攻,释迦不为所动,武力尽化灰烬;又遣三个美貌的女儿前往引诱,欲以姿容颜色“乱其净行”: 女诣菩萨(释迦),绮语作姿,三十有二姿,上下唇口,嫈嫇细视,现其陛脚,露其手臂,作凫雁鸳鸯哀鸾之声。
魔女善学女幻迷惑之术,而自言曰:“我等年在盛时,天女端正,莫逾我者,愿得晨起夜寐,供事左右。
”菩萨答曰:“汝有宿福,受得天身,形体虽好,而行为不端,革囊盛臭。
尔来何为?去!吾不用。
”其魔女化成老母,不能自复。
这一故事,在克孜尔石窟、库木吐拉石窟、敦煌莫高窟、云冈石窟的壁画、浮雕中多有表现,名为“降魔变”。
以莫高窟428窟的北周壁画为例,释迦结跏趺坐于画面中央,结降魔印,安忍不动,默如雷霆;上方为群魔乱舞,张弓、搭箭、持枪、抡斧、执蛇,气势汹汹地向佛扑去;下方左侧为三魔女青春靓丽向佛献媚,右侧已变成三个丑婆,“头白面皱,齿落垂涎,肉削骨立,腹大如鼓”,自惭形秽。
这刹那之间的美丑衰变,与栀子花的由极清纯而极污秽,不正相吻合吗?则即使栀子不是薝蔔花,也应是天魔女,与佛教的说教是脱不了干系的。
有了这一认识,再来审美栀子的香馥。
恍然回味到它有别于其他花卉,包括同样浓烈的桂花的香而清,而有一种类似于巴黎香水般香而腻的异域风情。
我曾于星洲观赏洋兰,惊艳之余,以为国兰之美如窈窕淑女而妩媚动人,洋兰之美则如浪荡胡姬而狐媚迷人。
栀子的形色,清真雅正,所体认的是典型的中华审美,但它的香馥,浓烈郁腻,总使人觉得像是异域的浪漫风情。
“花气熏人欲破禅”。
栀子还有一个别名叫“禅友”,它的含义,应该正是“破禅最是栀子花”吧?栀子的玲珑之形、冰玉之色、馥郁之香,兼清纯与狐媚,“我见犹怜”;则即使它明日便狼藉地凋零委顿,“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杜甫《曲江》),又何妨我今天及时的赏心悦目呢? 佛教的一切“受想行识”,“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乃至“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所以,释迦视魔女的美色为老妪的污秽而“去”之“不用”。
但我辈凡夫俗子,执 地珍惜眼前的“欢乐”、“少壮”一样。
自古以来的诗人、画家,于栀子的 歌咏、描绘,无不着眼于它的明丽而无视其芜秽,盖可以概见之矣。
我于栀子的受想行识,始于少年时代。
当时的农村,基本上没有种植观赏花卉的,但远村有一座老宅,天井的墙角有一株几十年的栀子,高达2米,茂密得很。
每到梅雨季节,便绽放出冰花朵朵,给闷湿的空气带来清新凉爽。
今天,每一个花园社区的绿化多有以栀子为主要植花的,而且有高株、矮株、重瓣、单瓣的多个品种,成为海棠、紫藤等春花以后主要的赏花景观。
接下来,便是赏荷了;之后,赏桂、赏菊、赏梅、赏山茶,一年四季,花事无有间断。
任一小区的空间,简直“空即是色”。
观花寻诗,读诗识花,是我从小的一个习惯。
所以,我很早就知道了栀子的别名叫薝蔔,尤对宋朱淑真的“一根曾寄小峰峦,薝蔔香清水影寒;玉质自然无暑意,更宜移向月中看”印象深刻,诚所谓“色空空色,明月前身”。
同时也学着自己做,不过率汰胡诌,打油自喜,覆酱嫌粗。
上世纪70年代后知道了一点格律的知识,慢慢地开始进入诗词的门户,但随写随弃,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的。
因为,当时的写诗只是为了一时的兴趣,包括咏栀子在内,犹如“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
所以乘兴而写,兴尽而弃,完全没有考虑到后来会同诗画打交道并被人误认为小有成就。
就像樱花并不是为了凋谢时的美丽而绽放,栀子更不会因为凋谢时的委顿而不绽放。
每有研究齐白石的专家讲到,白石老人的阔笔花卉配以工细草虫,是因为预见到晚年后会享大名,而届时画不出工细的形象了,所以趁年轻时画了许多虫子却不配景,留待晚年后补成。
但大多数人,事实上是很难预测到自己今后的人生和成就的,所以也就基本上不可能为几十年后的“大成”保存今天的“少作”资料。
不仅卑微如我,当年在农村种地时根本没有妄想过有一天会跳出“农门”,涉事高雅的文艺,就是谢稚柳先生,从小生活在诗人圈里,他早年所写的诗词,也多没有保存下来。
众所周知,谢老的诗词是从李义山、李长吉起手入门的。
但今天所见,纯粹是宋人的平实风格,于二李的谲丽几乎毫无瓜葛。
原来,我们所见之诗都是抗战避兵重庆之后,尤其是维新以来的作品,谢老因沈尹默先生的规劝而转向了宋人。
然而,近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见到部分散佚民间的谢老《词稿》,以陈老莲体的小行楷誊录于“调啸阁”诗笺上,多为40年代之前的作品。
一种呕心沥血、迷离瑰丽的穷工极妍,与后来的“不耐细究”完全不是一回事。
但当年的谢老并没有“敝帚自珍”,以致后来陆续整理《鱼饮诗稿》《甲丁诗词》《壮暮堂诗词》《壮暮堂诗钞》时,都没能收集到这部分真正体现其学二李风格的佳作。
自题栀子写生小卷》,应该便是在这前后所填: 一片江南,绵绵昼夜,梅雨看洗青黄。
更谁知有,薝蔔出银潢。
暑色霪霪搓白,三六出、弄玉斯降。
凝香雪,鼻端消息,渐冽愈迷茫。
琳琅。
初霁后,天凉如水,月影东墙。
照空色无形,馥起浪浪。
且向旃檀海里,快参透、抛却皮囊。
花微笑,何须煮酒,自在渡慈航。
词中的“三六出”,缘于古诗词中的“六出灵葩”。
刚读到时,颇有疑惑。
因为,“六出”的花朵,通常为球根类的草本,如水仙、萱草、百合等;栀子为常绿灌木,花瓣甚夥,虽未曾细数,但当不止六出。
后来一数,为十八瓣,乃暗讥古人格物的粗疏。
转念一想,或许不是为花写实,而是因其花色如雪,以雪花六出故拟之。
又后来,见到矮株单瓣的栀子,果然是六出!再检重瓣者,原来十八瓣分为三层,逐层绽放,每层为六出!乃知古人审物不苟,反是我走马观花、浅尝辄 头之美如荷花,于是也开始画栀子。
但当时的栀子种植并不普遍,连远村老宅中的那一株也被砍了,所以对花写生是要多方寻访、骑自行车前往的。
后来又见到宋人的、钱选的、陈淳的栀子,尽管图片印得很不清晰,还是认真地作对本临摹。
新世纪后,搬入园林化的小区,年年梅雨,都浸淫在薝蔔香中;古画的印刷,更仅“下真迹一等”,画栀子才渐入佳境。
双勾的,点厾的,设色的,水墨的,绢本的,纸本的,熟宣的,生宣的……不拘一格,体会日深而境界稍进,致使栀子,成了我最常画的花卉素材之
一。
庶使冰清玉洁的空色生香,破禅、悟禅,损亦友,益亦友,随缘而无执。
包括栀子在内,我的画上多题有诗文,倒不是因为志存风雅,而是因为性之所好,欲听还看两无厌,故将颜色染香音。
而唐释皎然的《答李季兰》诗,尤得我于栀子的画胆诗心: 天女来相试,将花欲染衣;禅心竟不起,还捧旧花归。
孤姿妍外净,幽馥暑中寒(国画)徐建融 姥家。
可在姥姥去世后的二十年间,我再也没有走上这条路。
但姥姥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中。
有时是委托我照顾她的女儿,有时是喊我过去吃饭,更多时,她像生前一样朦朦胧胧微笑着不说话。
我一阵惊喜,以为她还在世,醒来后却陷入恍惚。
我去年春节才终于知道她的名字——凤芹。
若是有文化的大户人家,这名字应写作凤琴,凤落琴弦,抑或风芩,风中芩草,然而姥姥只是苦出身,自然也只能写作凤芹。
这名字在故乡东大荒,野草一样遍地都是。
姥姥没读过书,一字不识,后来却成了一大家子的主心骨,在村里也颇有威望。
邻里纠纷,婆媳矛盾,兄弟反目,人们习惯来找她。
“老李大姑”到场,一通情理摆下来,人人服气,怨气、怒气也就平息了大半。
村里有一地痞,常年在外偷盗勒索、打架斗殴。
这年地痞从外乡回来,不时在夜里挨家挨户上门讨钱,村里人既恨且惧,不敢得罪,只好给钱免灾。
姥姥却坚决不肯。
她将一柄小斧头磨得锋利,入夜便塞在枕下。
一夜,地痞果然上门。
未等姥姥手中斧头举起,地痞抢先一步上前,屋内空气瞬间凝滞。
不想地痞却递上礼物,脸上堆笑说,我来看看老李大姑,你是我最敬重的人。
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姥姥却冷下一张脸,让他马上走,别弄脏了地。
地痞讪讪离开,姥姥随之把他带来的糕点盒子直接扔出门外。
姥姥是在苦水里泡大的。
1947年,通辽暴发鼠疫,死了上万人,有的甚至全家死绝。
在那场巨大的灾难中,姥姥的父母也双双感染,没几天就撒手人寰。
姥姥有两个哥哥,已经成家立户。
姥姥那时只有十七岁,放到现在才读高
二,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子,在那个饥荒遍地瘟疫横行的年月,养大了五个弟妹。
那时她最小的妹妹才三岁,最小的弟弟也不过五岁。
那段岁月经历了怎样的艰辛苦熬,姥姥从不说及。
我也不过听母亲说起零星的只言片语。
说是缺吃少穿,姥姥把旧袜子上的绒线拆下来,捻成线绳,给小弟弟做了一双鞋。
小弟弟有一次去河边,舍不得把鞋弄脏,就脱下来藏进芦苇丛。
没想到,回来时怎么也找不到,这双珍贵的鞋丢了。
小弟弟一路走一路哭,回到家抱住姐姐,两个人一起哭。
我惟一一次见到姥姥流泪,是有一回小姨姥跟姥姥闹别扭。
姥姥说,你怎么还跟姐姐记仇呢,咱们从小没妈,你是姐姐抱着长大的,就差吃姐姐的奶了呀!小姨姥闻言搂住姥姥,两个头发花白的老人哭了许久。
姥姥二十岁时嫁给姥爷。
姥爷国高毕业,读了许多线装书,写得一手好书法,也有着读书人的耿直与不谙世道。
姥爷家是一个大家族,姥姥的第一个孩子,也就是我妈出生时,因是女孩,按家规不分口粮,男丁才可以。
姥姥抱着孩子去找当家人,据理力争,终于在年底多分了一袋高粱。
姥姥奶水不足,我妈饿得面黄肌瘦。
姥姥把高粱米用水煮至半熟,在嘴里反复嚼出米浆,然后用纱布过滤出汤汁,喂给 周 静,去姥姥家 我妈。
高粱米不能完全煮熟,否则嚼不出浆来。
姥姥在月子里天天嚼着半熟的硬米粒,极大地损害了牙齿,以至于后来她不到四十岁,满口牙就掉光了。
可能是幼小时候的遭际,我妈成年后养成了沉默寡言的性情,严谨内向,五十岁之前从不对我们拥抱、亲吻,耻于表达爱意。
当年爷爷派我爸前去姥姥家给我妈下聘礼时,据说我爸一眼看中了活泼开朗的二姨,隐隐露出后悔之意。
可是姥姥干脆挑明,一句话镇住了我爸——老大没出阁,没可能考虑老
二。
一物降一物。
爷爷和姥姥,是我那骄傲的爸爸在这世上仅有的两个敬畏的人。
我常常想起姥姥,她小个儿,微丰的身材,哪里就有那么多的能量?姥姥有四个女婿,我爸和二姨父是村干部,能说会道,三姨父是农民,只知干活,性情木讷,小姨父在镇里做工,家境也很艰难。
姥姥从不对我爸和二姨父特殊招待,反倒是对三姨父和小姨父格外高看一眼,从不让他俩在家族聚会时有丝毫冷落。
几个女婿过年聚在一起打牌时,姥姥悄悄塞给三姨父和小姨父零钱,以免他们当众难堪。
姥姥一生,赢得了她所有儿女的敬重。
姥姥共有十五个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奇怪的是,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才是姥姥最疼爱的那个。
这是属于姥姥独有的慈祥,她总让我们觉得自己很重要,哪怕是一个顽劣的孩子。
至今我还记得,冬天的夜晚,姥姥把火炕烧得暖暖的,让我趴在热被窝里看电视,我总会在被窝里发现一两个平日难得吃到的苹果,有时是桔子…… 多年后我常常想起姥姥,每每不自觉对比,姥姥在我这个年龄时,已经做过哪些事情,如果姥姥遇到我眼前的困境,会怎么办?姥姥多么有智慧啊,她是我的榜样,有时甚至是我冥冥之中的人生导师。
是的,我觉得姥姥一定还在,在这世上虚无的一角,在扯不断的时空深处。
然而我这一生,再也回不到多年前那个黄昏,我满心欢喜地跟在她身后,穿过春天的田野,目睹整个春天带着慈悲,给一个孩子留下她后来苦苦追寻而再也不可得的,酸楚的甜蜜。
1993年夏天,我在常州一家服装厂打工。
常州《翠苑》杂志社开了一个作家培训班,对,就是这么牛皮哄哄,一帮并不会写作的家伙发一个广告,把文学爱好者们召集到一起,每个人交80块钱,来学习如何写作,或者学习如何做一个作家。
培训班有二十多人,有医生,京剧爱好者,中学教师……以及像我这样的打工人。
头一天报到,在一间会议室,沙发上坐着一个姑娘,皮肤略黑,小脸略扁,眉梢吊起来,是典型的丹凤眼,乌黑的长发,穿一件V领花色连衣裙,露出两块锁骨。
她在写收据,登记学员名单。
她叫周洁茹。
有一些人,天生是冷淡的,第一次见,她没笑;后来见,她也没有笑过,所以我不记得她笑的样子,如果让我寻找一个比喻,来形容一个人是如何的格格不入,指的大约是她,虽然在我许多朋友那里,格格不入的是我,事实也是,这二十多个人后来一直走 微 ﹃文 信公 汇 众 笔会 号﹄ 可是再没有见过。
后来听说她离 我们的青春 开了常州。
2000年的时候,文化宫地下广场摆 着《小妖的网》《糖》和《上海宝贝》,那时的书,可以随便翻,不像现在的书,大多用薄膜套住,除了皮,你什么也看不 到。
我对她的故事感到陌生,也感到不 李凤群 陌生。
她就是这样的。
她的1993年的姿势已经预言了她的文学和生活。
那 时“美女作家”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办 公室阅览室几本周刊上都有那一拨人 动,但大家并不十分喜欢我,一则,因为在我初中同学家的客厅里,我看到她的的访问,大幅照片和她们的作品。
我鲁莽,好出风头,喜欢与人争辩,另海报,觉得她没有所谓的瓜子脸,双眼 她给人感觉很疼痛,很别扭,不自 则,因为我穷,请不起大家吃茶点。
大皮,大眼睛,但我盯着海报上她的脸,那在地活着,但这种疼痛别扭不自在的姿 约有这个因素。
么美,我久久地看着,迷惑不解。
态正是我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呆呆地摩 但周洁茹的格格不入,则不是语 大家当面或是私下里都对周洁茹挲着她的书,我没有买。
那天下午我回 言能形容的。
外面请专家来讲课,或十分客气,几乎算是宠溺,不光是我,其到单位,告诉一个同事我认识周洁茹。
者组织讨论的时候,她也会在那里。
他人也不曾与她有过多的接触,我想可那是一个满脸痘印的文学男青年,他掩 但她几乎不说话,不是不与我说话,也能因为她当时已经在当地小有名气。
饰着他的不信任,说,那你也可以写
一 不与其他人说话。
她坐在那里,仿佛 再次见面是1996年,那时我已经部啊,像她一样出名。
人在那里,但心不知道在哪里。
有时在常州教育学院完成学业,交往了一个 我真的开始写。
如果没有她,以及 候也会抬头,露出眼梢,但她的眼神很帅气的男朋友。
有一次,我和男朋友“美女作家”们在常州文化宫集体亮相 从不落在某处,尤其不与人对视,即逛新华书店,也是常州仅有的几家书店的震撼,我也许不会写下第一部小说。
使她与你对视了,也仿佛没有在看之
一。
几乎可说是毫不意外地,我们在所以于我,她和她的《小妖的网》有不
一 你,简直是目空一切。
她的下颌骨略小说书区域碰到了。
她戴一副吊着链般的意义。
我觉得在现实与梦想之间, 宽,下巴像张爱玲那张经典的相片一子的眼镜,头发扎在脑后,比我第一次如果有一座桥梁,或者有一个前方,那 样略略抬起来,也是那样的不可冒见到她时成熟太多了。
我很震惊。
我她就是。
犯。
我们在一起度过了整个夏天,但喊了她的名字。
她已经不记得我了。
又过了一两年,我们培训班这一拨 每次都仿佛是第一次见到,我相信她我提醒了她培训班的事,她表示认出来人在我家聚会。
有人提到她的近况,说 不知道我是谁,我也相信她不记得其了。
她说,难怪在这里遇到你。
这几乎她回来了。
其实我不知道她去了哪里, 他人是谁。
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这就是她的特色。
她的特色在1993年就又从哪里回来了,但我们趁机给她打 个人就算没有善意,也没有一丝恶意,定住了。
如果我遇到了故人,通常我们电话。
电话接通了。
我告诉她,我已 虽然十分的有距离感,但她的模样和会更夸张,更热烈,更缅怀,或者更冷经开始写长篇。
那很好啊,她说,继 个性在我看来,是十分的非凡,桀骜不淡。
但周洁茹就是这样。
她的方式在续。
不热情不坚持,如果你见过1993 驯到脱离了常规。
1993年就是这样,所以1996年也是这年的她,就不能说她过于冷淡,她让电 就如当年我看到山口百惠的年代,样。
我们说了再见。
话里的时间像水一样,任它淌过去。
然后我们说了再见。
我开始写我的小说,过了两年,小 说出版,可是从来没有摆到过文化宫地下广场的摊位上,直到文化宫地下广场消失不见也没有。
后来我听说过她。
有一个共同的朋友,他告诉我,周洁茹在香港。
她过得很不容易。
大意是她每天要搭很长时间的车送儿女去上学。
那不像她,我于是怀疑地看着那个朋友,但没有追根究底。
我不是一个喜欢追根究底的人,相反,我是喜欢不懂装懂的人。
又过去了许多年,突然有一天,在微信上我接到一个好友邀请:周洁茹,作为《香港文学》的主编,来约稿。
我以为她来跟我叙旧,可是她完全想不起来——她因为戴瑶琴教授的推荐加我,她就是来约稿的。
然后就是朋友圈里的周洁茹。
我偶尔看她的小说,她养了一双可爱、阳光的儿女,她编《香港文学》,还勤奋地写,清单拉出来,吓我一跳,她一年写三十个短篇。
坦白说,她的小说似乎不是我的菜,我碰到就读一些,不碰到也就算了,但我对她这个人,充满了,充满了旧情。
充满了敬意,充满了怜爱。
我不知道怎么解释。
2020年,我回南京,在家里翻旧照片,翻到一张,她坐在沙发上,我如获至宝,立刻发给她,她认出了自己,然后问我:哪个是你? 那个背影。
穿着白色T恤的背影。
那件衣服我记得,料子厚而不透气,我因为年轻壮实而时常在流汗……但那是我们的青春,被好心人定格在那里,它使我酸楚。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
下一篇A04,A04 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