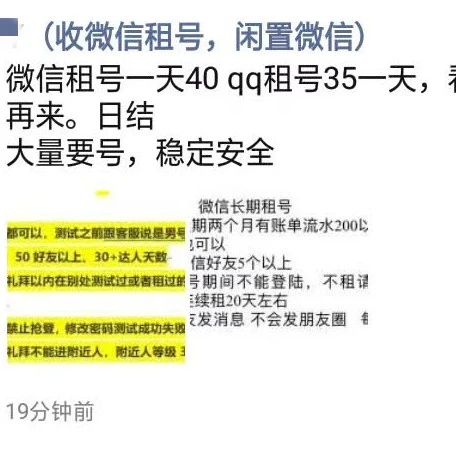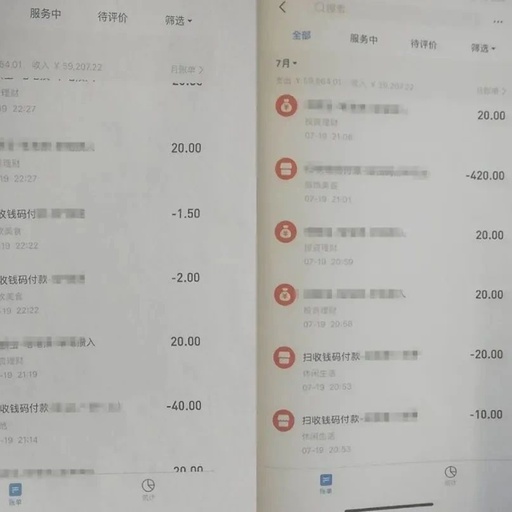□热线电话:(010)64812090□E-mail:wenypp@
上世纪70年代末在京求学,北京大学中文系众多老师中,我认识彭兰先生相对较晚。
但彭先生第一次给我们讲高适诗,我们就已经从她吟诵古诗的节奏、讲解诗歌时所流露出的激情,感受到她身上所特有的诗人气质。
跟彭先生聊多了,才知道她的家学渊源。
彭兰先生的父亲是清代进士,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受家庭的熏陶,彭先生从小就学书作诗。
由于父亲早逝,她很小就随舅舅读私塾。
一次舅舅随口出了个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当时年仅九岁的彭先生不假思索当即对出“对局相争一盘棋”的下联,显示出超人的文学天赋,赢得舅舅连声称赞。
彭先生对古典诗词极有悟性,少年时便写得一手好诗。
后来我曾读到彭先生的几首诗作,其中《月夜抒怀三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清辉依旧透窗纱,往事回想梦里花。
国破家亡人散尽,亲朋姐弟各天涯。
”“万里河山半劫灰,婵娟含恨且低回。
三更数尽难成梦,恍惚遥闻画角哀。
”“江汉奔涛犹滚滚,英雄儿女恨填膺。
冲冠怒发驱强寇,四亿中华庆再生。
”诗中既浸透着诗人对国破家亡的凄楚哀恨,又流露出巾帼不让须眉、驱逐强虏的悲壮豪情。
大教学生涯。
彭先生与张先生的这段佳话,我是近些年才陆陆续续了解到的,但在当年与彭先生、张先生点点滴滴的接触中,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依恋。
彭先生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高岑诗研究”,但她那平易近人、热情爽快的性格,使她与学生间很容易地建立起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还时常邀请学生去她家做客。
那时的师生关系真的十分单纯融洽。
拜访老师既不需要收到老师的邀请也不需要事先预约,都是直接找上门去。
话说回来,那个年代电话还是奢侈品,只有高干、名教授家才配备有电话。
这样也有好处,就是任何时候有了问题想去向老师请教,只要师生关系好,随时都可登门拜访。
那时的老师也有下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互动的传统。
我记得陈贻焮、袁行霈、陈铁民、周先慎等先生就都曾来到77级中文系学生居住的32楼看望学生。
我来自外地,在北京除了同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亲友。
彭先生对学生的热情与关心总能使我感到温暖与信任。
每当遇到问题,我都很愿意首先向彭先生请教。
这样,我也就成了彭先生家中的一位常客。
读研一的下半年,系里安排彭兰先生给我们几位古代文学研究生开设 “清辉依旧透窗纱”笔 荟 ——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兰先生 □王景琳 抗日战争时期,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彭先生为继续求学,变卖家产,只身随母亲前往西南联大。
不幸的是,母亲于途中患病,当时正值日本飞机的连日轰炸,医护人员都躲进了防空洞,年仅20岁的彭先生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躺在病床上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逝。
此后,彭先生一直被困在沦陷区,两年后才有机会逃离,辗转来到位于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后又转入昆明西南联大本部。
彭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新青年一样,积极投身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曾担任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主席,并经常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对沦陷家乡的深切怀念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这一点深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赏识。
特别当闻一多先生得知彭先生父母双亡的悲惨身世,对彭先生更是疼爱有加,收其为干女儿。
彭先生自己也把闻一多当作父亲一样看待。
彭兰先生与闻一多的这段往事,她很少主动向人提及。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彭先生不想借与闻一多先生一家的这种特殊关系而博人眼球,同时也是刻意避免以闻一多干女儿身份提高自己学术地位之嫌。
尽管如此,课上课下,彭兰先生每每引述闻一多先生对某一文学现象的看法或见解,我们仍可真切地感受到彭兰先生对闻一多先生由衷的仰慕与尊重。
这些年,我总是在想,像彭先生这一代这样低调谦虚平实的为人风范,在如今浮躁奢华夸张的社会风气中,已成凤毛麟角,更不是那些所谓“教授”“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上学期间,曾闻彭先生与张世英先生结为伉俪是由闻一多先生介绍并为其主婚的。
与彭先生熟识之后,曾向彭先生求证,才知所传有误。
写此文时,我又特地与彭、张两位先生的长子张晓岚确认,得知彭先生与张先生其实是在西南联大的湖北同乡会上相识的。
其时,彭先生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颇得闻一多、浦江清、罗庸、朱自清等先生赏识,而学哲学的张先生也对古典诗词饶有兴趣,常与彭先生唱和往来。
一来二去,两人由诗而结为情侣。
可以说,“诗”在彭先生和张先生的关系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张先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坦白”,当时的他并不像彭先生那样具有新青年式的激进,而更属于一心躲在“象牙塔”中做学问的青年学俊。
与彭先生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张先生曾特地与彭先生一起拜见闻一多先生,接受了闻先生“准岳父”式的“面试”长谈。
由此可见当初闻先生对彭先生的关爱的确犹如父亲对女儿一般。
此后,在闻一多与彭兰先生的共同影响下,张世英先生终于走出了“象牙宝塔”,也与彭先生一起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们在昆明结婚时,闻一多先生担任彭先生的主婚人,冯文潜先生担任张先生的主婚人,而汤用彤先生则为证婚人。
这一场号称“文学与哲学联姻”的婚礼,其证婚与主婚三人皆为现代学术界一顶一的大家! 彭先生和张先生婚后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就住在闻一多先生家中。
后来,两人一起离开昆明前往武汉任教,就在他们离开昆明不久,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
此事让彭先生与张先生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痛。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先生和彭先生又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北 “汉乐府研究”专题课。
开课前,系里告诉我们,由于彭先生身体不好,腿脚不便,要我们去彭先生家上课。
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彭先生比当年上“高岑诗研究”时的身体更差了。
她坐在椅子上,腿上还盖着一条毯子,似乎有些疲惫。
尽管如此,一开讲,彭先生立刻精神大振,吟诵起汉乐府的声调、魅力不亚于当年。
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在中关园42号公寓岳父家住过一段,那段时间里常在小区与住在43号公寓的彭先生与张先生碰面。
有时也带着女儿去彭先生家做客,因此跟张世英先生也熟悉起来。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
一次,张世英先生黑格尔戏剧理论的文章在中戏的学报刊登后引起了系里几位教授的重视。
当他们得知张先生的文章是我转交过来的,就找我商量能否邀请张先生为中戏师生做一次黑格尔戏剧理论的专题讲座。
我知道张先生是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平时科研教学任务繁重,我只答应可以去试试。
当天下午我去彭先生家时,张先生不在。
我就请彭先生转告张先生能否拨冗给中戏师生作个讲座。
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就得到了张先生肯定的答复。
到了上课那天,中戏派专车及系秘书到彭先生家来接张先生。
那天,我本也应该去学校听张先生的讲座,偏巧孩子生病,只好留在家里。
接张先生的车走了不到一小时,系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负责此事的系领导出差了,临走前忘记跟学校安排讲座的事,既没通知学生,也没安排教室。
我一听,头都炸了,这叫什么事啊!我请系秘书马上联系校车队派车送张先生回家,可被告知学校的车都在外面,一时回不来,只能按系里原定的时间派车。
半小时后,另一位系领导也给我打电话,要我当天务必代表学校先给张先生赔个不是,第二天系领导会登门亲自道歉。
放下电话,趁着张先生还被“困”在我们系的当口,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彭先生家,请求彭先生等张先生回来时,一定先给张先生消消气。
彭先生见我真的急了,马上宽慰我说,你放心,发生这样的事的确不好,但这不是你的错,张先生一定不会怪你的。
当晚,我一进彭先生家门,张先生就笑眯眯地接待了我,没等我开口道歉便说,今天我在你们系上了一堂物价课。
原来张先生在系办公室等车的时候,系秘书和几个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抱怨物价。
张先生打趣说,以前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些事,今天倒是难得有机会体恤了一下民情。
张先生的玩笑话让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我知道,这得归功于彭先生的劝说。
否则的话,让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系办公室干坐两个多小时,尽听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怎么可能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开玩笑呢。
稍后,张先生请我转告我们系领导不必来了,但彭先生认为这样对我不好,所以最后张先生还是答应见一面。
我离开时,彭先生悄悄叮嘱我,你们系领导来给张先生道歉时,你最好别在场,否则,会让你的领导难堪的。
彭先生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
对我来说,彭先生的的确确不仅是学业上让我十分尊敬的良师,而且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位可以信赖、托付的引导者。
此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总是会按照彭先生教我的去做,直到今天。
副刊 ·2019年7月8日 心语有“家”的感觉真好 ——张海回忆第一次全国书代会 □赵刚 随着“左”的思想冰封的解冻,文艺春天的大门于1980年5月在中原大地徐徐开启,胜利召开的河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不仅恢复了已被强行解散了13年的河南省文联,同时成立了全省各专业文艺团体,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孕育而生。
为了开创中原书坛新局面,几经物色,省书协理事、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海成为省书协唯一一位专职借调干事。
1981年春的一天,张海正在聚精会神地起草一份活动方案,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可将一份文件递给张海。
张海定睛细看,竟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备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召开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不禁兴奋道:“太好啦!这可是全国书界同道的大好事,咱们省书协终于有‘家’可归啦!” 喜形于色——而且是当着领导的面,这是素来稳重谦和的张海从来没有过的表现,流露出他对中国书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的殷切期待。
因为他知道,以实用文字的书写作为与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并列的艺术,是书法之于世界艺术宝库独有的贡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存在于一些人脑海中的偏颇认识,致使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呼声虽高,但终未形成共识。
如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书法终于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舞台,怎能不令张海倍感振奋!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中国书协创建工作主要参与者、第一次全国书代会秘书长佟韦,在其纪实文集《书坛纪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6月出版)中揭示了谜底。
原来,在标志着文学艺术的春天真正到来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再次响起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强烈呼声。
中国文联从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和各地书法团体的相继恢复与建立中,认识到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之重要性,经报告中宣部并获批准,由中国文联负责筹备中国书法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而正式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80年11月7日上午,一件对于书法界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书协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坐落于北京西山半山坡上的中国书协筹委会主任舒同家里召开。
与会的朱丹、陈叔亮等10人,虽然大多年逾古稀,但是激情饱满,深情地将中国书协这颗饱寄着中国书法人希冀的种子播入隆冬的土壤,全身心陪伴它经历三九严寒的考验,成长为中华艺术园林一道这边独好的风景! 手持《通知》,朱可犯难了。
因为,会议筹备组分配给河南省代表团仅有3个名额,而鉴于本次会议意义非凡,经河南省文联党组研究,除省书协副主席李悦民因身体原因不便出行外,希望其他3位正副主席都能出席。
如此,难题出现了,主席谢瑞阶年届八旬,副主席 庞白虹、陈天然年事已高,作为代表团诸多事务性工作难以处理。
如果能够多争取到1个代表名额,选派1名相对年轻、具有“代表”性、办事能力强者与三老同行,则可谓最佳方案。
如此,省文联党组决定,委派张海代表省文联,赴中国书协筹备组汇报增加代表名额一事。
深知责任重大,张海立即出发,坐了一夜火车。
下车后,脸不洗,饭不吃,直奔位于北京市五四大街的中国文联。
中国文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书协筹委会负责人佟韦热情地接待了张海,并说:“我和你们的黑丁先生(即著名作家、评论家,时任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于黑丁)认识。
他近况还好吧?”张海一一作答后,阐明来意。
做事干练、性格爽快的佟韦略作思考,遂将一份《代表登记表》交付张海,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希望也能成为书法大省,争取给你们增补1个名额。
为了尽快将这个好消息带回单位,他马不停蹄乘车返回。
次日清晨,经过一夜列车颠簸的张海拖着疲惫的身体,刚在办公室坐定,前后脚进来的朱可责怪道:“你平时办事不是挺利索吗?这回怎么拖拖拉拉,前天交办的事情,今天还没有动身?”张海一声不吭地将《登记表》交给朱可,讲了原委,朱可乐得直竖大拇指:“这次把三老托付给你,我就放心啦!” 就这样,39岁的张海以河南省代表团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1981年5月5日至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书代会。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发表了指明方向、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书协筹委会主任舒同作了题为《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艺术传统,为人民服务》的报告;中国书协筹委会副主任陈叔亮作了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委会工作报告》,并充满激情地为大会召开题词“心底开花,笔底神来。
书坛好友,有家可归”。
同时,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圆满完成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等各项议程。
当新当选的中国书协副主席启功在闭幕致词中讲到“广大书法篆刻工作者久已盼望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现在正式成立了!大家有个‘家’了!”的时候,强烈的共鸣使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张海的心灵更是为之震撼,神圣的使命与责任使他感到肩头沉甸甸的。
恰是这次被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兰亭盛会’”的亲历,深深地激励着张海以中原大地为舞台,为中国书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尽心竭力添砖加瓦。
而他的人生亦与蒸蒸日上的中国书法事业密切相连,以其优秀的组织才能和执著的艺术追求,在之后召开的第二至七次全国书代会上从未缺席,历任中国书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矿工的名义说祖国(外一首)□王金海 父亲,一位矿工在祖国边陲,与煤紧紧拥抱忘了小家,他用青春书写最朴实的誓言 那一代人,祖国就是家祖国是最亲的母亲祖国是唯一的依靠 乌鲁木齐芦草沟,祖国版图上一处火热的圆点 在祖国最西部父亲的能源梦在高高的井架前豪情父亲说,最苦是煤和荒漠但心中有诗和祖国 父亲已逝。
父亲的故事祖国最初的煤事都将是历史或将被人们淡忘,但祖国母亲不会忘你 在我心中,祖国是火与红的七月是雄壮激情的八月是沉甸甸的金秋十月 我的祖国 四十年,依靠在祖国的臂膀见证中国梦的历程那蓝色的大海上,海舰如祖国坚实的铜墙铁臂 父亲的祖国,父亲的煤我接力在改革开放紧跟新时代脚步,在高高的煤山前成熟 每当晴朗的早晨看见渐高刷新的煤山站在祖国大地上为煤,为这片土地吟赋出我最激情的诗篇 墨韵 佳冠图(中国画) □崔涛 乡村 堂嫂和三十斤粮票 □李宏 堂哥比我大五个月,我俩在一个屋檐下长大,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十八岁那年,公社武装部长给我送来了去云南边疆当兵的入伍通知书,父亲很焦灼,母亲很紧张,家里人很忐忑。
临离开家的头一天晚上,堂哥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到我手里说:“那边还在打仗,枪炮响起来时脑子灵光点,眼睛看远点,想家了买块糖吃。
”从小三天两头与我打架的堂哥这一席话,竟然把我搞得泪崩了,我对堂哥说:“打仗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爸妈有啥困难你多照应点。
”从那一刻起,似乎我俩都长大了,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
转眼间,我在部队已经呆了四年,身上两个兜的布衣也换成了四全兜的“的卡”。
一天下午,我一身泥土刚从训练场回到营地,通信员就举着一捆信冲着我说:“这几天每天都有你的信呢,好像还有一张照片,是不是你家又给你介绍女朋友了?你得请我喝瓶菠萝汽水。
”我接过信举过头顶,在太阳下一照,薄薄的白纸信封里果然有一张照片。
我从裤兜里掏出零钱递给通信员说:“菠萝汽水管你喝,今后有我的信第一时间送来。
” 躺在草坪上的树荫下,先打开了堂哥写来的信,信封里夹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
堂哥在信中说:“我注定要跟在牛屁股后面犁一辈子地了,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你未来的嫂子,刚满十七岁,样子生得很漂亮也很贤惠,娘家在靠近陕西那边的大山里,可惜她没有上过一天学。
你可别像哥一样,你得找一个在城里上班的,穿高跟鞋穿喇叭裤烫波浪头的洋婆娘回来。
” 这封信搞得我很兴奋。
我将信反复读了两遍后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顾不得一身疲惫便跑了几公里山路去了镇上的邮局,将电话打到了公社的公用电话上。
父亲接电话后责备我说:“这么远打个长途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也不怕浪费钱。
你堂哥结婚的时间订在腊月间。
只是女方又提出另外还要追加五十斤大米和一辆永久自行车,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哪有钱去置办这些东西,这几天把你堂哥一家人急得都快疯了。
”撂下电话,我原本很亢奋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
当时农村刚包产到户不久,堂哥家虽然比我家日子略为宽裕,但由于家里祖孙三代、兄弟姊妹七个,吃饱肚子的事还没有完全解决,置办聘礼已经举债了,再拿出五十斤大米一辆自行车的钱来,确实不是一件小事。
经过一夜的心理较量,我还是在第二天早晨借自行车去了镇上的邮局,我把自己攒下来准备探亲用的三十斤全国粮票和二十元钱寄给了堂哥。
过春节回家时,我终于见到了照片上的堂嫂。
土布衣服难掩堂嫂的漂亮羞涩,脚上的劣质皮鞋上全是泥,头发也有些散乱。
堂嫂一口川北土话大着嗓门对我说:“你寄回来的二十块钱和三十斤粮票救了他的急,不然,我爹是不会让我嫁到他们家的。
”堂嫂还说:“兄弟你放心,我这辈子砸锅卖铁也得把欠你的粮票还上。
”堂哥说:“女人家惦记的都是这些陈年旧事,你寄钱和粮票的事她
一 直挂在嘴上,前几天去县城,地摊上有人卖全国粮票做纪念品,她还说要买了送给你呢!被我骂了一顿。
”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期间我从云南到山东到江苏又到了北京,始终在军营里摸爬滚打,我与堂哥堂嫂两家人也都建了新房不再同居一个屋檐下了,我们从青涩少年变成了小老头儿,见面和写信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
父亲过世那年,堂哥带着他妻子孩子来我家奔丧,我突然感觉堂嫂一下子变得很苍老,头发枯黄了,皮肤变糙了,背也有些驼了,完全没有了当年照片上那个女人的水灵样。
堂嫂一边做事一边难为情地对我说:“现在粮票已经作废了,还不上你的情了,这几天忙完一定来我家,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过去多年了,谁说过让你还?那算是我随的份子。
” 堂嫂去池边洗菜的功夫,母亲对我絮叨说:“你堂哥整天看些莫名其妙的闲书喝寡酒,除了下河捞沙下地种田,家务事孩子上学一概不管不问,全靠他女人里外张罗。
”我问母亲:“他们家日子过得不好?人咋变得这么苍老?”母亲说:“这女人心强好胜,别看她大字不识一个,却一门心思要培养娃儿读书,儿子培养得一个赛一个有出息,老大西南财大还没毕业就被银行挖走了,老二又是全县的高才生,听村里人讲,考上川大重大没有问题。
”母亲的话,让我对堂嫂有了更多的敬重。
转眼到了今年七月,我回四川参加一个评审会,会议结束时我顺道回了一趟乡下。
车过堂哥家二层楼门口时,我问邻居:“堂哥家咋没有人呢?是下地干活了吗?”邻居告诉我说:“你堂哥两口子现在洋盘了,经常到外地旅游,刚从大理丽江回来,现在又去香港澳门旅游去了。
你没有你堂哥的微信呀,里面全是他们旅行的照片,你看看就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了”。
我从邻居那里要了堂哥的微信。
果然,里面全是一家人外出旅行的照片。
有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的,有在丽江古城的,有在紫荆广场的,堂哥堂嫂真的变得年轻洋气了,竟然还用上了抖音。
这天晚上回到驻地,我给堂哥写了一条微信:“缺粮票缺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享受阳光享受生活,真心祝福你们!”但最终,我还是将这条微信删了没有发出,我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 刊头题字 刘炳森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2号邮政编码:100029办公室(:010)64810369广告部:(010)64812322发行部:(010)64811201广告发布登记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068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印刷零售价:1.00元
但彭先生第一次给我们讲高适诗,我们就已经从她吟诵古诗的节奏、讲解诗歌时所流露出的激情,感受到她身上所特有的诗人气质。
跟彭先生聊多了,才知道她的家学渊源。
彭兰先生的父亲是清代进士,母亲出身于书香门第。
受家庭的熏陶,彭先生从小就学书作诗。
由于父亲早逝,她很小就随舅舅读私塾。
一次舅舅随口出了个上联:“围炉共话三杯酒”,当时年仅九岁的彭先生不假思索当即对出“对局相争一盘棋”的下联,显示出超人的文学天赋,赢得舅舅连声称赞。
彭先生对古典诗词极有悟性,少年时便写得一手好诗。
后来我曾读到彭先生的几首诗作,其中《月夜抒怀三首》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清辉依旧透窗纱,往事回想梦里花。
国破家亡人散尽,亲朋姐弟各天涯。
”“万里河山半劫灰,婵娟含恨且低回。
三更数尽难成梦,恍惚遥闻画角哀。
”“江汉奔涛犹滚滚,英雄儿女恨填膺。
冲冠怒发驱强寇,四亿中华庆再生。
”诗中既浸透着诗人对国破家亡的凄楚哀恨,又流露出巾帼不让须眉、驱逐强虏的悲壮豪情。
大教学生涯。
彭先生与张先生的这段佳话,我是近些年才陆陆续续了解到的,但在当年与彭先生、张先生点点滴滴的接触中,我总能深深地感受到他们之间的默契与依恋。
彭先生虽然只教了我们一个学期的“高岑诗研究”,但她那平易近人、热情爽快的性格,使她与学生间很容易地建立起了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她还时常邀请学生去她家做客。
那时的师生关系真的十分单纯融洽。
拜访老师既不需要收到老师的邀请也不需要事先预约,都是直接找上门去。
话说回来,那个年代电话还是奢侈品,只有高干、名教授家才配备有电话。
这样也有好处,就是任何时候有了问题想去向老师请教,只要师生关系好,随时都可登门拜访。
那时的老师也有下到学生中间与学生互动的传统。
我记得陈贻焮、袁行霈、陈铁民、周先慎等先生就都曾来到77级中文系学生居住的32楼看望学生。
我来自外地,在北京除了同学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亲友。
彭先生对学生的热情与关心总能使我感到温暖与信任。
每当遇到问题,我都很愿意首先向彭先生请教。
这样,我也就成了彭先生家中的一位常客。
读研一的下半年,系里安排彭兰先生给我们几位古代文学研究生开设 “清辉依旧透窗纱”笔 荟 ——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彭兰先生 □王景琳 抗日战争时期,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的彭先生为继续求学,变卖家产,只身随母亲前往西南联大。
不幸的是,母亲于途中患病,当时正值日本飞机的连日轰炸,医护人员都躲进了防空洞,年仅20岁的彭先生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躺在病床上因得不到及时救治而病逝。
此后,彭先生一直被困在沦陷区,两年后才有机会逃离,辗转来到位于叙永的西南联大分校,后又转入昆明西南联大本部。
彭先生在西南联大时,和那个时代的许多新青年一样,积极投身进步学生的爱国运动,曾担任西南联大湖北同乡会主席,并经常通过诗歌创作表达对沦陷家乡的深切怀念以及对日本侵略者的切齿痛恨,这一点深受联大中文系教授闻一多先生的赏识。
特别当闻一多先生得知彭先生父母双亡的悲惨身世,对彭先生更是疼爱有加,收其为干女儿。
彭先生自己也把闻一多当作父亲一样看待。
彭兰先生与闻一多的这段往事,她很少主动向人提及。
在我看来,这是因为彭先生不想借与闻一多先生一家的这种特殊关系而博人眼球,同时也是刻意避免以闻一多干女儿身份提高自己学术地位之嫌。
尽管如此,课上课下,彭兰先生每每引述闻一多先生对某一文学现象的看法或见解,我们仍可真切地感受到彭兰先生对闻一多先生由衷的仰慕与尊重。
这些年,我总是在想,像彭先生这一代这样低调谦虚平实的为人风范,在如今浮躁奢华夸张的社会风气中,已成凤毛麟角,更不是那些所谓“教授”“学者”所能望其项背的。
上学期间,曾闻彭先生与张世英先生结为伉俪是由闻一多先生介绍并为其主婚的。
与彭先生熟识之后,曾向彭先生求证,才知所传有误。
写此文时,我又特地与彭、张两位先生的长子张晓岚确认,得知彭先生与张先生其实是在西南联大的湖北同乡会上相识的。
其时,彭先生是中文系有名的才女,颇得闻一多、浦江清、罗庸、朱自清等先生赏识,而学哲学的张先生也对古典诗词饶有兴趣,常与彭先生唱和往来。
一来二去,两人由诗而结为情侣。
可以说,“诗”在彭先生和张先生的关系中起着催化剂的作用。
张先生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坦白”,当时的他并不像彭先生那样具有新青年式的激进,而更属于一心躲在“象牙塔”中做学问的青年学俊。
与彭先生确定恋爱关系以后,张先生曾特地与彭先生一起拜见闻一多先生,接受了闻先生“准岳父”式的“面试”长谈。
由此可见当初闻先生对彭先生的关爱的确犹如父亲对女儿一般。
此后,在闻一多与彭兰先生的共同影响下,张世英先生终于走出了“象牙宝塔”,也与彭先生一起积极参与进步学生组织的各种抗议活动。
上世纪四十年代,他们在昆明结婚时,闻一多先生担任彭先生的主婚人,冯文潜先生担任张先生的主婚人,而汤用彤先生则为证婚人。
这一场号称“文学与哲学联姻”的婚礼,其证婚与主婚三人皆为现代学术界一顶一的大家! 彭先生和张先生婚后曾有相当一段时间就住在闻一多先生家中。
后来,两人一起离开昆明前往武汉任教,就在他们离开昆明不久,闻一多先生惨遭杀害。
此事让彭先生与张先生都感到无比震惊与悲痛。
上世纪50年代初,张先生和彭先生又先后受聘于北京大学,开始了他们长达数十年的北 “汉乐府研究”专题课。
开课前,系里告诉我们,由于彭先生身体不好,腿脚不便,要我们去彭先生家上课。
第一次上课,就发现彭先生比当年上“高岑诗研究”时的身体更差了。
她坐在椅子上,腿上还盖着一条毯子,似乎有些疲惫。
尽管如此,一开讲,彭先生立刻精神大振,吟诵起汉乐府的声调、魅力不亚于当年。
读研究生的第二年曾在中关园42号公寓岳父家住过一段,那段时间里常在小区与住在43号公寓的彭先生与张先生碰面。
有时也带着女儿去彭先生家做客,因此跟张世英先生也熟悉起来。
研究生毕业后,我在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任教。
一次,张世英先生黑格尔戏剧理论的文章在中戏的学报刊登后引起了系里几位教授的重视。
当他们得知张先生的文章是我转交过来的,就找我商量能否邀请张先生为中戏师生做一次黑格尔戏剧理论的专题讲座。
我知道张先生是著名的黑格尔研究专家,平时科研教学任务繁重,我只答应可以去试试。
当天下午我去彭先生家时,张先生不在。
我就请彭先生转告张先生能否拨冗给中戏师生作个讲座。
没想到当天晚上我就得到了张先生肯定的答复。
到了上课那天,中戏派专车及系秘书到彭先生家来接张先生。
那天,我本也应该去学校听张先生的讲座,偏巧孩子生病,只好留在家里。
接张先生的车走了不到一小时,系秘书突然给我打电话,说负责此事的系领导出差了,临走前忘记跟学校安排讲座的事,既没通知学生,也没安排教室。
我一听,头都炸了,这叫什么事啊!我请系秘书马上联系校车队派车送张先生回家,可被告知学校的车都在外面,一时回不来,只能按系里原定的时间派车。
半小时后,另一位系领导也给我打电话,要我当天务必代表学校先给张先生赔个不是,第二天系领导会登门亲自道歉。
放下电话,趁着张先生还被“困”在我们系的当口,我急急忙忙地跑到了彭先生家,请求彭先生等张先生回来时,一定先给张先生消消气。
彭先生见我真的急了,马上宽慰我说,你放心,发生这样的事的确不好,但这不是你的错,张先生一定不会怪你的。
当晚,我一进彭先生家门,张先生就笑眯眯地接待了我,没等我开口道歉便说,今天我在你们系上了一堂物价课。
原来张先生在系办公室等车的时候,系秘书和几个不知道什么人在那里抱怨物价。
张先生打趣说,以前我从来没关心过这些事,今天倒是难得有机会体恤了一下民情。
张先生的玩笑话让我悬着的心彻底放了下来。
我知道,这得归功于彭先生的劝说。
否则的话,让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在我们系办公室干坐两个多小时,尽听些鸡毛蒜皮的琐事,怎么可能还能这么心平气和地开玩笑呢。
稍后,张先生请我转告我们系领导不必来了,但彭先生认为这样对我不好,所以最后张先生还是答应见一面。
我离开时,彭先生悄悄叮嘱我,你们系领导来给张先生道歉时,你最好别在场,否则,会让你的领导难堪的。
彭先生就是这样时时处处为他人着想。
对我来说,彭先生的的确确不仅是学业上让我十分尊敬的良师,而且也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位可以信赖、托付的引导者。
此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我都总是会按照彭先生教我的去做,直到今天。
副刊 ·2019年7月8日 心语有“家”的感觉真好 ——张海回忆第一次全国书代会 □赵刚 随着“左”的思想冰封的解冻,文艺春天的大门于1980年5月在中原大地徐徐开启,胜利召开的河南省第二次文代会,不仅恢复了已被强行解散了13年的河南省文联,同时成立了全省各专业文艺团体,河南省书法家协会孕育而生。
为了开创中原书坛新局面,几经物色,省书协理事、安阳市群众艺术馆副馆长张海成为省书协唯一一位专职借调干事。
1981年春的一天,张海正在聚精会神地起草一份活动方案,河南省文联党组成员、副主席朱可将一份文件递给张海。
张海定睛细看,竟是由中国文联和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备委员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召开中国书法家第一次代表大会的通知》,不禁兴奋道:“太好啦!这可是全国书界同道的大好事,咱们省书协终于有‘家’可归啦!” 喜形于色——而且是当着领导的面,这是素来稳重谦和的张海从来没有过的表现,流露出他对中国书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的殷切期待。
因为他知道,以实用文字的书写作为与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戏剧等并列的艺术,是书法之于世界艺术宝库独有的贡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存在于一些人脑海中的偏颇认识,致使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呼声虽高,但终未形成共识。
如今,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书法终于能够拥有属于自己的艺术舞台,怎能不令张海倍感振奋!这到底是怎么回 事呢?中国书协创建工作主要参与者、第一次全国书代会秘书长佟韦,在其纪实文集《书坛纪事》(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4年6月出版)中揭示了谜底。
原来,在标志着文学艺术的春天真正到来的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再次响起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的强烈呼声。
中国文联从大量群众来信来访和各地书法团体的相继恢复与建立中,认识到成立全国性书法组织对于推进社会主义文艺百花齐放之重要性,经报告中宣部并获批准,由中国文联负责筹备中国书法家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进而正式成立中国书法家协会。
那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1980年11月7日上午,一件对于书法界而言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中国书协筹委会第一次会议,在坐落于北京西山半山坡上的中国书协筹委会主任舒同家里召开。
与会的朱丹、陈叔亮等10人,虽然大多年逾古稀,但是激情饱满,深情地将中国书协这颗饱寄着中国书法人希冀的种子播入隆冬的土壤,全身心陪伴它经历三九严寒的考验,成长为中华艺术园林一道这边独好的风景! 手持《通知》,朱可犯难了。
因为,会议筹备组分配给河南省代表团仅有3个名额,而鉴于本次会议意义非凡,经河南省文联党组研究,除省书协副主席李悦民因身体原因不便出行外,希望其他3位正副主席都能出席。
如此,难题出现了,主席谢瑞阶年届八旬,副主席 庞白虹、陈天然年事已高,作为代表团诸多事务性工作难以处理。
如果能够多争取到1个代表名额,选派1名相对年轻、具有“代表”性、办事能力强者与三老同行,则可谓最佳方案。
如此,省文联党组决定,委派张海代表省文联,赴中国书协筹备组汇报增加代表名额一事。
深知责任重大,张海立即出发,坐了一夜火车。
下车后,脸不洗,饭不吃,直奔位于北京市五四大街的中国文联。
中国文联办公室副主任、中国书协筹委会负责人佟韦热情地接待了张海,并说:“我和你们的黑丁先生(即著名作家、评论家,时任河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的于黑丁)认识。
他近况还好吧?”张海一一作答后,阐明来意。
做事干练、性格爽快的佟韦略作思考,遂将一份《代表登记表》交付张海,他说,河南是人口大省,希望也能成为书法大省,争取给你们增补1个名额。
为了尽快将这个好消息带回单位,他马不停蹄乘车返回。
次日清晨,经过一夜列车颠簸的张海拖着疲惫的身体,刚在办公室坐定,前后脚进来的朱可责怪道:“你平时办事不是挺利索吗?这回怎么拖拖拉拉,前天交办的事情,今天还没有动身?”张海一声不吭地将《登记表》交给朱可,讲了原委,朱可乐得直竖大拇指:“这次把三老托付给你,我就放心啦!” 就这样,39岁的张海以河南省代表团正式代表身份,参加了1981年5月5日至9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第一次全国书代会。
会上,中宣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发表了指明方向、热情洋溢的讲话;中国书协筹委会主任舒同作了题为《团结起来,继承和发扬我国书法艺术传统,为人民服务》的报告;中国书协筹委会副主任陈叔亮作了题为《中国书法家协会筹委会工作报告》,并充满激情地为大会召开题词“心底开花,笔底神来。
书坛好友,有家可归”。
同时,在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氛围中,圆满完成了第一届理事会选举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等各项议程。
当新当选的中国书协副主席启功在闭幕致词中讲到“广大书法篆刻工作者久已盼望的中国书法家协会,现在正式成立了!大家有个‘家’了!”的时候,强烈的共鸣使会场爆发出雷鸣般经久不息的掌声,张海的心灵更是为之震撼,神圣的使命与责任使他感到肩头沉甸甸的。
恰是这次被誉为“社会主义时代的‘兰亭盛会’”的亲历,深深地激励着张海以中原大地为舞台,为中国书协这个来之不易的“家”尽心竭力添砖加瓦。
而他的人生亦与蒸蒸日上的中国书法事业密切相连,以其优秀的组织才能和执著的艺术追求,在之后召开的第二至七次全国书代会上从未缺席,历任中国书协理事、常务理事、副主席、主席、名誉主席。
我和我的祖国 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以矿工的名义说祖国(外一首)□王金海 父亲,一位矿工在祖国边陲,与煤紧紧拥抱忘了小家,他用青春书写最朴实的誓言 那一代人,祖国就是家祖国是最亲的母亲祖国是唯一的依靠 乌鲁木齐芦草沟,祖国版图上一处火热的圆点 在祖国最西部父亲的能源梦在高高的井架前豪情父亲说,最苦是煤和荒漠但心中有诗和祖国 父亲已逝。
父亲的故事祖国最初的煤事都将是历史或将被人们淡忘,但祖国母亲不会忘你 在我心中,祖国是火与红的七月是雄壮激情的八月是沉甸甸的金秋十月 我的祖国 四十年,依靠在祖国的臂膀见证中国梦的历程那蓝色的大海上,海舰如祖国坚实的铜墙铁臂 父亲的祖国,父亲的煤我接力在改革开放紧跟新时代脚步,在高高的煤山前成熟 每当晴朗的早晨看见渐高刷新的煤山站在祖国大地上为煤,为这片土地吟赋出我最激情的诗篇 墨韵 佳冠图(中国画) □崔涛 乡村 堂嫂和三十斤粮票 □李宏 堂哥比我大五个月,我俩在一个屋檐下长大,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从来没有分开过。
我十八岁那年,公社武装部长给我送来了去云南边疆当兵的入伍通知书,父亲很焦灼,母亲很紧张,家里人很忐忑。
临离开家的头一天晚上,堂哥从兜里掏出两块钱塞到我手里说:“那边还在打仗,枪炮响起来时脑子灵光点,眼睛看远点,想家了买块糖吃。
”从小三天两头与我打架的堂哥这一席话,竟然把我搞得泪崩了,我对堂哥说:“打仗的事你就别操心了,我爸妈有啥困难你多照应点。
”从那一刻起,似乎我俩都长大了,成了顶天立地的男人。
转眼间,我在部队已经呆了四年,身上两个兜的布衣也换成了四全兜的“的卡”。
一天下午,我一身泥土刚从训练场回到营地,通信员就举着一捆信冲着我说:“这几天每天都有你的信呢,好像还有一张照片,是不是你家又给你介绍女朋友了?你得请我喝瓶菠萝汽水。
”我接过信举过头顶,在太阳下一照,薄薄的白纸信封里果然有一张照片。
我从裤兜里掏出零钱递给通信员说:“菠萝汽水管你喝,今后有我的信第一时间送来。
” 躺在草坪上的树荫下,先打开了堂哥写来的信,信封里夹着一张一寸黑白照片。
堂哥在信中说:“我注定要跟在牛屁股后面犁一辈子地了,照片上这个女人就是你未来的嫂子,刚满十七岁,样子生得很漂亮也很贤惠,娘家在靠近陕西那边的大山里,可惜她没有上过一天学。
你可别像哥一样,你得找一个在城里上班的,穿高跟鞋穿喇叭裤烫波浪头的洋婆娘回来。
” 这封信搞得我很兴奋。
我将信反复读了两遍后实在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顾不得一身疲惫便跑了几公里山路去了镇上的邮局,将电话打到了公社的公用电话上。
父亲接电话后责备我说:“这么远打个长途还以为有什么大事呢,也不怕浪费钱。
你堂哥结婚的时间订在腊月间。
只是女方又提出另外还要追加五十斤大米和一辆永久自行车,他家的情况你也知道,哪有钱去置办这些东西,这几天把你堂哥一家人急得都快疯了。
”撂下电话,我原本很亢奋的心情一下子跌落到了谷底。
当时农村刚包产到户不久,堂哥家虽然比我家日子略为宽裕,但由于家里祖孙三代、兄弟姊妹七个,吃饱肚子的事还没有完全解决,置办聘礼已经举债了,再拿出五十斤大米一辆自行车的钱来,确实不是一件小事。
经过一夜的心理较量,我还是在第二天早晨借自行车去了镇上的邮局,我把自己攒下来准备探亲用的三十斤全国粮票和二十元钱寄给了堂哥。
过春节回家时,我终于见到了照片上的堂嫂。
土布衣服难掩堂嫂的漂亮羞涩,脚上的劣质皮鞋上全是泥,头发也有些散乱。
堂嫂一口川北土话大着嗓门对我说:“你寄回来的二十块钱和三十斤粮票救了他的急,不然,我爹是不会让我嫁到他们家的。
”堂嫂还说:“兄弟你放心,我这辈子砸锅卖铁也得把欠你的粮票还上。
”堂哥说:“女人家惦记的都是这些陈年旧事,你寄钱和粮票的事她
一 直挂在嘴上,前几天去县城,地摊上有人卖全国粮票做纪念品,她还说要买了送给你呢!被我骂了一顿。
” 转眼三十年过去了,世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这期间我从云南到山东到江苏又到了北京,始终在军营里摸爬滚打,我与堂哥堂嫂两家人也都建了新房不再同居一个屋檐下了,我们从青涩少年变成了小老头儿,见面和写信的机会也就少了许多。
父亲过世那年,堂哥带着他妻子孩子来我家奔丧,我突然感觉堂嫂一下子变得很苍老,头发枯黄了,皮肤变糙了,背也有些驼了,完全没有了当年照片上那个女人的水灵样。
堂嫂一边做事一边难为情地对我说:“现在粮票已经作废了,还不上你的情了,这几天忙完一定来我家,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我说:“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过去多年了,谁说过让你还?那算是我随的份子。
” 堂嫂去池边洗菜的功夫,母亲对我絮叨说:“你堂哥整天看些莫名其妙的闲书喝寡酒,除了下河捞沙下地种田,家务事孩子上学一概不管不问,全靠他女人里外张罗。
”我问母亲:“他们家日子过得不好?人咋变得这么苍老?”母亲说:“这女人心强好胜,别看她大字不识一个,却一门心思要培养娃儿读书,儿子培养得一个赛一个有出息,老大西南财大还没毕业就被银行挖走了,老二又是全县的高才生,听村里人讲,考上川大重大没有问题。
”母亲的话,让我对堂嫂有了更多的敬重。
转眼到了今年七月,我回四川参加一个评审会,会议结束时我顺道回了一趟乡下。
车过堂哥家二层楼门口时,我问邻居:“堂哥家咋没有人呢?是下地干活了吗?”邻居告诉我说:“你堂哥两口子现在洋盘了,经常到外地旅游,刚从大理丽江回来,现在又去香港澳门旅游去了。
你没有你堂哥的微信呀,里面全是他们旅行的照片,你看看就知道他们现在的光景了”。
我从邻居那里要了堂哥的微信。
果然,里面全是一家人外出旅行的照片。
有在澳门大三巴牌坊前的,有在丽江古城的,有在紫荆广场的,堂哥堂嫂真的变得年轻洋气了,竟然还用上了抖音。
这天晚上回到驻地,我给堂哥写了一条微信:“缺粮票缺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享受阳光享受生活,真心祝福你们!”但最终,我还是将这条微信删了没有发出,我在心里默默祝福他们! 刊头题字 刘炳森 本报所付稿酬包括作品数字化和信息网络传播的报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安苑北里22号邮政编码:100029办公室(:010)64810369广告部:(010)64812322发行部:(010)64811201广告发布登记证:京朝工商广登字20170068号中国青年报社印刷厂印刷零售价:1.00元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