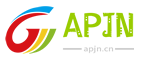著肖茜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前言效率的七宗罪第一章从工厂到平台第二章信息爆炸的初衷落空第三章教学机器的幻影第四章移动目标第五章身体管理第六章缺乏灵感致谢版权页
前言效率的七宗罪
为什么效率仍然只是半成品
人人都渴望效率,甚至赞美效率,这是不言而喻的。
但本书恰恰要批判效率(除非它是低效率)。
本书讲的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
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
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
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
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
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
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
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
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
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
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
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
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
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
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
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
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
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
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
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
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能放入电 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
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
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
(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1]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
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
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
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
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和罗伯特·
J.戈登(RobertJ.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重复了他在2000年的预测,即到2020年,人们仅花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2]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
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
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
我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
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
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
A.罗斯(EdwardA.Ross)在1900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
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
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
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
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
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在30多年前的1987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
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3]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
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 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
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4] 关于效率的其他许多告诫并不是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事项。
首先是能源问题。
质疑强制性能源效率目标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到了所谓的“反弹效应”,即效率更高的技术所节省的成本会被消费的增长所削弱,甚至完全抵消。
19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在英国的煤炭消费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而且随着每一次新的节能创新,类似情况都会再次出现。
能源成本的降低通常会被用来购买运动型多功能车和豪宅,更高效的空调技术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房间安装空调,或者用中央空调取而代之。
这种影响远非铁律,就连其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罗伯特·
J.迈克尔斯(RobertJ.Michaels)也承认,冰箱的强制性效率标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反弹。
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确实存在。
从LED照明到电动汽车的技术效率提升被从稀土矿开采到电子垃圾导致的环境破坏所抵消。
[5] 其次,紧随能源之后的是对农业效率的批评,这类批评通常来自左翼。
在农民和农场主的人均产出方面,常规的机械化农业一直表现突出。
然而,瑞典农业科学家费尽周折地重新衡量了能源投入和产出,最近却证明,一台拖拉机所需的能源比耕作同一片土地的马所需饲料的能源要高出67%。
拖拉机的效率远远高于马匹,它带来的产量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马匹在同一块地上生产出食物的2.5倍,但它所需的能量却是马匹的13倍。
我们的农业还面临其他的反对声。
对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进行快速采收和屠宰的效率,往往损害了营养价值和口感。
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种植的西红柿开始卷土重来。
为高效出栏而饲养的猪和鸡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牛的生长激素虽然是“天然”的,而且对人类是安全的,但它却会导致牛奶产量达到极限的水平, 这一水平对奶牛来说是痛苦的。
对效率的追求可能会鼓励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单一种植方式,比如在爱尔兰大饥荒前,土豆在其农业中占主导地位。
由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所有土豆的基因完全相同,因此源于新大陆的疫病毁掉了1845年的收成。
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在《欲望植物学》一书中所说,“单一化是自然逻辑与经济学逻辑发生冲突的地方,哪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是毋庸置疑的”。
[6]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
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
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一本关于其悖论的书就将包罗万象。
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
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甚至连拒绝这种理论限制并倾向于将太空探索视为突破所有地球资源限制方案的硅谷文化,也认识到效率过高导致的环境、健康、文化和伦理成本。
尽管拥有智能住宅、联网设备和自我监控装置,效率助手还是知道如何划清界限。
从有机产品的生产到(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没有技术的鲁道夫·施泰纳小学,手工价值观的成果吸引了许多高科技家庭的注意。
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低效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可靠和特权的标志。
这个新的上层社会阶级似乎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的“强盗男爵协会”没有共同之处。
在镀金时代,富豪阶层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价值观也许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人们认为它们甚至比不道德更糟糕,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
弗里克收藏馆和摩根图书馆等的旧瓶装新酒也是如此,早在1970年,经济学家 斯塔芬·林德(StaffanLinder)就出版了他的开拓性著作《受折磨的有闲阶级》。
当今的科技巨富们更有可能是在寻找下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在提前退休后享受最后一次创业所带来的财富。
然而,就像在凡勃伦时代一样,炫耀性的低效拥有特权。
正如科技记者戴夫·罗森伯格(DaveRosenberg)2013年在《旧金山纪事报》网站上指出的:“奢侈品,尤其是手表……是硅谷向往高质量精雕细琢的手工工具、服装和配饰的微妙追求的一部分……当普通人期待最新的未来主义身份象征时,技术未来主义者却在复古。
”其他劳动密集型工具也是如此,比如,手工锻造的厨师刀大受欢迎。
[7]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
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
(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极端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
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1986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
)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
阿瑟·
M.奥肯(Arthur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2015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
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
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
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
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8]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最佳理由。
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
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
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
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
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
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
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
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9] 对移动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指向了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不管是商业关系还是个人关系。
美国人至少一直对商业关系没什么感情,甚至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他们就抛弃了当地的大型百货零售商。
虽然许多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在社交媒体对注意力集中和 人际关系的影响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在硅谷的许多文化中,磨耗仍然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10] 对于效率拥护者来说,硅谷内外的反对声只是下一轮算法技术能够解决的暂时性问题。
“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机器人的倡导者可以指出先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同样落空了。
效率仍然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虽然硅谷的亿万富翁现在面临着更多质疑,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作为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美国文化缔造者继承人的衣钵。
史蒂夫·乔布斯有时和他们一样冷酷无情,但仍然受到数百万人的广泛怀念,因为他们相信乔布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对技术效率提出了不同的批评意见,它接受减少人力和自然资源浪费的目标,但也承认,正如比尔·盖茨及其合著者在1995年所说的那样,一心一意推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实际上可以提高效率。
它没有研究信息技术面临的所有社会、政治和伦理挑战,而是关注其带来的长期自我颠覆。
我们知道,对儿童卫生的过度关注会削弱免疫系统,过量使用抗生素会滋生超级细菌,滥用阿片类药物会降低其有效性并成瘾,习惯性地依赖安眠药会加剧失眠。
很少有人放弃药物,同时我们对自然平衡又有了新的敬畏之情。
现在,质疑效率必须超越效率和有效性之间的常见差异。
考虑到击败敌人所需的子弹或炮弹的数量,战争是极其低效的。
但由于战争失败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此,效率低下也会带来有效的结果。
反过来说,“清洁柴油”汽车发动机在燃料消耗方面是高效的,但由于它们的排放难以控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算法——使计算机硬件能力倍增的编程技术——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它们既高效又有效。
例如,尽管遭遇了许多成功的攻击,但公钥密码术利用了解析非常大的数字的难度,以确保电子金融交易的安全和互联网通信的总体安全。
从长远来看,其他算法可能不仅会危 及效率,还会危及有效性本身。
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
它们可以被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
一,反偶然性。
大多数偶发事件都是不利或中性的,效率使世界变得更可预测。
但是,如果一切都尽可能直截了当,我们也会失去邂逅偶然的随机化和生产性错误的好处。
传统算法以限制正面影响的高额代价来减少负面冲击,二者密不可分。
第
二,过度关注。
效率通常表现为专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和必要的。
但进化却给我们和其他动物提供了第二种视角,即周边视角,它对细节不那么敏感,但能让我们看到较大的图案和动作。
在天文学的早期历史中,人们就知道通过稍稍远看,“偏向视觉”可以更好地看到不显眼的物体。
正如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一书中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到一颗星星,可以通过将其转向视网膜的外部侧面来进行观察,这样更容易受到微弱光线的影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颗恒星。
” 第
三,自我放大量级。
效率在日常操作中不可或缺,不管有意无意,算法都可能无法通过放大最初的细微效果来做出最优选择,其早期的选择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是自动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风险,从金融交易到自动驾驶都会遇到。
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算法——其中没有一种是完美无瑕的——相互作用,有时不可能进行快速的人工干预。
第
四,技能腐蚀。
自动化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
它们几乎总是更加高效和连贯,这就是它们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原则上,一名技术人员和电子系统的合作比任何一方都能提供更好的业绩。
但当机器人伙伴发生故障时,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
如果人类,不管是医生、飞行员还是普通的驾车者,没有掌握相关技能,结果将会对整个系统的效率造成灾难性影响。
第
五,固执反馈。
当要求自动化系统不仅执行人类目标还提供激励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得更加棘手。
通过不满足真实预期结果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标准(如考试分数)是有可能的。
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为坎贝尔定律。
第
六,数据泛滥。
当精通基本流程的技术人员使用巨大的数据集时,可能会提高效率。
但使用这些数据集也会威胁到效率。
在许多领域,自动获取的数据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数据的存储成本,从而增加了支出。
大数据还可能提示假阳性和错误的假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评估和排除,从而导致(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警报过多和警觉疲劳。
最终可能造成实际效率下降。
第
七,单一文化。
如果没有细心的设计,算法可能会制定成功公式,使系统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应能力降低。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承认,他们的一些实验无法被复制,不是因为最初的设计、分析或数据收集有任何错误,而是因为社会及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生命科学家使用的老鼠的基因是标准化的,但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技术环境中,而且会经常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撰写关于信息技术的文章,就是要瞄准一个似乎不仅在变化而且还在加速发展的目标。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有许多其他书涉及同样的问题。
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网络技术非但没有扼杀印刷书籍的出版,反而有助于增强印刷书籍的出版。
网络上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是网络本身。
2017年5月,一篇维基百科类文章列出了49页关于互联网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新的重要作品尚未被收录。
亚马逊仅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分类下就列出了超过2.4万种图书。
这是该章将讨论的信息丰富性的一个突出例证。
[11] 虽然这些书中有许多是技术专著或大学教科书,还有一些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库或社会实验的初步研究报告,而其他一些 (如本书)则是对它们的解释。
有很多重复的研究援引了类似的证据,这些研究可能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平行的想法和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一拥而上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文学理论家早就对互文性进行了阐述,而早在1898年,小说作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t)就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来自北方的男人》中,更生动地将雄伟的大英博物馆圆桌阅览室描绘成一场由推着书车的侍者来回服务的“活人对死者的食肉盛宴”。
[12] 因此,在大约125年后,我应该给这本书找到什么样的定位?凯文·凯利的《技术想要什么》和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显然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技术乐观主义是好事。
鉴于令人沮丧的创新失败率,就连不切实际的希望也有助于为潜在有益的发明筹集资金。
宣传炒作不总是对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或消费者有好处,但可能对社会有好处。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Bostrom)的《超级智能》等技术预言家的作品。
快乐和恐惧的预言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点。
它们都预见到了人类的转变,它们仅在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的问题上意见不
一。
[13] 效率悖论是对技术乌托邦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作者提出的问题之
一,他们未必会对崩溃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有一些问题尤其值得讨论。
硅谷最彻底的反对派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他将思辨的头脑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结合在一起。
莫罗佐夫早年生活在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这让他意识到规划者的傲慢。
他成长于一个浓厚意识形态的社会,对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崇拜者的缺点有着敏锐的眼光。
他的著作《技术至死》批评了他所谓的解决主义(采纳自建筑评论家的一个概念),即认为人类问题完全可以用技术进行补救的观点。
他认为对效率的追求忽视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后果,以及毫无根据地将创新等同于改进。
他同样会称之为“新效率”的是“效率低下、模棱两可和不透明的,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掌权的极客和解决方案制定者毫无疑问地会一道提出反对意见”。
莫罗佐夫 观察到,“恰恰相反,这些恶习往往是伪装的美德”。
事实上,他反对“互联网”的存在本身,反对利用网络资源的强大组织提出的议程。
同时,他嘲笑一些网络批评者试图推广他们自己的进步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更有效的沟通没有也不会解决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14] 用莫罗佐夫的话说,我可能是一个“技术结构主义者”,不太关心“直接、有预期和理想的创新后果”,而更感兴趣的是“间接、意外和不受欢迎的后果”。
然而,我依然赞同莫罗佐夫的“后互联网”观点,并会援引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WilliamIsaac)和多萝西·斯温·托马斯(DorothySwaineThomas)提出的托马斯定理。
即如果人们相信某样东西是真的,那么它的后果就是如此。
举一个平淡无奇的例子,有关汽油短缺的假新闻有时会造成真正的汽油短缺,因为惊慌失措的司机会更频繁地加满油箱。
与控制有影响力的网站的人的操纵相反,“互联网”可能是一个神话,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谷歌和脸书网站算法的中立性,那它就成了现实。
由于基于网络的商业和出版不会消失,而且它们已经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结果,我认为应该接受这种情况,并找到新的方法来融合直观和算法,模拟和数字。
值得赞扬的是,莫罗佐夫并不惧怕否定,正如我不惧怕消极一样。
我记得我的本科老师、科学史学家查尔斯·
C.吉利斯皮(CharlesC.Gillispie)在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受过教育的人所面对的尴尬莫过于真正的陈词滥调。
”[15] 为了拯救这一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在《玻璃笼子:计算机如何改变了我们》中把效率确定为其价值观和战略的核心,如在谷歌的案例中,其核心表现为“固执到近乎偏执”。
该书还正确地强调了过度依赖算法会侵蚀人类技能的危险,卡尔在他的前一本书《浅薄》中有力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从相似的事实和研究中,本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卡尔是一名幻想破灭的信息技术专家,而我是一名历史学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发现,先是文字处 理,然后是电子图书馆资源帮助我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写作生涯。
因为我在研究方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信息技术成了一个乘数。
对技术影响的悲观看法分散了人们对教育和自我学习的真正需求,他们认为这是将算法与直觉、数字与模拟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16] 我认为是技术策展人詹姆斯·布莱克比(JamesBlackaby)最早提出了“玻璃笼子”的观点,即当我们从工具使用(老式的木工凳)转向工具管理(19世纪创新的工作台)时,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
布莱克比展示了计算尺比几十年前取代它的电子设备要求工程师更直接地参与计算。
工程师、技术史学家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Petroski)最近也表达了这一点。
卡尔没有呼吁恢复18世纪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他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的一首十四行诗,称赞西塞人在农业生产中实现了身体和工具的统
一。
卡尔并不孤单,手工割草是一种兴盛的小众爱好。
多亏了现代搜索引擎,未来的割草机可以选择来自奥地利、意大利、丹麦和澳大利亚的镰刀。
人们还能找到其他有关手工工具的文学作品,比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俄罗斯农民的锻炼方式》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这让人想找一个草场,然后转身离开”。
在这种人与工具关系的启发下,卡尔对莫罗佐夫所谓“技术把我们从苦力中解放出来”的简单想法嗤之以鼻。
(这是对莫罗佐夫关于卡尔的“麦克卢汉式中庸主义”言论的回应吗?)但我怀疑,与更多的诗人和小说家相比,那些前现代的农民对在收获季节要从黎明到黄昏,一直为生计疲于奔命的状态肯定不大满意。
老彼得·布吕赫尔(PeterBruegel)的画作和版画对其中人物的肌肉力量、疲劳和饥渴的形象都经过了程式化处理,但也可能是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
因此,我不同意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有更多“漫无目的和沮丧”,恰恰相反。
不能仅仅因为加入手工制作俱乐部更容易,就觉得它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
相反,我同意诺贝特·维纳(NorbertWiener)的观点,即如果运用得当,信息技术可以让我们摆脱头脑麻木的常规状态,从而腾出时间进 行更具创造性的活动。
使用羽毛笔时,工具、手和头脑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它可能强制人们刻意书写了如此多的文学经典,但我很高兴自己不需要被逼着使用羽毛笔了。
[17] 凯茜·奥尼尔(CathyO'Neil)的《数学毁灭武器:大数据如何加剧不平等和威胁民主》一书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警告。
与大多数技术批评者不同,奥尼尔一直站在发出警报的系统最前沿,认为无论是在工作场所的“健康”计划中,还是在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活动中,抑或在司法系统中,弱势人群都被算法瞄准成为目标。
她的愤世嫉俗使她的书成为迄今为止网上被广为评论的关于大数据和算法伦理的著作。
但在医学上,治疗比诊断更具挑战性。
她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审视的提议引发了质疑。
首先,其他许多理论家和技术专家认为,有了机器学习,就不再能以研究常规程序的源代码的方式来理解人工智能了。
目前尚不清楚,即使最初的代码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吸收了大量新数据后,该程序的最终行为是否也能为人类所理解。
如果这些专家是正确的,那么只要走得足够远,就会创造出一台人类理性难以理解因而也无法审核的黑匣子机器。
其次,即使软件及其隐含的偏见是可以理解的,审视中也不乏令人沮丧的先例。
谁能忘记安然丑闻后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倒闭,以及其他大型会计和债券评级公司未能质疑导致2008年经济衰退的做法呢?为了客观起见,法官保护法医学和量刑软件不被披露和有效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偏见的算法或许会取消与证人对质和反驳证据的权利。
[18] 法律学者弗兰克·帕斯卡尔(FrankPasquale)《黑箱社会》一书的出版先于《数学毁灭武器:大数据如何加剧不平等和威胁民主》,这本书至今仍是对立法者和监管者面临的来自秘密算法力量挑战的最佳论述。
帕斯卡尔建议采用欧洲管理大数据的方法,我也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经验。
但善意的隐私法是一把双刃剑。
被庄严载入欧盟法律的“被遗忘权”或许是为了从搜索引擎结果中删除年轻人年 少轻狂的印记。
但是,保护无权无势者的法律也可能保护特权者。
《每日电讯报》刊登了在被调查者提出异议后被删除的报道摘要,其中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军官和一名涉及性侵案件的神职人员。
当然,新闻报道可能是不公平或不准确的,但删除已公布的信息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帕斯卡尔的书和奥尼尔的书在揭秘硅谷方面互为补充。
他们担心的是对社会的影响。
奥尼尔对当今算法的良好运行印象深刻,这使得它们更加危险。
我自己强调的是,为什么算法的短期效率会阻碍创新而不是刺激创新。
[19] 大卫·萨克斯(DavidSax)的《模拟的复仇》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化学胶片到机械手表再到零售商店等旧媒介和体验具有极强的弹性,能够提供数字生活无法满足的人类需求。
自2001年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专卖店以来,从苹果专卖店的蓬勃发展,到笔记本再次广受欢迎,都生动地说明了触觉、具体体验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硅谷对它的认可。
这是对算法和人类直觉共存表示乐观的最佳呈现方式之
一,也是本书的主题。
[20] 但自从苹果专卖店出现后,乌云又重新出现了。
例如,从开业到2017年春天,美国百货商店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3。
虽然仍有实体利润市场,但除沃尔玛外,历史悠久的大型连锁超市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亚马逊竞争。
西尔斯和梅西百货这两家大型连锁商店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萧条和衰退后,在2017年处境艰难。
亚马逊自己的零售部门不大可能提供苹果专卖店里那种现场设备调试以及个人支持和维修服务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感觉。
宝丽来专利的新拥有者或许已经恢复了即时摄影,柯达公司也宣布了Ektachrome彩色幻灯片胶片的回归,虽然柯达的彩色胶片Kodachrome可能永远消失了,但35毫米电影胶片的制作仍在继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著名导演对制片公司和放映商的影响力。
[21] 经济学家兼作家蒂姆·哈福德(TimHarford)撰写的《混乱》一书在2016年问世,对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业模式进行了令人欣喜的纠正,之前的商业模式倡导组织、系统和有条不紊的习惯。
在大西洋两岸,厌倦了管理术语的公众为甜蜜的混乱而欢欣鼓舞,因为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绝佳的证明,即无序可以是有创造力的,即便它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反例。
包括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Schultz)的《错误》和哈福德早些时候的《适应》都提到了这一点。
然而,和其他大多数商界领袖一样,哈福德低估了运气的作用。
借鉴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研究以及最近有关投资和管理回报的研究,金融经济学家摩西·利维(MosheLevy)认为,归因于人才的大部分超额收益可以归结于运气。
就像哈福德的幸存者偏差所反映的,关于成功的叙事只关注引人注目的例子,却没有考虑到有很多具有相同的特征、经历或战略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
就像在华尔街一样,在一种市场环境中表现出色的风格也可能在另一种市场环境中遭遇失败。
考虑一下硅谷的大赢家的特点——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就出现在《混乱》里,我们从书中能发现他们高超的战略。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潜在的致命危机。
[22] 赢得竞争的“混乱”行为可能在权力分配方面导致无所适从,哈福德大胆赞扬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即兴风格,但使特朗普成为成功竞选者的原因似乎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未能获得广泛认可。
当然,另一位声名狼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赢得了连任,躲过了丑闻和弹劾,并仍被数百万人怀念,因此,哈福德或许是对的。
然而,批评人士也指出,混乱是导致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毁誉参半的原因之
一。
[23] 在最好的情况下,混乱充分说明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提出的“计划中的成就实际上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产物”。
但混乱并不是什么口号。
首先,字面上的混乱将付出高昂代价。
寻找放错位置的物品和文件所浪费的时间,或许没有得到真正科 学的估计——相关研究似乎是由销售追踪密钥和商业记录解决方案的公司资助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发现,创造力带来的混乱可能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平息。
其次,至少一位被哈福德描述为混乱的人,如查尔斯·达尔文可能曾经同时从事多个研究项目。
但达尔文是一名谨慎而有条理的人。
在剑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当年做的标签仍然受到高度重视。
最后,公司管理层并不真的相信绝大多数员工会在混乱中做出贡献,符合要求才是主流。
高效的绩效监控软件让大多数普通员工(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会发生创造性错误。
混乱可能只是另一个身份标志,是休闲过度阶级的特权。
研究人员指出,精英阶层会通过不合乎常理的行为来表明他们对大众标准并不在意,比如,脸书网站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就会在正式场合穿连帽衫,这种行为也被称为“红色运动鞋效应”。
这也难怪,因为哈福德的雇主、总部设在伦敦的《金融时报》在2017年5月说,该报读者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受众,拥有最强的购买力和最高的净资产”。
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财富金字塔最上端1%的水平,那就不要轻易尝试扎克伯格的做法。
[24]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另外两本书出现了:媒体研究学者、前音乐巡演经理和电影制片人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Taplin)的《快速行动,形成突破:脸书,谷歌和亚马逊如何造成文化困境和破坏民主》,作家、《新共和》的前编辑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Foer)的《不在乎的世界:大科技对生存的威胁》。
我没有机会仔细阅读它们的论点,但我同意(使用类似的统计数据)平台经济给许多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和音乐家带来了经济损失。
我就是遭遇损失的一员:我撰稿的《威尔逊季刊》《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文明》,以及其他杂志不再出版了。
我也赞同福尔对追求数字效率和点击量可能损害质量的分析。
尤其是脸书控制了越来越大的广告份额,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现在只能就这两本书的书名发表两点初步评论。
首先,本书不只讨论媒体和艺术,还涵盖了更多 的专业领域,会讨论移动计算、应用程序和大数据兴起的积极和消极后果。
其次,尽管拥有数千亿美元资产的精英在理论上能对决策产生影响,但在2016年,他们无法阻止一位在气候变化、移民、多元化和婚姻平等等问题上持反对立场的总统候选人当选,即使他们很多人对此表示遗憾。
亲特朗普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一篇文章支持拆分谷歌。
民主——或者至少是选举中的多数派——对硅谷带来的威胁可能要比来自硅谷自身的威胁更大,反之亦然。
[25] 《效率悖论》将两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联系起来。
第一个时代始于18世纪末,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
这个时代用连续的生产过程代替了离散的生产过程,带给了我们工业化的经典形象:纸卷、线轴、钢丝,以及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展示的经典流水线。
当然,这些产业只代表了工业国家产出的一部分,但连续生产过程的理想激励了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多亏了工业机器人,连续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劲,但它却失去了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带来的激情。
平台公司用软件将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效率。
这并非基于机器和人力的组织化,而是基于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换。
随着搜索引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网络软件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低潮中复苏,亚马逊网站开启的平台时代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正在研究这种新效率在媒体文化、教育、交通和医疗四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并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效率带给大多数人的好处难以捉摸。
我的结论是,我们不必要么选择大数据、算法和效率,要么选择直觉、技能和经验。
我们需要适当的融合,我将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套策略。
我将在第一章中提出,平台效率的问题在于,它促进了“颠覆性创新”概念的提出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业务流程创新。
它用自动化软件来匹配买卖双方,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效益是实实在在的,却也是有限的。
平台公司可以通过控制通胀来促进竞争,造 福消费者。
风险也是切实存在的,而且已经被批评者充分记录在案。
目前的寡头垄断以及潜在的垄断带来了消费者隐私权的丧失,有时服务协议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样板[Archicany的协议声称对客户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数据拥有广泛的所有权]。
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个结果是华尔街对平台效率的浪漫化。
它分散了资本和人才,使他们无法集中从事风险更大、最终更为广泛的创造市场的创新。
19世纪持续不断的工艺创新不仅减少了损耗,在取代某些工作的过程中,它们也创造了许多其他工作,这些新的工作往往技术性更强,薪资更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阶段的技术迭代是一次性事件,永远不会重演。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基于对最近记录的推断,有关未来的任何说法都可能是不准确的。
[26] 第二章转向所有算法中最强大的算法——谷歌的网页排名带来的革命,其根源在于对科学影响力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的出现和之后社交媒体的出现,这种最初的精英主义技术变成了一种民粹主义大环境。
在新闻和艺术领域,非但前《连线》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畅销书排名榜以外的大量作品)概念无法适用,反而使随机的初始优势成倍扩大,形成了连锁效应。
移动计算、社交媒体,以及新的、据称更精确的广告选择的兴起,同时也威胁到了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效率,因为它把资源从新闻生产转移到了社交媒体算法优化上。
第三章探讨教育领域的效率运动。
高等教育中的计算机化运动至今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爱迪生的一个梦想,即用100%高效的课堂电影取代他认为的“2%效率”的教科书。
尽管电脑在自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但无论是在考试还是在流行文化中,都没有证据表明电脑在提高大众识字率和算术水平方面有所斩获。
事实上,它们通过增强早期起步时建立的优势,一直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
第四章探讨了数字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引发的地理革命。
它把寻路与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即在没有指南针甚至地图的情况下,人们所使用的技巧。
在寻路方面,我们的技术已经变得更加精确,而又没那么复杂。
电子地图,尤其是显示在小屏幕移动设备上的电子地图,在提供关于特定地点的信息方面极为有效,但在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范围内则表现得远没那么出色,提供的信息很少。
很多时候,智能手机全球定位系统提供的直接路线恰好是我们需要的,人们都不想绕道出行。
不过,最快的路线不一定是最有效地安排旅程的路线。
全球定位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比人类自己找路更有效,但它可能是削弱人类最有价值的技能之
一。
第五章关于医学,探讨了提高医疗效率的计划对有效医疗造成的障碍。
实验室自动化是计算机化的杰出成就之
一。
现在,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中产阶级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到目前为止,对遗传信息的解析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电子病历曾经承诺要减轻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书写病例的负担,尤其是因笔迹模糊闻名的医生。
但事实相反,对一致且详细的病历的需求增加了这些人的负担,创造了新的代码输入管理,以及一个家庭手工业的辅导机构对程序进行分类以获得最大的费用。
即使获得成功,医疗量化也会受限,因为患者并非被动接受干预。
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对生活和对风险的态度,以及与医生的关系无法与结果分开。
虽然劝说的过程效率低下,但专业人员引导健康选择的能力往往比药物更重要。
与一本书构建起一种场景类似,一张大幅的地图不仅是其细节的总和,而且是一个应该作为整体来理解的领域,因此,患者的身心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组注释和数据点,尽管这些数据可能是有帮助的。
[27] 最后一章提出了关于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异端观点。
对计算机所擅长的细节的极限记忆可能不利于理解,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并不奇怪。
借鉴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Collins)在《人工专家》一书中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每个人都掌握着大量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是 不可能在有生之年传授给人工智能程序的。
在我们做出职业决定或购买选择时,这些直观的理解都会发生作用,还会影响我们的教育、地方经验以及健康。
其结果是,更多的算法应该是效率最低的方式,因为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正如某些搜索引擎研究人员所主张的),并提供假设性建议而不是明确的答案。
算法可能是偶然的,但并非一定如此。
它们真正的挑战在于分析熟悉的问题,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的市场调查,通过科学验证的既定模式得出的数据,可能被永远无法预测的方式创造性地颠覆。
市场调查曾宣称美国人喜欢廉价咖啡,但后来星巴克横空出世。
当然,毫无根据的直觉常常失败,这也是事实。
但行为经济学的发现不应对我们的直觉进行压制或恐吓,数据分析和隐性知识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对立的。
[28] 算法本身需要并且正在获得新的方法。
被称为模糊逻辑的编程技术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接受了需要的次优解决方案。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担任研究员的凯瑟琳·德尼加齐奥(CatherinD'Ignazio)发现,主要的搜索和媒体公司一直努力在服务和推荐中增加偶然性和信息多样性,但这并非易事。
如果可以应用更复杂和更有洞察力的算法,那么它们很可能源自学术项目和初创企业,而不是大型平台公司。
这些举措以及新一代对数字思维和模拟思维互利共存的洞察力,使我希望技术在金融危机和停滞不前之后能够再次实现自我更新发展。
[29] [1]“Newspapers: Fact /2015/04/29/newspapers-fact-sheet/. Sheet,” [2]RayKurzweil,TheAgeofSpiritualMachines:WhenComputers ExceedHumanIntelligence(NewYork:Penguin,2000),105;RayKurzweil,“The ComingMergingofMindandMachine,”ScientificAmerican,March23,200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8), /article/merging-of-mind-and-machine/. [3]Edward
A.RossquotedinHerbertM.Kliebard,TheStrugglefortheAmericanCurriculum,1893–1958(NewYork:RoutledgeFalmer,2004),76–78; YoramBauman,“Solow's‘ComputerAge’Quote:ADefinitiveCitation,” July14,2010,puter-age-quote-a- definitive-citation/. [4]“JulesVerneuratelyPredictsWhatthe20thCenturyWillLook LikeinHisLostNovel,ParisintheTwentiethCentury(1863),”OpenCulture,January25,2016,/2016/01/jules-verne- urately-predicts-what-the-20th-century-will-look-like.html. [5]Robert
J.Michaels,“EnergyEfficiencyandClimatePolicy:The Rebound Dilemma,” /wp- content/uploads/2012/07/NJI_IER_MichaelsStudy_WEB_20120706_v5.pdf. [6]Mick
Hamer,“HorsePowerBeatsDiesel,”NewScientist,July13,2002,11;MichaelPollan,TheBotanyofDesire(NewYork:RandomHouse,2001), 230–31. [7]DaveRosenberg,“SiliconValleyTechiesTurnBackTime,”SanFranciscoChronicle,March9,2013;seealsoMattRichtel,“ASiliconValleySchoolThatDoesn'tCompute,”NewYorkTimes,October23,2011. [8]NelsonD.Schwartz,“TheMiddleClassIsSteadilyEroding.Askthe BusinessWorld,”NewYorkTimes,February3,2014;DavidK.Randall,“OnlytheStoreIsGone,”NewYorkTimes,February19,2006;ArthurM.Okun,EqualityandEfficienc:TheBigTradeoff(Washington,
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15);FredHirsch,SocialLimitstoGrowth(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8). [9]EvgenyMorozov,ToSaveEverything,ClickHere:TheFollyofTechnologicalSolutionism(NewYork:PublicAffairs,2013),313–14. [10]MikeIsaac,“Uber'sCultureofGutsinessUnderReview,”NewYorkTimes,February23,2017. [11]/wiki/Category:Books_about_the_. [12]Arnoldt,AManfromtheNorth(NewYork:eH.DoranCo.,1911),69,citedinRoyPorter,“ReadingIsBadforYourHealth,”HistoryToday48,no.3(March1998):11–16. [13]SeemyreviewsoftheoptimisticKevinKelly'sWhatTechnologyWants,IssuesinScienceandTechnology27,no.1(Fall2010), (“Technophilia'sBigTent”),/271/br_tenner-2/;andthe skepticalDavidEdgerton'sTheShockoftheOldintheLondonReviewofBooks,May10,2007(“APlaceforHype”);RaffiKhatchadourian,“TheDoomsdayInvention,”NewYorker,November23,2015. [14]Morozov,ToSaveEverything,
6.Morozov'suseof“solutionism” reflectsacuriousgapintheEnglishlanguage.Foralltheinfluenceoftheefficiencymovementinthelateeenthandearlytwentiethcenturies,therewasnowordforefficiencyasamovement,exceptTaylorism,whichwasonlyonefacetofit.Themovementhaditscritics,butfewdaredcallthemselvesantiefficient. [15]Ibid.,171. [16]DavidCarr,TheGlassCage:HowComputersAreChangingUs(NewYork:
W.W.Norton,2014),211–224. [17]JamesR.Blackaby,“HowtheWorkbenchChangedtheNatureofWork,” InventionandTechnology2,no.2(Fall1986):27–30;HenryPetroski,“SlideRules:GonebutNototten,”AmericanScientist105,no.3(May–June2017):148ff;JeremyHastings,“TheRussianPeasant'sWorkout,”NewYorkTimes,June12,2016;LianaVardi,“ImaginingtheHarvestinEarlyModernEurop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01,no.5(December1996):1364–66;Morozov,ToSaveEverything,20–21. [18]CathyO'Neil,WeaponsofMathDestruction:HowBigDataIncreasesInequalityandThreatensDemocracy(NewYork:Crown,2016),esp.199–218;WillKnight,“TheDarkSecretattheHeartofAI,”TechnologyReview20, no.3(May–June2017):54–63;StephenJ.Dubner,“WhyUberIsanEconomist'sDream,”(includingtranscriptofNationalPublicRadiointerview),September7,2016,/podcast/ubereconomists-dream/. [19]FrankPasquale,TheBlackBoxSociety:TheSecretAlgorithmsThatControlMoneyandInform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15);examplesofdeletedstoriesfromDanielShuchman,reviewofFloyd Abrams,TheSouloftheFirstAmendment,inWallStreetJournal,May8, 2017. [20]DavidSax,TheRevengeofAnalog:RealThingsandWhyTheyMatter (NewYork:PublicAffairs,2016). [21]PaulKrugman,“WhyDon'tAllJobsMatter?
”NewYorkTimes,April17,2017;Sax,TheRevengeofAnalog;onthestateofretailing,see herMims,“ThreeDifficultLessonsforTraditionalRetailers,” WallStreetJournal,April30,2017. [22]TimHarford,Messy:ThePowerofDisordertoTransformOurLives (NewYork:Penguin,2016);MosheLevy,“InvestingIsMoreLuckThan Talent,”Nautilus,issue44(January19,2017). [23]MichaelShermer,“SurvivingStatistics,”ScientificAmerica311, no.3(September2014):94;KarenDamato,“WhenItComestoFund Performance,HistoryIsOftenWrittenbytheWallWinners,”StreetJournal, August6,2012;JamesB.Stewart,“CaseStudyinChaos:HowManagement ExpertsGradeaTrumpWhiteHouse,”NewYorkTimes,February3,2017;DavidA.Graham,“Trump'sDangerousLoveofImprovisation,”Atlantic,August9, 2017;BryanBurrough,“TheSeat-of-the-PantsPresidency,”reviewofNigel Hamilton,BillClinton:MasteringthePresidency,WashingtonPost,July15, 2007. [24]FrancescaGino,“LeadersSayTheyWantNonconformistEmployees. TheySureDon'tActLikeIt,”WallStreetJournal,May17,2017;MatthewHutson,“ThePoweroftheHoodie-WearingC.E.O.,”NewYorker,December17, 2013;“FTAdvantage,”/d/. [25]JonathanTaplin,MoveFastandBreakThings:HowFacebook,Google,andAmazonCorneredCultureandUnderminedDemocracy(NewYork:Little,Brown,2017);FranklinFoer,WorldWithoutMind:TheExistentialThreatofBigTech(NewYork:Penguin,2017);FredCampbell,“TrumpShouldBreakUp Google'sMediaMonopoly,”Breitbart,June21,2017.mentsonFoerare basedonhisacuteanalysisofthetechnologyindustrymentalityatTheNewRepublicin“WhenSiliconValleyTookOverJournalism,”Atlantic, September2017,28–31,whichIciteinChapterTwo. [26]JoelWinston,“TakesDNAOwnershipRights Customers and Their Relatives,” May 17, -takes-dna-ownership-rightsfrom- customers-and-their-relatives-dbafeed02b9e. from
2017, [27]ElisabethRosenthal,“TheCodeRush,”NewYorkTimesMagazine, April2,2017,42ff. [28]StevenPearlstein,“ConsumerConformity:WhyWeLikeThickClam Chowder(andOtherInferiorProducts),”WashingtonPost,July25,2011. [29]Seehersite,/. 第一章从工厂到平台 19世纪的效率如何在21世纪被重新定义 我们生活在第二个注重效率的时代。
记者和企业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使用效率这个词,我们稍后将看到一些同义词。
但是,我们始终意识到,无论是通过增加产量或利润,还是减少时间,都要从现有投入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的价值。
我认为短期内过于专注效率可能会损害长远的效率,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希望表明,人们在对此进行反思时,将它看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
正如我在后文会指出的,将有效的算法与整体的模拟相结合,可以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产生更好的结果。
但这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将效率视为在过去约两百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并将其看作一套更古老的实践会很有帮助。
正如我们看到的,效率这一概念出现在蒸汽时代,其最佳表达方式不是用18世纪对工厂里的劳动分工来体现(本质上仍然如此),而是用机器连续生产代替手工作坊来作为例证。
最伟大的企业投入了巨大的资金,雇用了10万名甚至更多的工人以保持工厂运转。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等学说都反映了这种模式。
就连共产党政府也羡慕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这一点也不奇怪。
20世纪中叶,瑞士建筑师兼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Giedion)和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
J.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首先强调了不间断(“连续过程”)技术对批量生产的 重要性。
轧辊、皮带和其他设备不仅改变了生产,也改变了消费的性质。
与20世纪50年代在电视上播出的《产业阅兵》系列节目相比,现在诸如《如何制造》之类的有线电视节目揭示了如今工业流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
但是,进一步降低装配线上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效率。
一种新型的企业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经济制高点,主导了经济议程,此前即使是最大胆的未来主义者也没预见到这种类型的企业。
硅谷唤起了人们曾经由东北部和中西部肮脏的工业大都市所激发的钦佩、恐惧和蔑视,尽管乘坐汽车或火车前往芝加哥、底特律或匹兹堡仍然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体验,但旧金山以南的半岛更能令人惊叹财富之巨。
尽管那里的公司服务器群可能并不起眼地分散在全球各地,然而,硅谷巨头们对社会组织的想法与列宁同样激进,他们与古典共产主义一样都对效率抱有强烈的信念。
[1] 这一章将考察连续过程的效率(那是让画家、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为之着迷和敬畏的效率)与平台效率之间的区别。
平台效率更有利可图,但具有隐蔽性,而且需要极大的想象力才能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
比如,网络平台应用的在线匹配不仅利用了集成电路效率的稳步提高,而且利用了巧妙的计算技术,即算法来使电路的运算速度成倍提高。
这种效率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平台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自我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为什么世界各地有的公民对他们的政府如此不满,以至于愿意寻求极端的解决办法?原因之一可能是平台革命一直在将人才和资金从其他可能更具变革性的技术项目中抢走。
我无法确定哪些项目具有潜力,也不排除它们已经很先进并可能很快就将硕果累累。
毕竟,美国在“二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像广播电视和干式复印这样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是在大萧条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展起来的,艾伦·图灵的理论研究也使平台经济成为可能。
问题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对投资者(尤其是早期的投资者)如此有利可图的平台公司一直表现不佳?拥趸会坚持认为,重大创新通常会带来一时的失望,最好的结果尚未到来。
这尤其是脸书及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观点,他在2017年年初发表了一份宣言,承认了错误,并发誓要在脸书用户的帮助下建立更好的社区和更美好的星球。
对许多竞争对手来说,这样的承诺长期以来都是“未来的炒作”“硅谷的万用灵药”——借用失望的技术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版的书的书名。
尤其是对左翼批评者来说,新老板与旧老板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配备了先进的监视和操纵设备,取代了昔日的老派做法。
一些谨慎的记者在扎克伯格等人的宣言中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面临的生存威胁。
我不确定有哪个组织真的有这样的权力。
我将在本章结尾提出,平台效率最严重的意外后果可能是它的机会成本,从长远来看,它对资源的要求将更有助于提高真正的效率。
[2] 效率运动的一个悖论在于,尽管数据令人泄气,但促进效率和理性的创新还是在直觉和情感的驱动下出现了。
这并不意味着直觉比基于数据的分析更可靠,而是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工具永远无法取代想象力来预见人类未来的行为模式。
大多数这样的直觉都失败了,一些例外充斥在励志书籍和商业书籍中。
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很高。
然而,在效率低下的大旋涡中出现了一些世界上最高效的技术。
效率的历史应当从自然本身开始。
正如生物物理学家所发现的,DNA比最先进的技术系统储存的能量更密集,对基因表达的控制使复杂而强壮的生物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发育,果蝇基因组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
进化在优化信息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用有限的资源是我们的生物遗产。
[3] 正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所揭示的,对效率的追求似乎也被纳入了人类生物学。
人类在工具制造方面已经经历了数万年的创新,这些创新有时会进入死胡同,但偶尔也会产生具有功能性的杰作,澳大利 亚原住民的回旋镖或中亚草原游牧民的复合弓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没有比传统方式锻造的日本刀更锋利的刀具,或者比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原住民熟练使用的黑曜石刀更锐利的切削工具呢? 在西方也是如此,许多古罗马的医疗设备都很好地发挥了用途,以至于它们的质量直到现代才被类似的仪器超越。
罗马军队以令敌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集结、修建桥梁和防御工事而闻名。
当时甚至有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并加盖早期商标印章的油灯在市场上销售。
[4] 与50年前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相比,最近的考古学揭示了古代世界更多的动力和技术创新。
例如,奴隶经济并不排斥使用像水车一样省力的工具,就像19世纪初期奴隶制下的甘蔗种植园使用蒸汽机一样,这些改进在实践中提高了效率。
但我们所知道的效率概念在古代生活中并没有明确的提法。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社会)的行政和档案保存系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但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提高产出的理论。
古典历史学家彼得·托内曼(PeterThonemann)强调,罗马社会是建立在庇护、忠诚和义务的原则上的。
没有关于工资、利息或生产率的理论。
威望往往比功能更重要。
书籍被写成卷轴,放在箱子里存放起来。
书写是延续的,字与字之间没有空格。
加上空格会增加莎草纸和羊皮纸的使用量,但会使阅读和教育变得容易得多。
解决阅读的困难——拿着卷轴,确定从哪儿断句——是受过教育的人技巧展示的一部分。
这种低效是一种特点,而不是一种缺陷。
[5] 在欧洲,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是一个提高实际效率的时代。
今天看来如此古怪和老套的黑色手写字体,对那些习惯了它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相对快速和清晰的写法。
罗马人有光学知识、玻璃吹制和冶金技术,能制造出眼镜,但没有市场。
上了年纪的文化人曾经让受过教育的奴隶读书给他们听,罗马人制造了很好的轧布机,可以使用青铜铸造的字母,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印刷。
[6] 到了18世纪,德尼·狄德罗(DenisDiderot)的《百科全书》和他的苏格兰模仿品《不列颠百科全书》总结了几十种行业的知识和进步。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证明了将制造针的整个工作流程分成不同的工序,可以使每个工人每天制造针的数量成倍增加。
在中世纪的波斯,针的制造有更精细的分工。
[7] 19世纪和20世纪的效率意识并不十分明显。
作为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是一位杰出的先驱。
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对衡量一个制针车间比传统车间的生产率高多少感兴趣。
许多产品仍然是根据手工传统和风格制造的,而不是经过系统研究客户需要后推出的。
法国技术理论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曾指出,中世纪晚期为雇佣兵制造刀剑的装甲工匠都遵循一种工艺传统和装饰风格,而不研究战斗的人体工程学。
每个士兵都必须使自己的战斗风格适应其装备,而不是令装备来适应自己的战斗风格。
[8] 没有哪位18世纪的人物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有名,因为他能将实际智慧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尽管或由于他接受正规教育的局限性。
富兰克林和他的同时代人——他从未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并鼓励他人进一步改造——设计的壁炉衬里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壁炉的效率。
但18世纪末的发明家仍然没有用科学的方法量化每单位木材节省的热量。
直到19世纪中叶,像酿酒师和科学家詹姆斯·焦耳这样的思想家才推出了测量热量的统一单位:英制热量单位和公制热量单位——焦耳。
引入现代效率的两项发明是19世纪初其他天才的杰作,现在主要为专家所熟知:装配工人奥利弗·埃文斯(OliverEvans)和造纸商亨利·富德里尼耶(HenryFourdrinier)。
如果我们看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会发现当时许多作坊与达·芬奇或伽利略时代的作坊并没有太大不同。
尽管斯密的分工原则开始传播开来,但作坊主还是 在工人和学徒的协助下制作每种产品。
货物仍然是被单独地或小批量地制造出来的。
[9] 奥利弗·埃文斯是连续过程效率的创始人。
他的知名度不及富兰克林、埃利·惠特尼、塞缪尔·摩尔斯或托马斯·爱迪生,但在两个世纪里,他的影响力至少不亚于这些人。
正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在其经典著作《机械化的决定作用》中所写,在美国出现真正的工业之前,“一个孤独而有先见之明的头脑设计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从一个操作到另一个操作的机械运输可能会将人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就像通过一连串的铲斗将原料运送到磨机的顶部,并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皮带、螺杆和其他连续输送装置输送到铣削的每个阶段。
分开来看,这些环节并不完全是新事物,有些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建立一个能加工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综合系统的想法在提高效率方面仍然是惊人的进步。
埃文斯的系统似乎缺乏富兰克林的说服力,但他具有“远见卓识”,吉迪恩正确地总结道:“奥利弗·埃文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10] 经典现代效率的第二个里程碑是富德里尼耶造纸厂。
从被引入中国直到今天,它在日本仍被应用于和纸制造。
和纸是用纤维制成的单张纸。
技术高超的造纸工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会垄断技术,使书籍和报纸的价格不菲。
一位名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Nicolas-LouisRobert)的法国印刷匠是第一位认识到连续纸张生产潜力的人。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库兰斯基(MarkKurlansky)指出的,罗伯特发明的金属丝框架早在传送带发明之前就使用了同样的原理。
(在1804年,皇家海军在制造压缩饼干时首次使用了这项技术。
)在他的机器中,移动的筛网吸收了湿纤维,就像纸张工匠所做的那样,横向搅拌纸浆以使其均匀分布。
除去水分后,半成品纸被卷到一起,最后被加热以使其干燥。
造纸商亨利和戴维·富德里尼耶对“罗伯特流程”进行了技术改进,但不足以使其实用化,他们被迫宣布破产。
工程师布赖恩·东金(BryanDonkin)根据罗伯特的想法最终制造出了可用的连续 造纸机。
这种复杂的关系揭示了连续过程效率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失败、协作和竞争的结果,甚至比其他创新更重要。
[11] 纸张、面粉和饼干的生产效率体现了两个世纪以来消费品生产的效率。
圆周运动无处不在:在战争中,它创造了左轮手枪和马克沁机枪。
和平时期,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苏格兰引入的不起眼的棉线轴,使艾萨克·辛格(IssacSinger)的缝纫机和服装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整个18世纪,线一般都是由亚麻制成的,仅以绞线的形式出售)。
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发明,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泡最初的市场很有限。
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一支由两个熟练的玻璃吹制工组成的团队要花整整一分钟,才能生产出两个玻璃壳,这一生产方法近两千年来未曾改变过。
由于康宁玻璃工厂几十年来的技术改进,到1926年,新一代自动灯泡机能在24小时里生产出40万个空灯泡。
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先是增加到100万,然后进一步达到300万。
事实证明,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和富德里尼耶对大众阅读和教育非常重要,现在默默无闻的发明家威廉·伍兹(WilliamWoods)也做出了类似贡献,他利用连续过程效率实现了爱迪生发明的灯泡的潜力。
其他机械发明者实现了玻璃瓶和金属罐的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灌装,以及在今天的机械化轮胎工厂中仍然使用的混合橡胶巨型旋转搅拌机。
在农场里,连续作业的收割机取代了镰刀,在20世纪,通过装有连续传送带的烘干机,新收获的谷物得到了烘干。
欧洲和美国的高级奶制品公司甚至在缓慢旋转的牛棚里给奶牛挤奶。
正如吉迪恩所说,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肉类分解流水线激发了以亨利·福特为首的工业家的生产流程。
到20世纪30年代初,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钢板是在一个连续轧制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一过程是由钢铁厂负责人约翰·
B.蒂图斯(JohnB.Tytus)首创的,他的灵感来自其祖父的富德里尼耶造纸机的设计。
[12]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利用了反复旋转运动带来的效率。
从布鲁克林大桥到金门大桥,这些悬索桥的巨大钢缆是约翰·勒布林(JohnRoebling)父子发明的机 械和工人旋转而成的。
就连新闻和文学也是用连续的旋转方法传播的。
巨大的长网造纸机制造出一卷卷的新闻纸,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等报业大亨的高速印刷机提供支持。
[13] 购物和娱乐业发生了转变。
百货公司的顾客通过旋转门进进出出,走过一块块地板和环形楼梯带。
西方主要的铁路不断运送大量货物和数以百万计的乘客,这是成熟的工业时代的终极体现和对管理的挑战。
北大西洋的远洋班轮按照可靠、固定的航程航行,精英乘客开始期待在几百年来闻所未闻的准时准点到达。
如果泰坦尼克号船长因为避开海冰而放慢速度,就像后来的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认为的那样,那么这艘船将会迟到一天,海洋历史学家会因为他的胆怯而不是谨慎记住他(如果有的话)。
[14] 虽然许多新工艺的发明者是从车间里走出来的,有时能积累巨大的财富,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都开始意识到经验技能是不够的。
随着过程效率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套新的价值和一组新的词汇,这被称为第一次效率运动。
它不仅激励了投资者、银行家和有抱负的经理人,而且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投身其中。
19世纪和20世纪初没有单一的工业效率学说,但有一套坚实的假设。
首先是量化理论。
虽然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衡量他的壁炉的输出效率与传统壁炉的输出效率可能并不重要,但19世纪的精英们对测量的热情与日俱增。
新的统计技术使人们能够呈现和评价数据,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会计专业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至关重要。
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Thomson)在1883年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他在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说:“当你能测量你所说的东西并用数字表达时,说明你了解这些东西。
但是,当你无法测量它,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时,你的知识就是微不足道的和难以令人满意的。
”[15] 经典的效率也取决于规模。
虽然进步运动的左派担心垄断,独立的生产者和商人则声称垄断不公平,但左派和右派往往一致认为大公司对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利。
从1875年安德鲁·卡内基旗下的埃德加·汤姆森工厂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多克投产后,正是规模使钢铁厂得以安装最高效、最昂贵的新机械,从而压低了价格,给竞争者带来了压力。
正是规模让约翰·
D.洛克菲勒垄断了石油的分销、精炼和销售,即使在标准石油公司因反托拉斯法被分拆之后,也有很大一部分依旧在发挥作用。
同样是规模使最早的工业机器人成为可能:早在1921年,受福特装配线的启发,密尔沃基的
A.O.史密斯公司就开始出售一种能够每天铆接一万辆汽车机身的机器人。
[16] 伴随着规模增长而来的是科层制和职业化。
就连电报运营商托马斯·爱迪生这样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他们需要高学历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不得不开设新的技术学校和课程的美国大学。
一个又一个以往凭借经验的职业被重塑为需要学校、学位和学术期刊参与的职业,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古根海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商业王国。
需要规范、考试和证书的不仅包括医学、法律和工程,还包括图书馆学、公共会计学、新闻和商业管理学等新的学术领域。
甚至在车间里,也设立了新岗位,如工具室文员,以使拥有高技能的工人尽可能多地使用机器。
[17] 伴随着规模的扩张,规划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
高效的公司不仅规模庞大,足以主导市场,而且能够从内部孵化未来的技术。
通用电气、杜邦、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巨头都为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感到骄傲。
虽然贝尔实验室现在主要因为引入晶体管而闻名遐迩,但就它的研究而言,每一项成果都是重要的。
根据《财富》杂志1936年刊登的两篇令人钦佩的文章所述,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铁路实验室也在对从灯泡到餐车等各种设备的供应进行测试,称“这个国家比土耳其或乌拉 圭更大。
它的整个行为就像一个国家,种种举动关系到数以十万计公民的生活”。
[18] 正如经济学家戴维·韦尔(DavidWeil)在其著作《有裂痕的工作场所》中所描述的,20世纪规模庞大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优势。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能够支付比大多数私营企业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在医疗计划、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熟练雇员的低离职率进一步提升了效率。
[19] 传统的企业效率也取决于与政府官僚机构的关系。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公司高管反对政府的监管,并推荐自己的管理方式。
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公司非常依赖政府合同,这种依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深。
技术史学家已经证明,当可互换部件的理想在技术上仍然有挑战性和高昂成本时,国家军械库是如何促进大规模生产的。
IBM被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是因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雇主提出了记账要求。
IBM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销售大师托马斯·沃森只是凭直觉认为,世界很快就会需要他所储备的昂贵设备以及他的研究实验室在大萧条早期开发出来的创意。
他更理性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败下阵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仙童半导体生产的集成电路的早期市场几乎完全与军事和太空计划有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关于国防合同的严格规范也在20世纪中叶提升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其他相关公司的产品可靠性水平,否则这些公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一标准。
[20] 企业高管认为,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规划未来的技术。
有些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博览会上布设展台,试图用它们在设计图上创造出的奇迹来鼓舞公众,包括需要政治批准的基础设施改建。
“二战”结束后,管理学者和专家鼓励企业领导人将自己视为国家未来的私人规划者,为所有利益攸关方谋福利。
有人质疑,贝尔系统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和IBM等是否能为了公 共利益无限制地进行管理创新。
既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的实验室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为什么它们不这样做呢?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像宝丽来、微软和苹果电脑这样的新公司一般都是为之前的大公司提供补充,而不是对其造成威胁。
就连施乐公司——或许是战后时代最初的颠覆性公司——都没有在摄影方面与柯达公司竞争,也没有与IBM在计算机硬件方面竞争,尽管其同样拥有出色的研究人员。
最后,20世纪的效率是精英主义的。
正如塞缪尔·哈伯(SamuelHaber)、托马斯·
C.伦纳德(ThomasC.Leonard)和其他人所证明的,引导不那么具有洞察力的大众的想法,一直在眼光敏锐的少数派的头脑中萦绕,无论是在产业、政府还是在教育领域,都是如此。
就连最敌视企业精英的人之
一、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也设想过建立一个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新联盟,他们可以把国家的产出提高3倍到12倍。
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主流政界人士都支持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和优胜劣汰理论,并对最聪明的男性和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和自杀感到担忧。
[21] 大公司的效率信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引入的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以及对工会的厌恶,在产业工程师弗兰克和莉莲·吉尔巴思(LillianGilbreth)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友好与温和,后者因为按照效率理念管理家庭和养育子女而享誉全国。
莉莲·吉尔巴思还赞助了一些关于座位对工人的健康和生产率影响的初步研究。
家长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公司,比如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直接向朋友和邻居出售商品的先驱,这一直销网络后来被雅芳和安利等公司进一步完善),以及代顿的国家出纳机公司,它们使健康和文化成为雇员生活的一部分。
(位于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行政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倒闭后不幸被拆除,大楼里面有一个中庭、一个早期的空调系统。
)对于少数几家领先的公司来说,效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2] 企业效率理念的最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时期,当时的能源冲击、通胀和劳资纠纷对人们固有的商业理念构成了挑战。
1966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不连续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必须保留一些综合效率。
全球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表达共同愿景并使每个组织能够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的机构”。
[23] 作为温和的左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警告说,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但他也承认大公司(和工会)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必要因素。
就连苏联也以自己的方式同意关于效率的许多理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公开接受了亨利·福特的现代主义设想,从农业机械化到庞大的工厂,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苏联的五年计划基于公认的福特生产方法的效率,斯大林本人也称赞美国的效率是“一种既不知道也不承认障碍的不屈不挠的力量”。
歌颂集体农场的苏联电影制片人并不羞于让贴在拖拉机散热器上的福特标志清晰可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注定会导致周期性危机和大规模失业。
苏联的计划将实现技术效率的承诺并超越西方。
苏联科技史学家斯拉瓦·格罗维奇(SlavaGerovitch)发现了1957年苏联科学院的一份机密报告,报告宣称:“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和规划,就其效率而言,必须具有绝对特殊的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将使决策速度提高数百倍,并避免目前参与这些活动的笨拙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错误。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规划者和计算机理论家认为,一个中央计划的国家网络——格罗维奇称之为“内部网络”——最终能够实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目标,即整个经济理性和谐地发展。
[24] 1991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像马格尼奥戈尔斯克这样的大型建筑群受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启发,类似美国钢铁公司的企业曾经是苏联体系的骄傲,现在却被认为在浪费能源和 其他自然资源,而且效率低下。
(1988年入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饭店时,我遇到了一位芬兰林业顾问,他前来帮助苏联进行产业改革;他提到苏联每公顷土地的产量只有他自己国家的1/4。
)[25] 但西方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
在IBM个人电脑开始改变办公室工作的10年后,随着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公司面临危机和新商业帝国的出现,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效率正在形成。
并不是说连续过程的效率被放弃了,它仍然存在,而且还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但在一直期待会出现“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它已经失去了激情。
相比之下,海外承包商可以从农村调集年轻人加入工业大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20来年是过渡时期,他们引入了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并采用了一些新的自我识别和贬义的名称:“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目前最受左派欢迎的)“新自由主义”。
1945—1975年是一个黄金时代。
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危机和日本的崛起所制造的恐惧取代了广泛的乐观情绪。
一个重大变化是行政级别的减少。
如今很少有人对等级制组织有好感。
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公务员的谨慎作风让一心想遏制任人唯亲和腐败的美国改革者羡慕不已。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如小艾尔弗雷德·
D.钱德勒(AlfredD.Chandler,Jr.)等一些商业史学家和理论家将多部门公司誉为技术理性的化身时,学术界和大众评论家却在嘲笑它的单一性、装配线的单调乏味以及中层管理者官僚化的思维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华尔街的企业家开始通过恶意收购和杠杆收购挑战管理层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股价和股东价值的即时回报超过了旧式的企业政治家风范。
德鲁克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有几个章节涉及“管理”“工会”“政府”“知识型工人”等主题,但没有提到股东或资本市场。
与行政扁平化密切相关的是股东价值理论的兴起。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私营和公共部门养老基金的增长,基金经理正受到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机构投资者希望为他们的客户带来最大的回报。
质疑管理的孤立和自满,起初这似乎是一个进步的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新政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
小阿道夫·
A.伯勒(AdolfA.Berle,Jr.)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警告说,控制公司决策但不拥有公司股份的专业管理阶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是时候让投资者和所有者坚持自己的权利了。
事实上,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养老基金社会主义”这个短语,并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看不见的革命》。
[26]在“顺风顺水”的公司中,更多的高管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在高管薪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结果令批评该公司的进步人士失望——薪酬变得更加不平等,然而,这类新公司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
[27]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陷入困境,催生了一场旧的效率理念的危机。
受到苏联技术官僚推崇的福特胭脂河工厂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占地2000英亩,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时雇用了10万名工人。
历史学家戴维·
L.刘易斯(DavidL.Lewis)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区”,“在纯粹的机械效率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福特汽车总是从数千家小供应商那里购买零部件,但胭脂河工厂的理想是以直接购买铁矿石、煤炭、橡胶和其他原材料为起点,进而逐步整合这些原材料,这是受到当时的摄影师和艺术家赞美的一体化流程。
尽管通用汽车公司旗下拥有“为每个钱包和每个目的”设计的多个品牌,而且对定制持友好态度,这似乎与福特的理念相反,但它仍遵循多级官僚机构的模式,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专制的家族式的福特更甚。
通用汽车公司甚至收购了滚珠轴承制造商之类的供应商,而不是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到20世纪70年代,外包取代了这种内包。
正如管理学领域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观察到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能够(在他的顾问彼得·德鲁克的鼓励下)出售许多设备,因为更高效的计算机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
[2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新模式不是来自通用电气,而是来自苹果电脑公司。
与竞争对手IBM和迅速扩张的施乐不同,苹果保持着由设计人员、营销人员和策划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核心,并将其许多其他职能外包。
苹果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甚至彻底地融合并修改了其他人的想法,但它几乎没有基础研究可与IBM的托马斯·
J.沃森研究中心或施乐传奇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相提并论。
苹果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施乐的个人电脑陷入停滞,苹果以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将其技术应用到麦金塔电脑上。
与此同时,高效的制造业本身陷入僵局。
从未经历过大萧条的新一代年轻工人正在反抗管理层对生产速度前所未有的追求。
“异化”从学术界渗透到流行文化中。
现在看来,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被压力和疲劳所玷污。
汽车行业后来出现医疗和养老金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工人在合同中优先考虑的是提前退休的福利。
[29] 伴随着新的高管薪酬模式,一种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出现了,即韦尔所说的“工作场所裂痕”。
组织的基本核心都是应急工作人员,临时业务往往外包,很少有工会,人员流动率很高。
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新公司环境中,管理层心目中理想员工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亨利·福特的主导下,员工会遵循由专业人士确定的固定程序,直到被提升为总监或退休。
在新的灵活的企业里,员工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做出迅速而富有创造性的反应。
曾担任拉金公司高管的作家兼出版商阿尔伯特·哈伯德在其1899年出版的《致加西亚的信》中塑造了一个绝对服从公司的形象,这本书重印了4000万册,被分发到从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到美国陆军等机构的员工 手里。
这本小册子无处不在,反映了1900年左右各组织的效率学说。
几乎在整整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一位名叫斯宾塞·约翰逊的医生出版了一本同样受到赞誉和厌恶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
和之前要求一心一意遵照命令相比,这次新的看重灵活性的公司准备奖励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他们不仅能应对变化而且能预见变化。
维基百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谁动了我的奶酪?》在出版的头10年里共售出2600万册。
批评者指责这些书都美化了服从,但两者是不同的。
灵活的下属现在被描述为服从的不是某个人——将奖励忠实和热情服务的上司,而是服从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社会变革趋势,因为上司也会被迫追随这种趋势。
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灵活的“学习型组织”——有时明显受到机体免疫系统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管理理论上的旧的稳定的准军事结构。
[30] 正如灵活性取代了静态的等级制度,私有制侵蚀了贵族阶级在与竞争者和政府关系中的义务。
冷战时期的企业——不仅是航空航天企业,还有像AT&T和IBM这样的科技巨头——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
在某些方面,AT&T和IBM是垄断企业,但它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姿态来对自己的地位做出补偿。
正如乔恩·格特纳(JonGertner)在《思想工厂》一书中指出的,贝尔实验室以2.5万美元的相对低廉的费用向所有制造商发放了晶体管的特许经营权,而不是要求获得高额特许经营费。
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公司2017年的市值为1770亿美元,其技术基于管理大型数据库的创新理念,这一理念是由IBM的计算机科学家埃德加·
F.科德(EdgarF.Codd)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从未获得过专利。
这要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甲骨文公司的崛起对IBM的高管来说肯定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科德的突破是对他们现有产品的威胁,但他们选择了对此视而不见。
[31] 1984年AT&T和贝尔系统公司的解散表明,没有哪家公司会因为规模太大或太受尊重,而避免受到新来者的挑战。
新效率的支柱之一已经确立,“镀金时代”的发财方式是把以前独立的石油生产商、钢铁 厂和铁路公司合并成巨型组织,理由是通过规模来降低成本;现在,效率可能意味着在它们功能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将它们分拆。
科研投资不高和官僚作风较弱的、较精简的新竞争对手可能会提供压低以前优质服务和硬件的价格。
以前默默无闻的中西部地区微波无线电企业家比尔·麦高恩(BillMcGowan)曾设法让美国政府支持他在1974年对AT&T提起反垄断诉讼,那次诉讼涉及贝尔系统公司大量的法律资源,这表明没有一个组织是安全的。
[32] 新公司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全球化。
“镀金时代”的信托基金可能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但它们几乎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和永久移民经营的。
如今,一家典型的美国大公司可能有80%的收入来自海外;如何对这一收入征税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正如商业记者丹尼尔·格罗斯(DanielGross)指出的那样,以“二战”前的标准来看,美国跨国公司的总部也是国际化的,“忘了影响政策吧,如今许多美国一流的首席执行官甚至不能在这里投票”。
一些左翼批评者认为,新世界是一个超越阶级的世界,对彼此的忠诚超过了对同胞的忠诚。
对这些国际化精英的怨恨对于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胭脂河工厂”模式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关键行业对国际供应链的相互依赖可能会挫败经济民族主义。
[33] 到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学家开始修正长期以来对公司性质的假设。
1989年,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
C.詹森(MichaelC.Jensen)预言了“上市公司的消亡”。
在此前的10年中,他和其他学者培训了一代精英顾问和高管,让他们将回报股东视为企业的唯一目的,打破了平衡投资者利益与雇员、客户和公众利益的旧观念。
詹森及其同事倡导的“代理人”理论已经赋予了企业常春藤盟校的血统,这些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资产的高效再分配者和交易成本的敌人。
如果高管对股东收入有真正的贡献,那么高管可以获得补偿,但这一承诺却从未实现其潜力。
对于高管来说,有太多的方法可以用创 造性的会计方式来操纵业绩,甚至在糟糕的年份,他们的薪酬也可以获得提高。
正如坎贝尔定律所预言的那样,衡量利润的标准可能会被操纵,这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该衡量股东的长期利益。
到2014年,有数百家公司使用非标准的会计方法来证明高管奖金的合理性。
从长远来看,旨在减少高管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代理理论可能会增加这种冲突。
[34]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
1995年,《哈佛商业评论》里一篇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与哈佛大学约瑟夫·鲍尔(JosephL.Bower)合著的论文中首创了“颠覆性创新”一词,由此开启了思考技术变革的新阶段。
克里斯坦森的创新之处在于质疑传统的商业智慧,即倾听消费者的意见并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
新的革命性技术最初往往不如既定的技术高效。
一开始,它吸引的不是现有用户,而是背景和需求各异的买家。
克里斯坦森和鲍尔援引了计算机磁盘驱动器行业的例子。
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计算机硬盘才能与传统产品竞争并最终主导行业,在这一行业中,老牌公司嘲笑最初降低存储容量的新型紧凑型硬盘,而正是这种硬盘最终使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行业成为可能。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例子,该行业最初的制造商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但到21世纪初,希捷(鲍尔和克里斯坦森专门提到希捷)已经成为全球硬盘驱动器行业最主要、管理最完善的公司之
一。
然而,颠覆可能是实实在在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伊士曼柯达公司未能通过推广自己实验室开发的数字技术与其主要的胶片产品竞争。
[35] 几乎在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出版的同一时间,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出现。
平台模式开始挑战更早的“颠覆性”企业。
在连续过程效率下,重点是物料的生产、零售分销和快速的货运。
平台创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它不是始于个人电脑,而是始于互联网和图形浏览器的普及。
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为其他服务 或交易提供框架。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尽管存在种种开支和官僚作风,但公司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机构。
但是,如果技术能够匹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呢?这一想法似乎可以追溯到199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隐形引擎:软件平台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转型》。
平台公司可以结合委托销售、广告、信息经纪等功能。
事实上它可能以职业介绍所或出租车公司的形式表现出来。
它的吸引力在于,它将信息和服务集中起来,否则这些信息和服务都需要多方搜索。
它可以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形成消息和建议的信息流,并将用户的在线行为转化为可以出售给第三方的信息。
对投资者来说最有用的是,它甚至可以诱使用户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
平台公司可以自行制造、分销产品。
微软、IBM,尤其是苹果仍在销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硬件。
但最大的增长空间出现在其他地方:从其他企业和个人那里获得收益,以提高交易效率。
[36] 推动软件革命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处理器速度和存储量的指数式增长。
少数巧妙的想法减少了对硬件的需求,如纠错码(如果没有这一点,在线商务和通信就会崩溃)、数据压缩(使存储容量成倍增加)和公钥密码(使安全的互联网对话成为可能)之类的技术。
这些想法使硬件的效率成倍增加,出色的算法可能相当于巨大的硬件及其强大的力量。
它们基于以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概念,这些想法可以用代码表达。
以产品代码编号系统为例,它是电子商务的基础,也是20世纪90年代亚马逊网站迅速发展的基础之
一。
它是荷兰数学家雅各布斯·韦霍夫(JacobVerhoeff)设计的,是一个在数字上添加额外数字的公式。
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你可能会在这个数字之前看到一些代码,它被称为校验数字,只允许计算机程序通过处理一个复杂的公式来验证真实数字,从而得到个位数的答案。
如果该数字与选中的数字不匹配(例如,由于客户错误地转换了两位数),就会出现错误通知。
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生成和检查输入的数字。
那是算法 之美,遗憾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把数学产生的经济力量视为理所当然。
[37] 我们都听说过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但只有技术专家和历史学家听说过雅各布斯·韦霍夫。
然而,当贝佐斯计划实施在线零售时,图书销售是一个自然的开端,因为就韦霍夫的算法而言,与其他商品类别相比,图书拥有标准化的产品条码。
同样,直到最近,很少有人知道卡尔海因兹·勃兰登堡(KarlheinzBrandenburg)或其他德国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同行的名字。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开发的MP3和其他音乐压缩算法,使像史蒂夫·乔布斯的iPod之类的设备能够高效地进行数字存储。
数字存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破坏了音乐唱片产业,此前唱片产业以最低每张16.98美元的价格出售唱片,而其制造成本不到1美元。
[38] 如果将互联网上远程计算机中的海量存储与高效的算法相结合,就可以使一种被称为大数据的新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在幻灯片和打孔卡的时代,人们也曾感觉到被数据淹没,早期的商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分析数据的技术。
但是,存储和分析前所未有的记录的能力不仅仅只是连续过程时代统计思想的升级版本,它还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员工的生产率和利润以及客户的价值。
迈克尔·刘易斯在畅销书《魔球》中暗示,任何经理都可以效仿奥克兰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Beane),像他那样用更精密的衡量方法确定员工的潜在贡献。
大数据的问题在于,竞争对手通常能够获得类似的数据集和算法,因此,竞争优势类似于会计师所说的递耗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机器和其他东西会逐渐失去价值,而技术需要不断改进。
平台公司积累了如此庞大的数据,以至于与运动员不同的是,它们很难失去领先位置。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Davies)所说,它们也有能力在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关注并操纵公众情绪。
19世纪的数据统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完成的,21世纪后的大数据统计正在成为一种专有工具。
目前由于法官会优先 考虑保密算法的结论,法院破坏了对刑事和民事司法所必需的有争议证据的竞争性辩护。
[39] 反过来,大数据的基础是用户生成的信息。
收集和录入数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比如,在民意测验和焦点小组中就是如此。
平台效率的部分基础是鼓励客户在不付费的情况下创建数据,亚马逊的顾客评级系统是这一理念最有名的早期版本。
更深刻的革命是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与早期的搜索软件不同,它依赖于无数网站所有者选择的链接之间的关系。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等信息科学家率先利用科学论文中的引文指出那些最有影响力,因而被认为质量和关注度最高的作品。
谷歌的创始人、计算机科学研究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了科学以外的整个互联网。
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这方面的更多情况。
尽管存在公认的问题,而且需要不断修正算法以防受到操纵,但其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和质量依然很快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
这样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用户分类。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系统化仍在试图建立一个单一的知识层次结构。
21世纪的读者,甚至一些专业图书馆员现在更关注标签,这些关键词可能是由外行读者提出的,而不是由分类专家制定的。
例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图书馆仍然使用杜威十进制系统,但在从不同范围抽取的主题“单元”中放置非小说类书籍(如技术研究书籍)。
尽管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越来越重要,而且人们担心脸书和推特成为默认的信息来源,但在控制数据激增方面,搜索作为一种信息习惯,似乎并没有让使用量下降。
虽然谷歌没有公布每年的搜索量,但一个搜索行业网站将其声明解读为,仅2012—2016年,谷歌的搜索量就增长了50%以上,每年超过两万亿次,其中15%的关键词是之前从未搜索过的。
社交媒体可能取代一些网站,但它们似乎也产生了更多的搜索。
自2012年与人合写了一篇题为《追踪信息流向家庭》的论文 后,通信学者
W.拉塞尔·诺伊曼(
W.RussellNeuman)和他的同事就一直在给这个领域的一项旧的特性赋予新的生命力。
按照诺伊曼的说法,信息推送是指,在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由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信息的吸引力在于用户按照偏好获得媒体产品(无论是通过搜索还是流媒体服务)。
谷歌和其他现代搜索引擎使人们能够更主动地利用信息,明确地提出要求,而不是从数量有限的媒体上获取信息。
[40] 信息拉取反过来又有助于实现平台效率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个性化。
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按年龄、性别、地域和估计收入等特征将广泛的人口细分为不同类别的消费者。
也有一些有特殊兴趣的群体被添加进邮寄名单,如关于仙人掌和多肉植物的书籍的狂热购买者等,尽管这些书价格昂贵,而且并不总是最新的。
网络零售商和搜索引擎公司的大数据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准确地识别消费者品味和预测其行为。
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平台已经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了。
谷歌的用户会注意到,他们获得广告服务(不仅来自他们最初寻找的公司,也来自竞争对手)的频率之高,是任何印刷媒体或广播媒体都不可能与之媲美的。
得益于这种力量,从2005年首次公开募股到2016年,谷歌的广告收入增长了10倍以上,从63.7亿美元增至793.8亿美元。
[41] 对一些公司来说,平台提供了另一个战略机遇:非物质化。
最初建立在实体产品分销基础上的技术公司,尤其是IBM和苹果,已经转向基于网络的服务。
亚马逊现在从网络服务中获得的利润比从零售业务中获得的收益要高。
[42] 在1995年之后的10年里,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开始之后,移动计算的惊人崛起使个性化服务和基于云技术的服务变得更受欢迎。
在iPhone推出后,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是信息技术史上最快的一次。
从1976年推出AppleI电脑到2003年,家庭购买个人电脑的比例增长到约 60%,这用了大约25年。
而从2007年iPhone问世到2015年,智能手机仅用了8年时间就达到了这一普及率,且这段时间大部分处于历史性衰退中。
(事实上,经济困难或许有助于推广这项技术,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已经成为近20%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上网的主要途径。
)因此,无论好坏,许多网络资源都针对个人的、移动的小型屏幕进行了优化,而不是主要面向办公室或家庭电脑显示器。
社会科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趋势的潜力。
甚至在iPhone推出之前,心理学家谢里·特克尔(SherryTurkle)就称这种新的移动信息潮流为“永远的,永远在你身上”。
对平台公司和广告商来说,尽管消费者可以选择禁止泄露位置坐标,但基于实时定位来联系消费者的能力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43] 平台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商业企业类型之
一,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机构相比,它们需要的雇员要少得多,借助人工智能平台,甚至可以让公司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和精简。
2015年脸书的收入为280亿美元,员工只有17048人。
该公司同年的净收入为100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超过58.6万美元。
传统的20世纪科技公司IBM仍然以119亿美元的净收入略高于脸书,但2017年IBM有约41.4万名员工,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约为2.87万美元。
尽管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拥有强大的实力,但相较于向企业出售先进服务,利用算法从用户生成的数据中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以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的利润要高得多。
[44] 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利用了智能手机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创造了新的基于位置的效率类别。
作为平台公司,优步、Lyft(来福车)和其他公司并不拥有出租车、豪华轿车,也不雇用司机。
它们以超高效的中介身份出售其服务,通过跟踪位置并根据需求调整价格的算法来对客户和司机进行匹配。
实际上,优步可以向大城市的客户保证:无论天气、交通条件如何,或是否有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在5分钟内以一定的价格乘车。
因此,优步可能是消费者平台效率公司中最快取 得成功的一家。
研究过其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称,尽管人们对优步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尤其是在欧洲,但它确实是高效的。
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即使乘车费用激增,也比买车、保养和支付保险更便宜。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优步公司及其针对自己的司机和竞争对手的政策伦理,至少它在匹配乘客和司机方面非常高效。
根据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evenLevitt)的一项研究(使用该公司的数据),至少在2017年年初,优步的费率(在许多地区低于成本)远远低于其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
莱维特的合作者斯蒂芬·
J.杜布纳(StephenJ.Dubner)认为,2015年花费40亿美元购买优步公司服务的客户本来愿意多支付110亿美元,这为社会带来70亿美元的消费盈余,这是“经济学家的梦想”。
受此类统计数据的鼓舞,私人投资者对平台经济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以至于2017年2月,优步公司的市值达到625亿美元,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99亿美元的市值。
尽管有人指控优步公司高管的行为不端,但该公司的市值在新首席执行官于2017年8月底上任时已增至近700亿美元。
[45] 与许多较小的平台公司一样,优步的商业模式也部分基于美国劳工法和税法的含混不清。
当一个人是公司雇员时,必须遵守最低工资法,并且雇主要缴纳税款和保险费,而当他是独立承包商时,他的权利和义务则往往并不清楚。
软件可以使优步利用这种模糊性,将独立性(自由设定自己的时间并使用竞争性调度服务)与具有激励作用的竞争性调度服务相结合,该技术被称为“选择架构”。
[46] 对于优步这样的服务,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他们利用游说力量,通过改变监管规定,获得了相对于现有服务的不公平优势。
提高价格是富人插队的另一种方式,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这根本不是一项根本性的创新,因此,对于创造一个更高效的社会没有多大帮助。
比如,其鼓励了不必要的出行,而不是让司机和乘客的匹配更迅速。
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研究共享乘车程序的效果。
对平台效率的一个反对意见实际上是,它根本没有深远的颠覆性。
最强烈的批评不是来自硅谷的进步派批评者,而是来自最认同颠覆思想的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本人。
克里斯坦森和他的同事德里克·范贝弗(DerekvanBever)以及布赖恩·梅祖埃(BryanMezue)最近区分了两种颠覆性:效率创新和创造市场的创新。
后者是以更低的价格向更多人提供现有商品和服务。
优步的目标不同,它的目标是以低于或高于传统公司收费的市场结算价格持续提供交通运输服务,而且它遵循的是效率模式。
效率创新通常会减少就业。
创造市场的创新会带来新的产品类别并创造就业机会。
[47] 根据克里斯坦森、范贝弗和梅祖埃的分析,在19世纪90年代推出并一直沿用至今的自行车不仅比其中世纪的前代产品更快捷、更便宜,而且它重新定义并推广了一项新技术,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了几个量级。
早期最受欢迎的自行车是所谓的“便士-法寻”自行车,在骑手下方有一个巨大的轮子,以及一个较小的尾轮。
虽然轮子的大直径能将那个时代仍未铺柏油的道路的颠簸程度降至最低,但当轮子撞上障碍物时,它也有可能给向前倾的车手造成严重伤害。
这种自行车实际上吸引了许多年轻和富有的男性冒险者,他们是最早的骑车人。
在新的“安全”自行车中,菱形车架、充气轮胎和滚珠轴承的结合使骑行不仅更安全、更省钱、更舒适,而且实际上比以前的车型速度更快,从而受到了女性、中年人、老年人以及薪酬更高的产业工人和手工艺人的广泛青睐。
在1960年的连续过程时代的晚期,另一项创造市场的创新是施乐914型复印机。
这种复印机不仅能更好地替代湿法处理照片,而且有时能复制出比原版质量更好的复印件。
它淘汰了爱迪生时代的油印机,并就此带来了历史上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公司之
一。
(1960年对施乐公司1万美元的投资到1972年增长到100万美元)。
相比之下,除了通过智能手机运营外,优步或Lyft汽车与传统的黑车没什么两样。
[48]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尽管更具挑战性的技术可能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更高效(例如,改进蓄电池能简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过程,并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范围、提高其效率),但这些技术仍面临创新资金不足的窘境。
冷战时期推动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投入的军事紧迫感已经减弱,气候变化成了一个党派问题。
与电子网络和逻辑相比,物理和化学体系存在更多的挑战和限制。
制造高效的设备可能需要多年表面上是浪费的实验。
研究“二战”后美国喷气式发动机发展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Scranton)总结说,喷气式发动机的成功不是科学的项目管理,而是“非线性的、非理性的、不确定的、多边的、极富激情的技术和商业实践的结果。
不是通过计划,而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成功的。
关键在于决心、对失败的某种漠不关心(这有助于保密)以及巨额的公共资金支出”。
这一成功不仅使民用航空运输速度实现了飞跃,而且提高了可靠性。
与依靠活塞式发动机的道路运输相比,每公里成本降低了。
在20世纪60年代的爆炸式增长之前,施乐公司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初创期。
在伊士曼柯达公司的阴影中,作为一家小型摄影用品公司,哈洛德公司(后来在突破静电复印技术应用后改名为施乐)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发,发明家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Carlson)最终在1938年将干式照相专利转化为商业上成功的设备。
碳粉在纸张上的高温定影可能会引起火灾,如果被复印的文件中有太多的零和字母
O,原版文件就会有着火的风险。
该设备在1960年的一场大型贸易展会上就引发了一场小火灾,不过幸好没有被顾客注意到。
即便是现在,最高效的锂离子电池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2016年秋天,韩国电子巨头三星公司召回了几百万部旗舰产品Note7智能手机,原因是两家不同的供应商的电池故障引发了数百起着火事故。
高端电子产品的用户既需要紧凑的体积,也需要全天电量储备,但唯一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的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易燃电解质。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一旦出了问题,就会着火……这是它们的自然属性。
”[49] 因此,平台效率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带来的回报可能比创造市场的创新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算法能够以超过物理和化学创新的速度被测试,并被应用于更大的系统。
现在,人工智能程序可以从经验中快速学习,人工智能不仅能在象棋和围棋这样的游戏中,而且在“无限制德州扑克”之类的竞赛中击败顶尖专业人士。
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击败了顶级扑克玩家,获得了180万美元的奖金。
当然,软件和硬件的进步并非完全不同步,例如,锂电池需要复杂的程序控制才能安全运行,创造市场的创新的相对困难不大可能消失。
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软件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的改进中,2008年经济衰退后的经济复苏速度要比20世纪的几次危机缓慢。
[50] 平台效率的第二个问题发生在金融交易领域。
新效率并没有减少金融所代表的社会管理费用,反而使管理费用进一步增加。
20世纪90年代,《未来之路》[比尔·盖茨、内森·米赫尔沃尔德(NathanMyhrvold)和彼得·林纳森(PeterRinearson)于1995年出版]“硅谷宣言”的读者认为,他们期待着“无摩擦的商业”。
事实上,对用户来说,亚马逊和其他领先的零售网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单纯的交易功能。
亚马逊的Echo语音识别智能音箱的用户可以用该公司的Alexa系统下订单,而无须点击屏幕。
微软、谷歌和苹果也推出了类似的电子语音助手。
而那些高效的、愿意触碰某样东西的人,可以选择亚马逊公司支持Wi-Fi的设备,这种设备可以连接到家用电器上,用于即时订购相关品牌的易耗消费品,如洗衣机专用的洗涤剂等。
微处理器巨头英特尔公司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预测,在未来,消费者也许会通过植入大脑的传感器接收到的想法下订单。
虽然这家芯片制造商似乎在经济衰退期让这个项目悄然延后了,但它不太可能消失。
[51] 不过,摩擦还是有办法避免的,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效率。
亚马逊平台上有200万第三方商家,这些商家的商品与亚马逊自营的商品一起被展示。
他们的一些订单是通过亚马逊的仓库配送完成的,其他订单则直接从卖家那里发货。
供应商可能对相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保 修政策,消费者评级和收货时间也不同。
此外,他们使用专门开发的软件来调整自己的价格,使之与亚马逊和非亚马逊供应商的价格相适应。
在“动态定价”下,报价可以在不通知卖家的情况下自动更改。
亚马逊使用一种复杂且秘密的算法在“购买框”中选择默认供应商,通过链接将商品添加到消费者的购物车中。
这种算法不仅列出了获得订单的供应商之外的其他供应商,点击其他链接的客户还可以看到其他厂商。
亚马逊的供应商使用特殊的软件来计算他们的价格,他们可能会设置一个更高或更低的价格。
到目前为止,与通常最低价格、订购的便利性——亚马逊的界面设计得非常好——以及优享计划的交付速度相比,这些变化给用户带来的选择烦恼还不算大。
来自亚马逊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通胀,事实上亚马逊的销售利润微乎其微,(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它的真正利润来自它为其他公司和政府提供的网络服务。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重大收购是否可能将亚马逊变成一家反竞争而非支持竞争的公司。
[52] 只有当消费者愿意接受亚马逊的算法时,他们才能享受到该平台提供的充分的效率,而亚马逊的算法也正在与满意度各异的各种供应商的算法进行竞争。
寻找最低价格的消费者可能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完整的清单并衡量供应商的声誉。
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站允许购买者查看亚马逊的历史价格,并在价格跌至预设水平时设置电子邮件通知,但这往往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决定设置什么价格。
它主要适用于昂贵的非必需产品,特别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们会受到制造商季节性价格下调的影响。
不管有没有此类价格追踪工具,最初作为一个简单而高效的购物系统的平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佳报价可能会突然出现或消失,这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算法和平台供应商对自己购物模式的监控。
同样,在线旅游服务最初似乎通过比较最佳的酒店价格来简化决策,已有之类的聚合平台出现,该聚合平台声称可以从其他 预订网站上找到最优惠的报价。
旅行预订平台的复杂性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曾经受到网络预订致命威胁的旅行社出现了复兴。
[53] 在网络商品和服务网站以及社交媒体上对顾客评级进行评估也变得更加复杂。
据《纽约时报》报道,将亚马逊用户评论与专业消费者组织报告以及转售价值进行比较的市场研究人员发现,用户评论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并不可靠。
2012年,一位学术数据挖掘学者估计,网上的评论中有1/3是伪造的。
一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靠在亚马逊上为自己出版的作品撰写评论,每个月能赚2.8万美元。
我想在网上找一家附近的电脑维修店,但注意到一家被打了五星评论的维修店,其客户评论大同小异,这让人对客户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比如,偶尔出现的温和批评会让客户评论看起来更真实,而且评论者也没有对任何其他类型的机构发表过意见。
相反,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评论,尤其是对公寓出租方的评论,似乎都在致力于表达消费者的不满。
更复杂的是,一些真正的在线书评家似乎对几乎所有事情都表现出真诚的积极态度。
但核心问题是,评论受到了追随者效应和评级泡沫等社会倾向的影响。
在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方面,虚假评论的影响力可能令人吃惊。
[54] 不管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显示了坎贝尔定律的作用。
这些评论的影响来源于发表评论者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消除他们的偏见。
社会学家和网站管理员创造了将真实评论与虚假评论区分开来的算法,但这些努力遇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正如在文字和图片鉴别中一样,用于检测欺诈的工具可以被用来更巧妙地造假。
最后,并不是说用户评论毫无用处,而是说用户评论的时间效率要比刚出现时低得多。
经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它们,并找到每种产品或服务的优劣之处。
专业的书籍和产品测评者的确限制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但如果你相信他们的判断,那么追随他们比试图去猜测大众的智慧更有效。
[55] 目前还不清楚网络零售的平台经济是否比传统商店更有效率。
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观点认为,与传统的实体购物相比,网购通过减少汽车出行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理论上,在网上订购并送货上门的包裹会比多次外出购物产生的碳排放量更低。
至少在2012年,亚马逊在其网站上的“网购效率”频道中声称自己提供“更绿色的购物体验”。
实际上,算法效率的结果一旦开始与人类行为相互作用,就几乎无法对其进行衡量。
努力减少碳足迹的确可以为人们节省出行里程和时间。
但是,来自特拉华州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他人可能通过其他类型的活动,如娱乐来花掉自己节省的时间和里程。
即时满足的效率还意味着更多商品被分装在不同的包装中运送给消费者,当这些商品被运送给零售商时,它们可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单独的盒装形式。
正如电子库存控制使精益制造成为可能一样,一些消费者在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的帮助下进行淘货,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位傲慢的作家在文章中宣称:“未雨绸缪已经过时。
”亚马逊大力推销收取年费的优享计划,许多产品可以在两天里免费送达,这鼓励了冲动购物。
一种形式的高效——快速交付——与另一种形式的高效相抵触。
在西尔斯百货公司提供商品目录的时代,消费者可以明显地注意到联合发货过程中的节约。
虽然纸板行业一直是回收利用的领头羊,但由于网络购物的便利性,包装盒的销量一直在迅速增长,回收利用在运输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环境成本。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环保概
但本书恰恰要批判效率(除非它是低效率)。
本书讲的是一个明显的悖论,也就是低效率看起来毫无意义,但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刻意的低效率也很有必要。
在大多数情况下,效率是好的,但同其他所有好东西一样,它也有可能过犹不及。
就如同过量饮水都能致命一样。
在20年前互联网兴起之初,我正在写第一本关于技术带来的意外后果的书——《技术的报复》。
这本书于1996年出版,当时我从未想过效率本身可能会成为威胁。
事实上,同那些自称为“新卢德主义者”(这个称呼如今也被他们的朋友和敌人共用)的批评者不同,我很早就接受了新技术而且是一个狂热的技术爱好者。
我是科学刊物的一名编辑,该刊物在全球范围内招募作者,而且用大学提供的电子邮箱同这些作者保持联系,我早已习惯使用这种方式来联络并约见作者。
作为一位很早就使用电子数据库的研究人员,我发现新的网络浏览器和图形界面进行了受欢迎的改进。
作为一个总是修改自己文字的作家,我自里根时代初期使用TRS-80笔记本电脑时,就已经开始使用文字处理软件。
一想到重复输入的枯燥乏味和那些乱糟糟的复写纸,我就对自己的打字机没有任何怀旧之情,虽然我也发现由于字符压入纸张的力度和碳素色带从饱和到模糊的不同,打字机打出来的字母确实有一种特殊的图形风格。
我见过也写过新技术的缺点,比如,久坐不动的办公室生活造成的长期背部疼痛和腕部疾病,以及无纸化办公带来的滑稽命运。
但我也认可20世纪90年代末期技术乐观主义的很多内容。
互联网最初被视为取代报纸和杂志的天赐之物。
无论电子出版物是否会取代印刷品,出版商看重的是:它们对能够吸引大量读者的高质量内容拥有无价的特许权,而这正是广告商所梦寐以求的。
到21世纪初期,技术本身就成为一种赚钱的广告焦点。
我偶尔发现在我的剪报中也存有厚厚的《纽约时报》中关于技术的文章,这些文章得到硬件和软件制造商以及电子销售商的慷慨资助。
高效的电子新闻编辑室让一切成为可能。
看起来社会上也有利润丰厚的蛋糕,并且已经被吃掉。
亚马逊出现了,但它仍然可以同有利可图的大型连锁书店共存。
很难想象亚马逊会威胁鲍德斯和巴诺书店,因为这些书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用横扫一切的规模和较早一代的技术摧毁了独立书店。
机器人的出现并没有威胁就业水平。
老式的商业杂志同以技术为导向的新秀《连线》杂志和《产业标准》分享仍然兴旺发达的报刊亭。
技术乌托邦作者传播个体赋权的福音,而企业精英则挣到比以前更多的钱。
如果说20世纪60年代是经济腾飞的年代,那么20世纪90年代则得益于互联网的高效而成为双赢时代。
自2005年起,全新的高效世界跨入了一个不同的阶段。
随着2007年苹果手机的问世,电脑处理速度的快速演变使电子设备不再是人们用完就放置一旁的工具,而成为人们自己及其职业网络的延伸。
与此同时,尤为高效的搜索引擎谷歌和社交网站脸书同亚马逊一道,通过为因特网增加一个新的层次——介于公司网站和开放网站之间的平台,改变了电子商务。
自2008年起,通过不断提升电子效率来建立乌托邦的梦想开始变得黯淡。
那一年开始的经济衰退有很多根源,但部分原因是,银行家和证券从业人员能够借助技术轻松地管控风险。
与此同时,能放入电 脑芯片的晶体管数量的增幅开始放缓。
这个数量过去大约每18个月就会翻一番,这一规律自1965年起被称为“摩尔定律”(以戈登·摩尔的姓氏命名,他是占统治地位的芯片生产商英特尔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但自2005年起,这一频率被拉长到2~3年。
此外,新平台成功吸引了广告商和市场营销人员,却付出了放弃报纸和杂志收益的代价。
(广告收入的历史峰值直到网络问世后的第10年即2005年才出现,当时纸质媒体的广告收入为474亿美元,网络媒体为20亿美元,而到了2014年,这两个数值分别为164亿美元和35亿美元。
)[1] 当然,面对新的高效网络,有很多成功者,也有很多失败者。
在这种网络中,电脑技术——算法——取代了直觉判断。
价格竞争的加剧使会上网的客户受益。
但对许多经济学家而言,关于更高效的生产与分配所带来的好处能提高公众生活水平的梦想正在褪色。
知名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Cowen)和罗伯特·
J.戈登(RobertJ.Gordon)分别在其著作《大停滞》和《美国增长的起落》中,进一步阐述了之前与众不同的想法,即到20世纪,“摘容易的果子”的时代已经终结,用今天的标准来看,那些变革性发明的开发成本相对较低。
即使在2008年的经济衰退中,这种乐观情绪也出现了急剧转变,当时计算机科学家和未来学家雷·库兹韦尔(RayKurzweil)重复了他在2000年的预测,即到2020年,人们仅花1000美元就可以买到一台能模仿人类大脑运作的电脑。
[2] 不仅一些经济学家,就连很多西方国家的公民也对产业和学术精英为中产阶级或穷人提供好处的能力失去了信心。
除非这个趋势得到逆转,否则无论哪个政党掌权,全世界的政坛都很有可能在未来的数年中动荡不安。
因此,现在是时候考虑过于高效是否已经成为问题的一部分了。
我认为,我们不需要放弃效率的观念,而需要培养低效的行为方式,从长远来看,这些行为不仅会使技术更有效(完成更多工作),而且会更有效率(使用更少的资源)。
首先,我们需要一个效率的定义。
我在这里不会遵循经济学家在技术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否则这将变成另外一本书。
我将效率定义为最大限度地生产商品、提供服务或信息,或以最少的浪费处理交易。
效率这个词在19世纪得到广泛使用,当时科学家和工程师将效率这一物理概念扩展至人类劳动,即单位能量所做的有用功。
从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社会科学家反过来将这一概念扩展至社会所有的投入和产出,实际上也延伸到“社会效率”这一领域,即合理优化人类福利。
尽管这句话在今天听起来很天真,但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它不仅植根于技术理想主义,而且还植根于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
这一理念的先驱、社会学家爱德华·
A.罗斯(EdwardA.Ross)在1900年因发表反亚言论而被迫离开了斯坦福大学。
在后来出版的《社会控制》一书中,他向“躁动不安,努力拼搏,像雅利安人那样做事,怀有令人尊敬的个人抱负,对权力充满渴望,激起自身怒火以及愿意颠覆世界以赢得名望、财富或想要的女人”等行为致敬,但同时担心,这种浮士德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受约束就会毁掉社会。
作为一位本土主义进步派,罗斯希望学校利用工业合理化的方法向新一代灌输善政伦理。
这种效率意识形态早就消失了,但以较少努力获得更多成果的目标依然盛行。
我将把“效率”一词用于所有旨在减少人类完成任务所需时间的技术,无论是购买产品、学习某个主题、计划一次旅行还是做出医疗决定。
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Solow)在30多年前的1987年曾说过,计算机已经无处不在,但生产力统计方面除外。
如今,除了实际个人收入统计方面,算法效率的优势随处可见。
[3] 我对未来不持特定立场,不管我们是否注定裹足不前、不平等是否会日益加剧,或者某种新的超级高效技术是否会使今天的担忧看起来像是20世纪30年代的许多经济学家抱有的那些悲观看法,战后繁荣的技术基础实际上是在抗生素、洗涤剂、塑料以及个人电脑领域奠定的。
如果可以对技术预测进行什么概括的话,那就是许多预料中的革 命都已胎死腹中,而其他一些原本不起眼的创新则改变了社会。
科幻小说也不例外,儒勒·凡尔纳的出版商认为他在《20世纪的巴黎》中对未来进行了最准确的展望,凡尔纳本人也令人难以置信地同意了这一点,于是那本书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出版发行。
[4] 关于效率的其他许多告诫并不是本书的一部分,因为其他人都非常清楚地注意到了这些事项。
首先是能源问题。
质疑强制性能源效率目标的保守派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提到了所谓的“反弹效应”,即效率更高的技术所节省的成本会被消费的增长所削弱,甚至完全抵消。
19世纪60年代,经济学家威廉·斯坦利·杰文斯(WilliamStanleyJevons)在英国的煤炭消费中首次注意到了这一情况,而且随着每一次新的节能创新,类似情况都会再次出现。
能源成本的降低通常会被用来购买运动型多功能车和豪宅,更高效的空调技术意味着会有更多的房间安装空调,或者用中央空调取而代之。
这种影响远非铁律,就连其主要支持者之一的罗伯特·
J.迈克尔斯(RobertJ.Michaels)也承认,冰箱的强制性效率标准并没有带来明显的反弹。
但毫无疑问,这种影响确实存在。
从LED照明到电动汽车的技术效率提升被从稀土矿开采到电子垃圾导致的环境破坏所抵消。
[5] 其次,紧随能源之后的是对农业效率的批评,这类批评通常来自左翼。
在农民和农场主的人均产出方面,常规的机械化农业一直表现突出。
然而,瑞典农业科学家费尽周折地重新衡量了能源投入和产出,最近却证明,一台拖拉机所需的能源比耕作同一片土地的马所需饲料的能源要高出67%。
拖拉机的效率远远高于马匹,它带来的产量几乎是20世纪20年代马匹在同一块地上生产出食物的2.5倍,但它所需的能量却是马匹的13倍。
我们的农业还面临其他的反对声。
对种植植物和养殖动物进行快速采收和屠宰的效率,往往损害了营养价值和口感。
直到最近,传统方式种植的西红柿开始卷土重来。
为高效出栏而饲养的猪和鸡可能会出现健康问题,牛的生长激素虽然是“天然”的,而且对人类是安全的,但它却会导致牛奶产量达到极限的水平, 这一水平对奶牛来说是痛苦的。
对效率的追求可能会鼓励一种具有潜在灾难性的单一种植方式,比如在爱尔兰大饥荒前,土豆在其农业中占主导地位。
由于爱尔兰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几乎所有土豆的基因完全相同,因此源于新大陆的疫病毁掉了1845年的收成。
正如作家迈克尔·波伦(MichaelPollan)在《欲望植物学》一书中所说,“单一化是自然逻辑与经济学逻辑发生冲突的地方,哪种逻辑最终会占上风是毋庸置疑的”。
[6] 在全球层面上,真正的效率始终很难计算,因为提高效率的某些手段可能会降低地球的总体生产率,比如,化肥和杀虫剂会伤害河流中的鱼类和危及授粉的虫媒。
事实上,我们整个工业文明一直在通过碳排放威胁自身的效率。
如果对“效率”进行宽泛定义,那么一本关于其悖论的书就将包罗万象。
它将回到罗马尼亚裔美国学者尼古拉斯·乔治斯库-勒根(NicholasescuRoegen)的生态经济学,他认为世界秩序的衰落——熵的增加——是人类试图挑战秩序的必然结果。
气候变化有助于唤起人们对乔治斯库的想法的兴趣,但我把对这些想法有效性的评估留给其他人。
甚至连拒绝这种理论限制并倾向于将太空探索视为突破所有地球资源限制方案的硅谷文化,也认识到效率过高导致的环境、健康、文化和伦理成本。
尽管拥有智能住宅、联网设备和自我监控装置,效率助手还是知道如何划清界限。
从有机产品的生产到(我们将在第三章中看到的)没有技术的鲁道夫·施泰纳小学,手工价值观的成果吸引了许多高科技家庭的注意。
劳动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低效在他们的社会中占有一席之地,成为可靠和特权的标志。
这个新的上层社会阶级似乎与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Veblen)在1899年出版的《有闲阶级论》一书中描述的“强盗男爵协会”没有共同之处。
在镀金时代,富豪阶层的父权制和种族主义价值观也许并没有完全消失,现在人们认为它们甚至比不道德更糟糕,它们已经不合时宜了。
弗里克收藏馆和摩根图书馆等的旧瓶装新酒也是如此,早在1970年,经济学家 斯塔芬·林德(StaffanLinder)就出版了他的开拓性著作《受折磨的有闲阶级》。
当今的科技巨富们更有可能是在寻找下一家初创企业,而不是在提前退休后享受最后一次创业所带来的财富。
然而,就像在凡勃伦时代一样,炫耀性的低效拥有特权。
正如科技记者戴夫·罗森伯格(DaveRosenberg)2013年在《旧金山纪事报》网站上指出的:“奢侈品,尤其是手表……是硅谷向往高质量精雕细琢的手工工具、服装和配饰的微妙追求的一部分……当普通人期待最新的未来主义身份象征时,技术未来主义者却在复古。
”其他劳动密集型工具也是如此,比如,手工锻造的厨师刀大受欢迎。
[7] 技术专家的个人传统主义可能被视为令人钦佩的实用主义和开明态度,以及在日益自动化的背景下促进就业的力量。
这也可以被看作对社会分层的愤世嫉俗的认可:普通品为大众服务,奢侈品为创意创新者服务。
(一直以来都存在这种极端情况,而优质中档产品的市场有所萎缩。
布鲁明代尔百货店和沃尔玛还有发展空间,但经典的中产阶级百货公司如金贝尔百货公司在1986年已关门歇业,其昔日的竞争对手也在苦苦挣扎。
)这又引出了对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种趋势会加剧不平等,从而危及公民生活乃至民主本身。
阿瑟·
M.奥肯(ArthurM.Okun)的《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出版40年后仍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争论,并在2015年由布鲁金斯学会重新发行。
可以想象,这个社会既高效又不稳定。
硅谷对颠覆性的崇拜最初是建议把权力从寡头转向人民。
但现在,这也可能意味着建立一个似乎更难推翻的新寡头政权。
在硅谷,房价和公寓租金的上涨证实了经济学家弗雷德·赫希(FredHirsch)的分析,他在20世纪70年代预见,即使效率和生产率继续提高,也会出现一种基于“地位经济”的商品,永远不可能像信息技术产品那样让大众都买得起,就像热门演出好位置的票,或者全球经济中心的公寓,这两者都是赫希所说的“地位商品”。
[8] 即便如此,我认为,地位商品与日俱增的重要性和由此产生的挫折感,并不是反对效率的最佳理由。
技术狂热者反驳说,即使贫富差距扩大,亿万富翁攫取了世界上更多的产出,地球上的人民仍然能生活得更好。
如果没有像大多数企业那样承担风险和承受失败的动力,情况可能就不会如此。
按照这种观点,硅谷有赖于一种看上去低效和浪费的创业文化来最终创造一个更有效率的社会。
电子化效率存在更严重的问题。
在技术层面上,安全挑战和黑客威胁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如果对电子交易的恐惧达到了临界水平,那么电子商务可能会受到强烈的抵制,但到目前为止,银行和信用卡公司获利颇丰,它们至少能够忍受将一些欺诈行为作为做生意的成本。
同样,20世纪90年代参与性民主的梦想至少因为边缘群体使用网站和社交媒体的能力而陷入停滞,但电子民主主义的捍卫者总是能够提出满怀希望的新倡议。
技术评论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Morozov)正确地指出,如果“一个民主管理的社区的审慎承诺”对“不人道的泰勒制(工作方式的组织化)和市场原教旨主义”持反对态度,那么效率低下反而是好事。
这并不妨碍市场原教旨主义者获得超级高效民主的认可。
同样,算法可以有意或无意地根据性别、种族、地理或社会经济地位对个人进行歧视,但捍卫者却可以说,它可以让违规的程序变得更公平,甚至更有效。
算法收集了有关我们,或者至少是我们朋友的开支、旅行、投资、信贷和政治观点的海量数据,每天都有美国人的隐私受到威胁,一些人开始选择不参与网络生活,但迄今为止,无论是身份盗窃还是侵入式营销,都没有造成足够大的破坏,从而彻底改变了美国人的行为。
[9] 对移动技术效率的另一种批评指向了它对人际关系的损害,不管是商业关系还是个人关系。
美国人至少一直对商业关系没什么感情,甚至在电子商务兴起之前,他们就抛弃了当地的大型百货零售商。
虽然许多人,尤其是儿童和青少年的父母,在社交媒体对注意力集中和 人际关系的影响方面持保留态度,但在硅谷的许多文化中,磨耗仍然是一个特点,而不是一个缺陷。
[10] 对于效率拥护者来说,硅谷内外的反对声只是下一轮算法技术能够解决的暂时性问题。
“机器人带来大规模失业”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假设,而机器人的倡导者可以指出先前世界末日的预言同样落空了。
效率仍然是美国的核心价值,虽然硅谷的亿万富翁现在面临着更多质疑,但他们并没有失去作为托马斯·爱迪生、约翰·洛克菲勒和亨利·福特等美国文化缔造者继承人的衣钵。
史蒂夫·乔布斯有时和他们一样冷酷无情,但仍然受到数百万人的广泛怀念,因为他们相信乔布斯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这本书对技术效率提出了不同的批评意见,它接受减少人力和自然资源浪费的目标,但也承认,正如比尔·盖茨及其合著者在1995年所说的那样,一心一意推动一个“无摩擦”的世界实际上可以提高效率。
它没有研究信息技术面临的所有社会、政治和伦理挑战,而是关注其带来的长期自我颠覆。
我们知道,对儿童卫生的过度关注会削弱免疫系统,过量使用抗生素会滋生超级细菌,滥用阿片类药物会降低其有效性并成瘾,习惯性地依赖安眠药会加剧失眠。
很少有人放弃药物,同时我们对自然平衡又有了新的敬畏之情。
现在,质疑效率必须超越效率和有效性之间的常见差异。
考虑到击败敌人所需的子弹或炮弹的数量,战争是极其低效的。
但由于战争失败可能会导致灾难性的结果,因此,效率低下也会带来有效的结果。
反过来说,“清洁柴油”汽车发动机在燃料消耗方面是高效的,但由于它们的排放难以控制,因此不能被认为是有效的。
算法——使计算机硬件能力倍增的编程技术——带来了一系列不同的问题。
大多数时候,它们既高效又有效。
例如,尽管遭遇了许多成功的攻击,但公钥密码术利用了解析非常大的数字的难度,以确保电子金融交易的安全和互联网通信的总体安全。
从长远来看,其他算法可能不仅会危 及效率,还会危及有效性本身。
也就是说,它们不仅有可能导致不良后果,而且有可能导致工作浪费和机会错失。
它们可以被分为以下七个部分。
第
一,反偶然性。
大多数偶发事件都是不利或中性的,效率使世界变得更可预测。
但是,如果一切都尽可能直截了当,我们也会失去邂逅偶然的随机化和生产性错误的好处。
传统算法以限制正面影响的高额代价来减少负面冲击,二者密不可分。
第
二,过度关注。
效率通常表现为专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积极和必要的。
但进化却给我们和其他动物提供了第二种视角,即周边视角,它对细节不那么敏感,但能让我们看到较大的图案和动作。
在天文学的早期历史中,人们就知道通过稍稍远看,“偏向视觉”可以更好地看到不显眼的物体。
正如埃德加·爱伦·坡在《莫格街凶杀案》一书中写的:“一眼就可以看到一颗星星,可以通过将其转向视网膜的外部侧面来进行观察,这样更容易受到微弱光线的影响,能更清晰地看到这颗恒星。
” 第
三,自我放大量级。
效率在日常操作中不可或缺,不管有意无意,算法都可能无法通过放大最初的细微效果来做出最优选择,其早期的选择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这是自动化过程中的一种特殊风险,从金融交易到自动驾驶都会遇到。
在这个过程中,多种算法——其中没有一种是完美无瑕的——相互作用,有时不可能进行快速的人工干预。
第
四,技能腐蚀。
自动化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
它们几乎总是更加高效和连贯,这就是它们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原则上,一名技术人员和电子系统的合作比任何一方都能提供更好的业绩。
但当机器人伙伴发生故障时,可能会出现严重问题。
如果人类,不管是医生、飞行员还是普通的驾车者,没有掌握相关技能,结果将会对整个系统的效率造成灾难性影响。
第
五,固执反馈。
当要求自动化系统不仅执行人类目标还提供激励时,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变得更加棘手。
通过不满足真实预期结果的方式来达到某种标准(如考试分数)是有可能的。
在社会科学中,这被称为坎贝尔定律。
第
六,数据泛滥。
当精通基本流程的技术人员使用巨大的数据集时,可能会提高效率。
但使用这些数据集也会威胁到效率。
在许多领域,自动获取的数据量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数据的存储成本,从而增加了支出。
大数据还可能提示假阳性和错误的假设,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进行评估和排除,从而导致(尤其是在医疗保健领域)警报过多和警觉疲劳。
最终可能造成实际效率下降。
第
七,单一文化。
如果没有细心的设计,算法可能会制定成功公式,使系统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反应能力降低。
例如,社会心理学家承认,他们的一些实验无法被复制,不是因为最初的设计、分析或数据收集有任何错误,而是因为社会及其价值观发生了变化。
生命科学家使用的老鼠的基因是标准化的,但人们生活在一个不断演变的技术环境中,而且会经常不自觉地调整自己的行为。
撰写关于信息技术的文章,就是要瞄准一个似乎不仅在变化而且还在加速发展的目标。
最大的挑战之一是,有许多其他书涉及同样的问题。
正如我将在第二章中指出的那样,网络技术非但没有扼杀印刷书籍的出版,反而有助于增强印刷书籍的出版。
网络上最受欢迎的话题之一是网络本身。
2017年5月,一篇维基百科类文章列出了49页关于互联网方面的书籍,还有一些新的重要作品尚未被收录。
亚马逊仅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分类下就列出了超过2.4万种图书。
这是该章将讨论的信息丰富性的一个突出例证。
[11] 虽然这些书中有许多是技术专著或大学教科书,还有一些是关于经济和社会统计、数据库或社会实验的初步研究报告,而其他一些 (如本书)则是对它们的解释。
有很多重复的研究援引了类似的证据,这些研究可能会在同一个时期出现;平行的想法和相互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这种一拥而上的现象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文学理论家早就对互文性进行了阐述,而早在1898年,小说作家阿诺德·贝内特(Arnoldt)就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一个来自北方的男人》中,更生动地将雄伟的大英博物馆圆桌阅览室描绘成一场由推着书车的侍者来回服务的“活人对死者的食肉盛宴”。
[12] 因此,在大约125年后,我应该给这本书找到什么样的定位?凯文·凯利的《技术想要什么》和雷·库兹韦尔的《奇点临近》显然都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总的来说,技术乐观主义是好事。
鉴于令人沮丧的创新失败率,就连不切实际的希望也有助于为潜在有益的发明筹集资金。
宣传炒作不总是对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或消费者有好处,但可能对社会有好处。
另一种极端情况是牛津大学哲学家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Bostrom)的《超级智能》等技术预言家的作品。
快乐和恐惧的预言实际上有许多共同点。
它们都预见到了人类的转变,它们仅在这个世界是天堂还是地狱的问题上意见不
一。
[13] 效率悖论是对技术乌托邦主义持怀疑态度的作者提出的问题之
一,他们未必会对崩溃的可能性感到担忧。
有一些问题尤其值得讨论。
硅谷最彻底的反对派是叶夫根尼·莫罗佐夫,他将思辨的头脑与令人印象深刻的文章结合在一起。
莫罗佐夫早年生活在苏联时期的白俄罗斯,这让他意识到规划者的傲慢。
他成长于一个浓厚意识形态的社会,对西方信息技术产业及其崇拜者的缺点有着敏锐的眼光。
他的著作《技术至死》批评了他所谓的解决主义(采纳自建筑评论家的一个概念),即认为人类问题完全可以用技术进行补救的观点。
他认为对效率的追求忽视了严重的社会、政治和伦理后果,以及毫无根据地将创新等同于改进。
他同样会称之为“新效率”的是“效率低下、模棱两可和不透明的,不管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新掌权的极客和解决方案制定者毫无疑问地会一道提出反对意见”。
莫罗佐夫 观察到,“恰恰相反,这些恶习往往是伪装的美德”。
事实上,他反对“互联网”的存在本身,反对利用网络资源的强大组织提出的议程。
同时,他嘲笑一些网络批评者试图推广他们自己的进步解决方案,他认为这些努力都是徒劳的,更有效的沟通没有也不会解决社会、政治和伦理问题。
[14] 用莫罗佐夫的话说,我可能是一个“技术结构主义者”,不太关心“直接、有预期和理想的创新后果”,而更感兴趣的是“间接、意外和不受欢迎的后果”。
然而,我依然赞同莫罗佐夫的“后互联网”观点,并会援引社会学家威廉·艾萨克(WilliamIsaac)和多萝西·斯温·托马斯(DorothySwaineThomas)提出的托马斯定理。
即如果人们相信某样东西是真的,那么它的后果就是如此。
举一个平淡无奇的例子,有关汽油短缺的假新闻有时会造成真正的汽油短缺,因为惊慌失措的司机会更频繁地加满油箱。
与控制有影响力的网站的人的操纵相反,“互联网”可能是一个神话,但如果有足够多的人接受谷歌和脸书网站算法的中立性,那它就成了现实。
由于基于网络的商业和出版不会消失,而且它们已经产生了积极和消极的结果,我认为应该接受这种情况,并找到新的方法来融合直观和算法,模拟和数字。
值得赞扬的是,莫罗佐夫并不惧怕否定,正如我不惧怕消极一样。
我记得我的本科老师、科学史学家查尔斯·
C.吉利斯皮(CharlesC.Gillispie)在演讲中说过这样的话:“受过教育的人所面对的尴尬莫过于真正的陈词滥调。
”[15] 为了拯救这一切,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Carr)在《玻璃笼子:计算机如何改变了我们》中把效率确定为其价值观和战略的核心,如在谷歌的案例中,其核心表现为“固执到近乎偏执”。
该书还正确地强调了过度依赖算法会侵蚀人类技能的危险,卡尔在他的前一本书《浅薄》中有力地阐述了这一主题。
从相似的事实和研究中,本书得出了不同的结论。
卡尔是一名幻想破灭的信息技术专家,而我是一名历史学家。
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我发现,先是文字处 理,然后是电子图书馆资源帮助我恢复了一度中断的写作生涯。
因为我在研究方面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所以信息技术成了一个乘数。
对技术影响的悲观看法分散了人们对教育和自我学习的真正需求,他们认为这是将算法与直觉、数字与模拟相结合的最佳方式。
[16] 我认为是技术策展人詹姆斯·布莱克比(JamesBlackaby)最早提出了“玻璃笼子”的观点,即当我们从工具使用(老式的木工凳)转向工具管理(19世纪创新的工作台)时,我们失去了一些东西。
布莱克比展示了计算尺比几十年前取代它的电子设备要求工程师更直接地参与计算。
工程师、技术史学家亨利·彼得罗斯基(HenryPetroski)最近也表达了这一点。
卡尔没有呼吁恢复18世纪的农业生产方式,但他引用了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Frost)的一首十四行诗,称赞西塞人在农业生产中实现了身体和工具的统
一。
卡尔并不孤单,手工割草是一种兴盛的小众爱好。
多亏了现代搜索引擎,未来的割草机可以选择来自奥地利、意大利、丹麦和澳大利亚的镰刀。
人们还能找到其他有关手工工具的文学作品,比如《纽约时报》的评论文章《俄罗斯农民的锻炼方式》引用了托尔斯泰的话,“这让人想找一个草场,然后转身离开”。
在这种人与工具关系的启发下,卡尔对莫罗佐夫所谓“技术把我们从苦力中解放出来”的简单想法嗤之以鼻。
(这是对莫罗佐夫关于卡尔的“麦克卢汉式中庸主义”言论的回应吗?)但我怀疑,与更多的诗人和小说家相比,那些前现代的农民对在收获季节要从黎明到黄昏,一直为生计疲于奔命的状态肯定不大满意。
老彼得·布吕赫尔(PeterBruegel)的画作和版画对其中人物的肌肉力量、疲劳和饥渴的形象都经过了程式化处理,但也可能是更准确地反映了历史。
因此,我不同意我们这个时代肯定比过去几十年或几个世纪有更多“漫无目的和沮丧”,恰恰相反。
不能仅仅因为加入手工制作俱乐部更容易,就觉得它能让我们感到快乐和满足。
相反,我同意诺贝特·维纳(NorbertWiener)的观点,即如果运用得当,信息技术可以让我们摆脱头脑麻木的常规状态,从而腾出时间进 行更具创造性的活动。
使用羽毛笔时,工具、手和头脑之间存在一种密切的关系,它可能强制人们刻意书写了如此多的文学经典,但我很高兴自己不需要被逼着使用羽毛笔了。
[17] 凯茜·奥尼尔(CathyO'Neil)的《数学毁灭武器:大数据如何加剧不平等和威胁民主》一书向信息技术专业人员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警告。
与大多数技术批评者不同,奥尼尔一直站在发出警报的系统最前沿,认为无论是在工作场所的“健康”计划中,还是在以营利为目的的高等教育活动中,抑或在司法系统中,弱势人群都被算法瞄准成为目标。
她的愤世嫉俗使她的书成为迄今为止网上被广为评论的关于大数据和算法伦理的著作。
但在医学上,治疗比诊断更具挑战性。
她对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审视的提议引发了质疑。
首先,其他许多理论家和技术专家认为,有了机器学习,就不再能以研究常规程序的源代码的方式来理解人工智能了。
目前尚不清楚,即使最初的代码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得,吸收了大量新数据后,该程序的最终行为是否也能为人类所理解。
如果这些专家是正确的,那么只要走得足够远,就会创造出一台人类理性难以理解因而也无法审核的黑匣子机器。
其次,即使软件及其隐含的偏见是可以理解的,审视中也不乏令人沮丧的先例。
谁能忘记安然丑闻后安达信会计事务所的倒闭,以及其他大型会计和债券评级公司未能质疑导致2008年经济衰退的做法呢?为了客观起见,法官保护法医学和量刑软件不被披露和有效质疑。
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偏见的算法或许会取消与证人对质和反驳证据的权利。
[18] 法律学者弗兰克·帕斯卡尔(FrankPasquale)《黑箱社会》一书的出版先于《数学毁灭武器:大数据如何加剧不平等和威胁民主》,这本书至今仍是对立法者和监管者面临的来自秘密算法力量挑战的最佳论述。
帕斯卡尔建议采用欧洲管理大数据的方法,我也认为我们可以从中学习经验。
但善意的隐私法是一把双刃剑。
被庄严载入欧盟法律的“被遗忘权”或许是为了从搜索引擎结果中删除年轻人年 少轻狂的印记。
但是,保护无权无势者的法律也可能保护特权者。
《每日电讯报》刊登了在被调查者提出异议后被删除的报道摘要,其中包括一名医生、一名军官和一名涉及性侵案件的神职人员。
当然,新闻报道可能是不公平或不准确的,但删除已公布的信息却是一个令人担忧的先例。
帕斯卡尔的书和奥尼尔的书在揭秘硅谷方面互为补充。
他们担心的是对社会的影响。
奥尼尔对当今算法的良好运行印象深刻,这使得它们更加危险。
我自己强调的是,为什么算法的短期效率会阻碍创新而不是刺激创新。
[19] 大卫·萨克斯(DavidSax)的《模拟的复仇》令人信服地证明,从化学胶片到机械手表再到零售商店等旧媒介和体验具有极强的弹性,能够提供数字生活无法满足的人类需求。
自2001年史蒂夫·乔布斯创立苹果专卖店以来,从苹果专卖店的蓬勃发展,到笔记本再次广受欢迎,都生动地说明了触觉、具体体验的持续相关性,以及硅谷对它的认可。
这是对算法和人类直觉共存表示乐观的最佳呈现方式之
一,也是本书的主题。
[20] 但自从苹果专卖店出现后,乌云又重新出现了。
例如,从开业到2017年春天,美国百货商店的就业人数减少了1/3。
虽然仍有实体利润市场,但除沃尔玛外,历史悠久的大型连锁超市都没有足够的资源与亚马逊竞争。
西尔斯和梅西百货这两家大型连锁商店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反复萧条和衰退后,在2017年处境艰难。
亚马逊自己的零售部门不大可能提供苹果专卖店里那种现场设备调试以及个人支持和维修服务所带来的令人振奋的感觉。
宝丽来专利的新拥有者或许已经恢复了即时摄影,柯达公司也宣布了Ektachrome彩色幻灯片胶片的回归,虽然柯达的彩色胶片Kodachrome可能永远消失了,但35毫米电影胶片的制作仍在继续,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少数著名导演对制片公司和放映商的影响力。
[21] 经济学家兼作家蒂姆·哈福德(TimHarford)撰写的《混乱》一书在2016年问世,对自本杰明·富兰克林以来占据支配地位的商业模式进行了令人欣喜的纠正,之前的商业模式倡导组织、系统和有条不紊的习惯。
在大西洋两岸,厌倦了管理术语的公众为甜蜜的混乱而欢欣鼓舞,因为这本书提出了一个绝佳的证明,即无序可以是有创造力的,即便它本身有可能成为一种反例。
包括凯瑟琳·舒尔茨(KathrynSchultz)的《错误》和哈福德早些时候的《适应》都提到了这一点。
然而,和其他大多数商界领袖一样,哈福德低估了运气的作用。
借鉴20世纪8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的研究以及最近有关投资和管理回报的研究,金融经济学家摩西·利维(MosheLevy)认为,归因于人才的大部分超额收益可以归结于运气。
就像哈福德的幸存者偏差所反映的,关于成功的叙事只关注引人注目的例子,却没有考虑到有很多具有相同的特征、经历或战略的人并没有获得成功。
就像在华尔街一样,在一种市场环境中表现出色的风格也可能在另一种市场环境中遭遇失败。
考虑一下硅谷的大赢家的特点——亚马逊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夫·贝佐斯就出现在《混乱》里,我们从书中能发现他们高超的战略。
然而,我们同时也发现了潜在的致命危机。
[22] 赢得竞争的“混乱”行为可能在权力分配方面导致无所适从,哈福德大胆赞扬了唐纳德·特朗普的即兴风格,但使特朗普成为成功竞选者的原因似乎在其总统任期的第一年里未能获得广泛认可。
当然,另一位声名狼藉的总统比尔·克林顿赢得了连任,躲过了丑闻和弹劾,并仍被数百万人怀念,因此,哈福德或许是对的。
然而,批评人士也指出,混乱是导致克林顿在总统任期内毁誉参半的原因之
一。
[23] 在最好的情况下,混乱充分说明了社会学家查尔斯·蒂利(CharlesTilly)提出的“计划中的成就实际上是一连串意外事件的产物”。
但混乱并不是什么口号。
首先,字面上的混乱将付出高昂代价。
寻找放错位置的物品和文件所浪费的时间,或许没有得到真正科 学的估计——相关研究似乎是由销售追踪密钥和商业记录解决方案的公司资助的,但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发现,创造力带来的混乱可能需要花费宝贵的时间来平息。
其次,至少一位被哈福德描述为混乱的人,如查尔斯·达尔文可能曾经同时从事多个研究项目。
但达尔文是一名谨慎而有条理的人。
在剑桥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达尔文当年做的标签仍然受到高度重视。
最后,公司管理层并不真的相信绝大多数员工会在混乱中做出贡献,符合要求才是主流。
高效的绩效监控软件让大多数普通员工(不管是白领还是蓝领)不会发生创造性错误。
混乱可能只是另一个身份标志,是休闲过度阶级的特权。
研究人员指出,精英阶层会通过不合乎常理的行为来表明他们对大众标准并不在意,比如,脸书网站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就会在正式场合穿连帽衫,这种行为也被称为“红色运动鞋效应”。
这也难怪,因为哈福德的雇主、总部设在伦敦的《金融时报》在2017年5月说,该报读者是“世界上最受欢迎的受众,拥有最强的购买力和最高的净资产”。
换句话说,如果你还没有达到财富金字塔最上端1%的水平,那就不要轻易尝试扎克伯格的做法。
[24] 在本书即将付梓之际,另外两本书出现了:媒体研究学者、前音乐巡演经理和电影制片人乔纳森·塔普林(JonathanTaplin)的《快速行动,形成突破:脸书,谷歌和亚马逊如何造成文化困境和破坏民主》,作家、《新共和》的前编辑富兰克林·福尔(FranklinFoer)的《不在乎的世界:大科技对生存的威胁》。
我没有机会仔细阅读它们的论点,但我同意(使用类似的统计数据)平台经济给许多作家、艺术家、作曲家和音乐家带来了经济损失。
我就是遭遇损失的一员:我撰稿的《威尔逊季刊》《美国发明与技术遗产》《文明》,以及其他杂志不再出版了。
我也赞同福尔对追求数字效率和点击量可能损害质量的分析。
尤其是脸书控制了越来越大的广告份额,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
我现在只能就这两本书的书名发表两点初步评论。
首先,本书不只讨论媒体和艺术,还涵盖了更多 的专业领域,会讨论移动计算、应用程序和大数据兴起的积极和消极后果。
其次,尽管拥有数千亿美元资产的精英在理论上能对决策产生影响,但在2016年,他们无法阻止一位在气候变化、移民、多元化和婚姻平等等问题上持反对立场的总统候选人当选,即使他们很多人对此表示遗憾。
亲特朗普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的一篇文章支持拆分谷歌。
民主——或者至少是选举中的多数派——对硅谷带来的威胁可能要比来自硅谷自身的威胁更大,反之亦然。
[25] 《效率悖论》将两个追求效率的时代联系起来。
第一个时代始于18世纪末,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
这个时代用连续的生产过程代替了离散的生产过程,带给了我们工业化的经典形象:纸卷、线轴、钢丝,以及像查理·卓别林在电影《摩登时代》里展示的经典流水线。
当然,这些产业只代表了工业国家产出的一部分,但连续生产过程的理想激励了资本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事实上,多亏了工业机器人,连续生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劲,但它却失去了20世纪初期和中期曾带来的激情。
平台公司用软件将商品和服务的买卖双方聚集在一起,它代表了一种新的效率。
这并非基于机器和人力的组织化,而是基于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换。
随着搜索引擎、智能手机、社交媒体、网络软件的崛起,以及人工智能从20世纪90年代初的低潮中复苏,亚马逊网站开启的平台时代在21世纪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我正在研究这种新效率在媒体文化、教育、交通和医疗四个方面带来的影响,并想知道为什么这种效率带给大多数人的好处难以捉摸。
我的结论是,我们不必要么选择大数据、算法和效率,要么选择直觉、技能和经验。
我们需要适当的融合,我将提出实现这一目标的一套策略。
我将在第一章中提出,平台效率的问题在于,它促进了“颠覆性创新”概念的提出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所说的业务流程创新。
它用自动化软件来匹配买卖双方,从而降低了交易成本,社会效益是实实在在的,却也是有限的。
平台公司可以通过控制通胀来促进竞争,造 福消费者。
风险也是切实存在的,而且已经被批评者充分记录在案。
目前的寡头垄断以及潜在的垄断带来了消费者隐私权的丧失,有时服务协议被认为是不合情理的样板[Archicany的协议声称对客户的DNA(脱氧核糖核酸)数据拥有广泛的所有权]。
容易被人忽视的另一个结果是华尔街对平台效率的浪漫化。
它分散了资本和人才,使他们无法集中从事风险更大、最终更为广泛的创造市场的创新。
19世纪持续不断的工艺创新不仅减少了损耗,在取代某些工作的过程中,它们也创造了许多其他工作,这些新的工作往往技术性更强,薪资更高。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这一阶段的技术迭代是一次性事件,永远不会重演。
然而,我们有理由怀疑,基于对最近记录的推断,有关未来的任何说法都可能是不准确的。
[26] 第二章转向所有算法中最强大的算法——谷歌的网页排名带来的革命,其根源在于对科学影响力进行分析。
随着网络的出现和之后社交媒体的出现,这种最初的精英主义技术变成了一种民粹主义大环境。
在新闻和艺术领域,非但前《连线》编辑克里斯·安德森提出的“长尾”(畅销书排名榜以外的大量作品)概念无法适用,反而使随机的初始优势成倍扩大,形成了连锁效应。
移动计算、社交媒体,以及新的、据称更精确的广告选择的兴起,同时也威胁到了大部分新闻报道的效率,因为它把资源从新闻生产转移到了社交媒体算法优化上。
第三章探讨教育领域的效率运动。
高等教育中的计算机化运动至今已持续了近一个世纪,最早可以追溯到托马斯·爱迪生的一个梦想,即用100%高效的课堂电影取代他认为的“2%效率”的教科书。
尽管电脑在自我教育方面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进步,但无论是在考试还是在流行文化中,都没有证据表明电脑在提高大众识字率和算术水平方面有所斩获。
事实上,它们通过增强早期起步时建立的优势,一直在扩大而不是缩小不平等。
第四章探讨了数字地图和地理信息系统(GIS)引发的地理革命。
它把寻路与这一点联系在一起,即在没有指南针甚至地图的情况下,人们所使用的技巧。
在寻路方面,我们的技术已经变得更加精确,而又没那么复杂。
电子地图,尤其是显示在小屏幕移动设备上的电子地图,在提供关于特定地点的信息方面极为有效,但在将其置于更广泛的范围内则表现得远没那么出色,提供的信息很少。
很多时候,智能手机全球定位系统提供的直接路线恰好是我们需要的,人们都不想绕道出行。
不过,最快的路线不一定是最有效地安排旅程的路线。
全球定位系统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比人类自己找路更有效,但它可能是削弱人类最有价值的技能之
一。
第五章关于医学,探讨了提高医疗效率的计划对有效医疗造成的障碍。
实验室自动化是计算机化的杰出成就之
一。
现在,人类基因组测序的成本已经降到了中产阶级的可承受范围之内。
到目前为止,对遗传信息的解析还远没有那么简单。
电子病历曾经承诺要减轻医疗保健服务提供者书写病例的负担,尤其是因笔迹模糊闻名的医生。
但事实相反,对一致且详细的病历的需求增加了这些人的负担,创造了新的代码输入管理,以及一个家庭手工业的辅导机构对程序进行分类以获得最大的费用。
即使获得成功,医疗量化也会受限,因为患者并非被动接受干预。
他们的文化、价值观、对生活和对风险的态度,以及与医生的关系无法与结果分开。
虽然劝说的过程效率低下,但专业人员引导健康选择的能力往往比药物更重要。
与一本书构建起一种场景类似,一张大幅的地图不仅是其细节的总和,而且是一个应该作为整体来理解的领域,因此,患者的身心是一个整体,而不仅仅是一组注释和数据点,尽管这些数据可能是有帮助的。
[27] 最后一章提出了关于高效率和低效率的异端观点。
对计算机所擅长的细节的极限记忆可能不利于理解,在心理学家看来这并不奇怪。
借鉴社会学家哈里·柯林斯(HarryCollins)在《人工专家》一书中的研究成果,我认为每个人都掌握着大量隐性知识,这些隐性知识是 不可能在有生之年传授给人工智能程序的。
在我们做出职业决定或购买选择时,这些直观的理解都会发生作用,还会影响我们的教育、地方经验以及健康。
其结果是,更多的算法应该是效率最低的方式,因为它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进行更深入的分析(正如某些搜索引擎研究人员所主张的),并提供假设性建议而不是明确的答案。
算法可能是偶然的,但并非一定如此。
它们真正的挑战在于分析熟悉的问题,这可以追溯到最早期的市场调查,通过科学验证的既定模式得出的数据,可能被永远无法预测的方式创造性地颠覆。
市场调查曾宣称美国人喜欢廉价咖啡,但后来星巴克横空出世。
当然,毫无根据的直觉常常失败,这也是事实。
但行为经济学的发现不应对我们的直觉进行压制或恐吓,数据分析和隐性知识是互为补充而不是对立的。
[28] 算法本身需要并且正在获得新的方法。
被称为模糊逻辑的编程技术在探索世界的过程中接受了需要的次优解决方案。
曾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担任研究员的凯瑟琳·德尼加齐奥(CatherinD'Ignazio)发现,主要的搜索和媒体公司一直努力在服务和推荐中增加偶然性和信息多样性,但这并非易事。
如果可以应用更复杂和更有洞察力的算法,那么它们很可能源自学术项目和初创企业,而不是大型平台公司。
这些举措以及新一代对数字思维和模拟思维互利共存的洞察力,使我希望技术在金融危机和停滞不前之后能够再次实现自我更新发展。
[29] [1]“Newspapers: Fact /2015/04/29/newspapers-fact-sheet/. Sheet,” [2]RayKurzweil,TheAgeofSpiritualMachines:WhenComputers ExceedHumanIntelligence(NewYork:Penguin,2000),105;RayKurzweil,“The ComingMergingofMindandMachine,”ScientificAmerican,March23,2009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2008), /article/merging-of-mind-and-machine/. [3]Edward
A.RossquotedinHerbertM.Kliebard,TheStrugglefortheAmericanCurriculum,1893–1958(NewYork:RoutledgeFalmer,2004),76–78; YoramBauman,“Solow's‘ComputerAge’Quote:ADefinitiveCitation,” July14,2010,puter-age-quote-a- definitive-citation/. [4]“JulesVerneuratelyPredictsWhatthe20thCenturyWillLook LikeinHisLostNovel,ParisintheTwentiethCentury(1863),”OpenCulture,January25,2016,/2016/01/jules-verne- urately-predicts-what-the-20th-century-will-look-like.html. [5]Robert
J.Michaels,“EnergyEfficiencyandClimatePolicy:The Rebound Dilemma,” /wp- content/uploads/2012/07/NJI_IER_MichaelsStudy_WEB_20120706_v5.pdf. [6]Mick
Hamer,“HorsePowerBeatsDiesel,”NewScientist,July13,2002,11;MichaelPollan,TheBotanyofDesire(NewYork:RandomHouse,2001), 230–31. [7]DaveRosenberg,“SiliconValleyTechiesTurnBackTime,”SanFranciscoChronicle,March9,2013;seealsoMattRichtel,“ASiliconValleySchoolThatDoesn'tCompute,”NewYorkTimes,October23,2011. [8]NelsonD.Schwartz,“TheMiddleClassIsSteadilyEroding.Askthe BusinessWorld,”NewYorkTimes,February3,2014;DavidK.Randall,“OnlytheStoreIsGone,”NewYorkTimes,February19,2006;ArthurM.Okun,EqualityandEfficienc:TheBigTradeoff(Washington,
D.C.:BrookingsInstitutionPress,2015);FredHirsch,SocialLimitstoGrowth(Cambridge, 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8). [9]EvgenyMorozov,ToSaveEverything,ClickHere:TheFollyofTechnologicalSolutionism(NewYork:PublicAffairs,2013),313–14. [10]MikeIsaac,“Uber'sCultureofGutsinessUnderReview,”NewYorkTimes,February23,2017. [11]/wiki/Category:Books_about_the_. [12]Arnoldt,AManfromtheNorth(NewYork:eH.DoranCo.,1911),69,citedinRoyPorter,“ReadingIsBadforYourHealth,”HistoryToday48,no.3(March1998):11–16. [13]SeemyreviewsoftheoptimisticKevinKelly'sWhatTechnologyWants,IssuesinScienceandTechnology27,no.1(Fall2010), (“Technophilia'sBigTent”),/271/br_tenner-2/;andthe skepticalDavidEdgerton'sTheShockoftheOldintheLondonReviewofBooks,May10,2007(“APlaceforHype”);RaffiKhatchadourian,“TheDoomsdayInvention,”NewYorker,November23,2015. [14]Morozov,ToSaveEverything,
6.Morozov'suseof“solutionism” reflectsacuriousgapintheEnglishlanguage.Foralltheinfluenceoftheefficiencymovementinthelateeenthandearlytwentiethcenturies,therewasnowordforefficiencyasamovement,exceptTaylorism,whichwasonlyonefacetofit.Themovementhaditscritics,butfewdaredcallthemselvesantiefficient. [15]Ibid.,171. [16]DavidCarr,TheGlassCage:HowComputersAreChangingUs(NewYork:
W.W.Norton,2014),211–224. [17]JamesR.Blackaby,“HowtheWorkbenchChangedtheNatureofWork,” InventionandTechnology2,no.2(Fall1986):27–30;HenryPetroski,“SlideRules:GonebutNototten,”AmericanScientist105,no.3(May–June2017):148ff;JeremyHastings,“TheRussianPeasant'sWorkout,”NewYorkTimes,June12,2016;LianaVardi,“ImaginingtheHarvestinEarlyModernEurope,”AmericanHistoricalReview101,no.5(December1996):1364–66;Morozov,ToSaveEverything,20–21. [18]CathyO'Neil,WeaponsofMathDestruction:HowBigDataIncreasesInequalityandThreatensDemocracy(NewYork:Crown,2016),esp.199–218;WillKnight,“TheDarkSecretattheHeartofAI,”TechnologyReview20, no.3(May–June2017):54–63;StephenJ.Dubner,“WhyUberIsanEconomist'sDream,”(includingtranscriptofNationalPublicRadiointerview),September7,2016,/podcast/ubereconomists-dream/. [19]FrankPasquale,TheBlackBoxSociety:TheSecretAlgorithmsThatControlMoneyandInform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 2015);examplesofdeletedstoriesfromDanielShuchman,reviewofFloyd Abrams,TheSouloftheFirstAmendment,inWallStreetJournal,May8, 2017. [20]DavidSax,TheRevengeofAnalog:RealThingsandWhyTheyMatter (NewYork:PublicAffairs,2016). [21]PaulKrugman,“WhyDon'tAllJobsMatter?
”NewYorkTimes,April17,2017;Sax,TheRevengeofAnalog;onthestateofretailing,see herMims,“ThreeDifficultLessonsforTraditionalRetailers,” WallStreetJournal,April30,2017. [22]TimHarford,Messy:ThePowerofDisordertoTransformOurLives (NewYork:Penguin,2016);MosheLevy,“InvestingIsMoreLuckThan Talent,”Nautilus,issue44(January19,2017). [23]MichaelShermer,“SurvivingStatistics,”ScientificAmerica311, no.3(September2014):94;KarenDamato,“WhenItComestoFund Performance,HistoryIsOftenWrittenbytheWallWinners,”StreetJournal, August6,2012;JamesB.Stewart,“CaseStudyinChaos:HowManagement ExpertsGradeaTrumpWhiteHouse,”NewYorkTimes,February3,2017;DavidA.Graham,“Trump'sDangerousLoveofImprovisation,”Atlantic,August9, 2017;BryanBurrough,“TheSeat-of-the-PantsPresidency,”reviewofNigel Hamilton,BillClinton:MasteringthePresidency,WashingtonPost,July15, 2007. [24]FrancescaGino,“LeadersSayTheyWantNonconformistEmployees. TheySureDon'tActLikeIt,”WallStreetJournal,May17,2017;MatthewHutson,“ThePoweroftheHoodie-WearingC.E.O.,”NewYorker,December17, 2013;“FTAdvantage,”/d/. [25]JonathanTaplin,MoveFastandBreakThings:HowFacebook,Google,andAmazonCorneredCultureandUnderminedDemocracy(NewYork:Little,Brown,2017);FranklinFoer,WorldWithoutMind:TheExistentialThreatofBigTech(NewYork:Penguin,2017);FredCampbell,“TrumpShouldBreakUp Google'sMediaMonopoly,”Breitbart,June21,2017.mentsonFoerare basedonhisacuteanalysisofthetechnologyindustrymentalityatTheNewRepublicin“WhenSiliconValleyTookOverJournalism,”Atlantic, September2017,28–31,whichIciteinChapterTwo. [26]JoelWinston,“TakesDNAOwnershipRights Customers and Their Relatives,” May 17, -takes-dna-ownership-rightsfrom- customers-and-their-relatives-dbafeed02b9e. from
2017, [27]ElisabethRosenthal,“TheCodeRush,”NewYorkTimesMagazine, April2,2017,42ff. [28]StevenPearlstein,“ConsumerConformity:WhyWeLikeThickClam Chowder(andOtherInferiorProducts),”WashingtonPost,July25,2011. [29]Seehersite,/. 第一章从工厂到平台 19世纪的效率如何在21世纪被重新定义 我们生活在第二个注重效率的时代。
记者和企业家不再像过去那样经常使用效率这个词,我们稍后将看到一些同义词。
但是,我们始终意识到,无论是通过增加产量或利润,还是减少时间,都要从现有投入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的价值。
我认为短期内过于专注效率可能会损害长远的效率,一些人会认为这是异端邪说,而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
我希望表明,人们在对此进行反思时,将它看作一个显而易见的命题。
正如我在后文会指出的,将有效的算法与整体的模拟相结合,可以比单独使用任何一种方式产生更好的结果。
但这并不总是一目了然的,将效率视为在过去约两百年中逐渐形成的一个概念,并将其看作一套更古老的实践会很有帮助。
正如我们看到的,效率这一概念出现在蒸汽时代,其最佳表达方式不是用18世纪对工厂里的劳动分工来体现(本质上仍然如此),而是用机器连续生产代替手工作坊来作为例证。
最伟大的企业投入了巨大的资金,雇用了10万名甚至更多的工人以保持工厂运转。
古典经济自由主义和与之对立的马克思主义等学说都反映了这种模式。
就连共产党政府也羡慕西方的大规模生产,这一点也不奇怪。
20世纪中叶,瑞士建筑师兼评论家西格弗里德·吉迪恩(SiegfriedGiedion)和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
J.布尔斯廷(DanielJ.Boorstin)首先强调了不间断(“连续过程”)技术对批量生产的 重要性。
轧辊、皮带和其他设备不仅改变了生产,也改变了消费的性质。
与20世纪50年代在电视上播出的《产业阅兵》系列节目相比,现在诸如《如何制造》之类的有线电视节目揭示了如今工业流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自动化。
但是,进一步降低装配线上的劳动力成本并不是我们感兴趣的那种效率。
一种新型的企业占领了弗拉基米尔·列宁所说的经济制高点,主导了经济议程,此前即使是最大胆的未来主义者也没预见到这种类型的企业。
硅谷唤起了人们曾经由东北部和中西部肮脏的工业大都市所激发的钦佩、恐惧和蔑视,尽管乘坐汽车或火车前往芝加哥、底特律或匹兹堡仍然是一种视觉上的震撼体验,但旧金山以南的半岛更能令人惊叹财富之巨。
尽管那里的公司服务器群可能并不起眼地分散在全球各地,然而,硅谷巨头们对社会组织的想法与列宁同样激进,他们与古典共产主义一样都对效率抱有强烈的信念。
[1] 这一章将考察连续过程的效率(那是让画家、摄影师和电影制片人为之着迷和敬畏的效率)与平台效率之间的区别。
平台效率更有利可图,但具有隐蔽性,而且需要极大的想象力才能以戏剧化的方式呈现。
比如,网络平台应用的在线匹配不仅利用了集成电路效率的稳步提高,而且利用了巧妙的计算技术,即算法来使电路的运算速度成倍提高。
这种效率提出了一个深刻的问题。
为什么这些平台对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的自我满意度的影响不明显?为什么世界各地有的公民对他们的政府如此不满,以至于愿意寻求极端的解决办法?原因之一可能是平台革命一直在将人才和资金从其他可能更具变革性的技术项目中抢走。
我无法确定哪些项目具有潜力,也不排除它们已经很先进并可能很快就将硕果累累。
毕竟,美国在“二战”后的繁荣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像广播电视和干式复印这样的技术创新,这些创新是在大萧条最黑暗的年代里发展起来的,艾伦·图灵的理论研究也使平台经济成为可能。
问题是,为什么迄今为止对投资者(尤其是早期的投资者)如此有利可图的平台公司一直表现不佳?拥趸会坚持认为,重大创新通常会带来一时的失望,最好的结果尚未到来。
这尤其是脸书及其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的观点,他在2017年年初发表了一份宣言,承认了错误,并发誓要在脸书用户的帮助下建立更好的社区和更美好的星球。
对许多竞争对手来说,这样的承诺长期以来都是“未来的炒作”“硅谷的万用灵药”——借用失望的技术专家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出版的书的书名。
尤其是对左翼批评者来说,新老板与旧老板并没有太大区别,只是配备了先进的监视和操纵设备,取代了昔日的老派做法。
一些谨慎的记者在扎克伯格等人的宣言中看到了自己的职业生涯面临的生存威胁。
我不确定有哪个组织真的有这样的权力。
我将在本章结尾提出,平台效率最严重的意外后果可能是它的机会成本,从长远来看,它对资源的要求将更有助于提高真正的效率。
[2] 效率运动的一个悖论在于,尽管数据令人泄气,但促进效率和理性的创新还是在直觉和情感的驱动下出现了。
这并不意味着直觉比基于数据的分析更可靠,而是数据和分析数据的工具永远无法取代想象力来预见人类未来的行为模式。
大多数这样的直觉都失败了,一些例外充斥在励志书籍和商业书籍中。
风险投资的失败率很高。
然而,在效率低下的大旋涡中出现了一些世界上最高效的技术。
效率的历史应当从自然本身开始。
正如生物物理学家所发现的,DNA比最先进的技术系统储存的能量更密集,对基因表达的控制使复杂而强壮的生物能够以惊人的速度发育,果蝇基因组的微小变化会导致截然不同的行为。
进化在优化信息流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利用有限的资源是我们的生物遗产。
[3] 正如人类学和考古学证据所揭示的,对效率的追求似乎也被纳入了人类生物学。
人类在工具制造方面已经经历了数万年的创新,这些创新有时会进入死胡同,但偶尔也会产生具有功能性的杰作,澳大利 亚原住民的回旋镖或中亚草原游牧民的复合弓就是其中的代表。
有没有比传统方式锻造的日本刀更锋利的刀具,或者比哥伦布到达以前的美洲原住民熟练使用的黑曜石刀更锐利的切削工具呢? 在西方也是如此,许多古罗马的医疗设备都很好地发挥了用途,以至于它们的质量直到现代才被类似的仪器超越。
罗马军队以令敌人眼花缭乱的速度集结、修建桥梁和防御工事而闻名。
当时甚至有一种大规模生产的并加盖早期商标印章的油灯在市场上销售。
[4] 与50年前的历史学家所承认的相比,最近的考古学揭示了古代世界更多的动力和技术创新。
例如,奴隶经济并不排斥使用像水车一样省力的工具,就像19世纪初期奴隶制下的甘蔗种植园使用蒸汽机一样,这些改进在实践中提高了效率。
但我们所知道的效率概念在古代生活中并没有明确的提法。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以及包括埃及在内的其他地中海和近东社会)的行政和档案保存系统已有数千年历史,但他们并没有系统地提高产出的理论。
古典历史学家彼得·托内曼(PeterThonemann)强调,罗马社会是建立在庇护、忠诚和义务的原则上的。
没有关于工资、利息或生产率的理论。
威望往往比功能更重要。
书籍被写成卷轴,放在箱子里存放起来。
书写是延续的,字与字之间没有空格。
加上空格会增加莎草纸和羊皮纸的使用量,但会使阅读和教育变得容易得多。
解决阅读的困难——拿着卷轴,确定从哪儿断句——是受过教育的人技巧展示的一部分。
这种低效是一种特点,而不是一种缺陷。
[5] 在欧洲,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是一个提高实际效率的时代。
今天看来如此古怪和老套的黑色手写字体,对那些习惯了它的人来说,其实是一种相对快速和清晰的写法。
罗马人有光学知识、玻璃吹制和冶金技术,能制造出眼镜,但没有市场。
上了年纪的文化人曾经让受过教育的奴隶读书给他们听,罗马人制造了很好的轧布机,可以使用青铜铸造的字母,但他们觉得没有必要印刷。
[6] 到了18世纪,德尼·狄德罗(DenisDiderot)的《百科全书》和他的苏格兰模仿品《不列颠百科全书》总结了几十种行业的知识和进步。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证明了将制造针的整个工作流程分成不同的工序,可以使每个工人每天制造针的数量成倍增加。
在中世纪的波斯,针的制造有更精细的分工。
[7] 19世纪和20世纪的效率意识并不十分明显。
作为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家,斯密是一位杰出的先驱。
不管是自由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都会对衡量一个制针车间比传统车间的生产率高多少感兴趣。
许多产品仍然是根据手工传统和风格制造的,而不是经过系统研究客户需要后推出的。
法国技术理论家雅克·埃吕尔(JacquesEllul)曾指出,中世纪晚期为雇佣兵制造刀剑的装甲工匠都遵循一种工艺传统和装饰风格,而不研究战斗的人体工程学。
每个士兵都必须使自己的战斗风格适应其装备,而不是令装备来适应自己的战斗风格。
[8] 没有哪位18世纪的人物比本杰明·富兰克林更有名,因为他能将实际智慧与对科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尽管或由于他接受正规教育的局限性。
富兰克林和他的同时代人——他从未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并鼓励他人进一步改造——设计的壁炉衬里极大地提高了传统壁炉的效率。
但18世纪末的发明家仍然没有用科学的方法量化每单位木材节省的热量。
直到19世纪中叶,像酿酒师和科学家詹姆斯·焦耳这样的思想家才推出了测量热量的统一单位:英制热量单位和公制热量单位——焦耳。
引入现代效率的两项发明是19世纪初其他天才的杰作,现在主要为专家所熟知:装配工人奥利弗·埃文斯(OliverEvans)和造纸商亨利·富德里尼耶(HenryFourdrinier)。
如果我们看看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会发现当时许多作坊与达·芬奇或伽利略时代的作坊并没有太大不同。
尽管斯密的分工原则开始传播开来,但作坊主还是 在工人和学徒的协助下制作每种产品。
货物仍然是被单独地或小批量地制造出来的。
[9] 奥利弗·埃文斯是连续过程效率的创始人。
他的知名度不及富兰克林、埃利·惠特尼、塞缪尔·摩尔斯或托马斯·爱迪生,但在两个世纪里,他的影响力至少不亚于这些人。
正如西格弗里德·吉迪恩在其经典著作《机械化的决定作用》中所写,在美国出现真正的工业之前,“一个孤独而有先见之明的头脑设计了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从一个操作到另一个操作的机械运输可能会将人们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
就像通过一连串的铲斗将原料运送到磨机的顶部,并在重力作用下通过皮带、螺杆和其他连续输送装置输送到铣削的每个阶段。
分开来看,这些环节并不完全是新事物,有些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
建立一个能加工原材料和半成品的综合系统的想法在提高效率方面仍然是惊人的进步。
埃文斯的系统似乎缺乏富兰克林的说服力,但他具有“远见卓识”,吉迪恩正确地总结道:“奥利弗·埃文斯的发明开启了人类历史的新篇章。
”[10] 经典现代效率的第二个里程碑是富德里尼耶造纸厂。
从被引入中国直到今天,它在日本仍被应用于和纸制造。
和纸是用纤维制成的单张纸。
技术高超的造纸工人组成了强大的工会垄断技术,使书籍和报纸的价格不菲。
一位名为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Nicolas-LouisRobert)的法国印刷匠是第一位认识到连续纸张生产潜力的人。
正如历史学家马克·库兰斯基(MarkKurlansky)指出的,罗伯特发明的金属丝框架早在传送带发明之前就使用了同样的原理。
(在1804年,皇家海军在制造压缩饼干时首次使用了这项技术。
)在他的机器中,移动的筛网吸收了湿纤维,就像纸张工匠所做的那样,横向搅拌纸浆以使其均匀分布。
除去水分后,半成品纸被卷到一起,最后被加热以使其干燥。
造纸商亨利和戴维·富德里尼耶对“罗伯特流程”进行了技术改进,但不足以使其实用化,他们被迫宣布破产。
工程师布赖恩·东金(BryanDonkin)根据罗伯特的想法最终制造出了可用的连续 造纸机。
这种复杂的关系揭示了连续过程效率的一个重要特点:它是失败、协作和竞争的结果,甚至比其他创新更重要。
[11] 纸张、面粉和饼干的生产效率体现了两个世纪以来消费品生产的效率。
圆周运动无处不在:在战争中,它创造了左轮手枪和马克沁机枪。
和平时期,在英国与拿破仑的战争中,苏格兰引入的不起眼的棉线轴,使艾萨克·辛格(IssacSinger)的缝纫机和服装的大规模生产成为可能(在整个18世纪,线一般都是由亚麻制成的,仅以绞线的形式出售)。
作为19世纪最著名的发明,托马斯·爱迪生的电灯泡最初的市场很有限。
直到19世纪90年代末,一支由两个熟练的玻璃吹制工组成的团队要花整整一分钟,才能生产出两个玻璃壳,这一生产方法近两千年来未曾改变过。
由于康宁玻璃工厂几十年来的技术改进,到1926年,新一代自动灯泡机能在24小时里生产出40万个空灯泡。
到20世纪30年代,这个数字先是增加到100万,然后进一步达到300万。
事实证明,尼古拉斯-路易斯·罗伯特和富德里尼耶对大众阅读和教育非常重要,现在默默无闻的发明家威廉·伍兹(WilliamWoods)也做出了类似贡献,他利用连续过程效率实现了爱迪生发明的灯泡的潜力。
其他机械发明者实现了玻璃瓶和金属罐的完全自动化生产和灌装,以及在今天的机械化轮胎工厂中仍然使用的混合橡胶巨型旋转搅拌机。
在农场里,连续作业的收割机取代了镰刀,在20世纪,通过装有连续传送带的烘干机,新收获的谷物得到了烘干。
欧洲和美国的高级奶制品公司甚至在缓慢旋转的牛棚里给奶牛挤奶。
正如吉迪恩所说,芝加哥肉类加工业的肉类分解流水线激发了以亨利·福特为首的工业家的生产流程。
到20世纪30年代初,汽车制造商使用的钢板是在一个连续轧制过程中被生产出来的,这一过程是由钢铁厂负责人约翰·
B.蒂图斯(JohnB.Tytus)首创的,他的灵感来自其祖父的富德里尼耶造纸机的设计。
[12]19世纪和20世纪美国最伟大的一些基础设施也利用了反复旋转运动带来的效率。
从布鲁克林大桥到金门大桥,这些悬索桥的巨大钢缆是约翰·勒布林(JohnRoebling)父子发明的机 械和工人旋转而成的。
就连新闻和文学也是用连续的旋转方法传播的。
巨大的长网造纸机制造出一卷卷的新闻纸,为约瑟夫·普利策(JosephPulitzer)和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RandolphHearst)等报业大亨的高速印刷机提供支持。
[13] 购物和娱乐业发生了转变。
百货公司的顾客通过旋转门进进出出,走过一块块地板和环形楼梯带。
西方主要的铁路不断运送大量货物和数以百万计的乘客,这是成熟的工业时代的终极体现和对管理的挑战。
北大西洋的远洋班轮按照可靠、固定的航程航行,精英乘客开始期待在几百年来闻所未闻的准时准点到达。
如果泰坦尼克号船长因为避开海冰而放慢速度,就像后来的许多作家和电影导演认为的那样,那么这艘船将会迟到一天,海洋历史学家会因为他的胆怯而不是谨慎记住他(如果有的话)。
[14] 虽然许多新工艺的发明者是从车间里走出来的,有时能积累巨大的财富,但实业家和中产阶级都开始意识到经验技能是不够的。
随着过程效率的不断提高,出现了一套新的价值和一组新的词汇,这被称为第一次效率运动。
它不仅激励了投资者、银行家和有抱负的经理人,而且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专业人士投身其中。
19世纪和20世纪初没有单一的工业效率学说,但有一套坚实的假设。
首先是量化理论。
虽然对本杰明·富兰克林来说,衡量他的壁炉的输出效率与传统壁炉的输出效率可能并不重要,但19世纪的精英们对测量的热情与日俱增。
新的统计技术使人们能够呈现和评价数据,以便做出更准确的决策。
会计专业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对上市公司至关重要。
物理学家和发明家开尔文勋爵威廉·汤姆森(WilliamThomson)在1883年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他在一次广为流传的演讲中说:“当你能测量你所说的东西并用数字表达时,说明你了解这些东西。
但是,当你无法测量它,无法用数字来表达时,你的知识就是微不足道的和难以令人满意的。
”[15] 经典的效率也取决于规模。
虽然进步运动的左派担心垄断,独立的生产者和商人则声称垄断不公平,但左派和右派往往一致认为大公司对消费者和工人都有利。
从1875年安德鲁·卡内基旗下的埃德加·汤姆森工厂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德多克投产后,正是规模使钢铁厂得以安装最高效、最昂贵的新机械,从而压低了价格,给竞争者带来了压力。
正是规模让约翰·
D.洛克菲勒垄断了石油的分销、精炼和销售,即使在标准石油公司因反托拉斯法被分拆之后,也有很大一部分依旧在发挥作用。
同样是规模使最早的工业机器人成为可能:早在1921年,受福特装配线的启发,密尔沃基的
A.O.史密斯公司就开始出售一种能够每天铆接一万辆汽车机身的机器人。
[16] 伴随着规模增长而来的是科层制和职业化。
就连电报运营商托马斯·爱迪生这样在工作中不断学习的企业家也意识到,他们需要高学历的工程师和科学家,以及不得不开设新的技术学校和课程的美国大学。
一个又一个以往凭借经验的职业被重塑为需要学校、学位和学术期刊参与的职业,卡内基、梅隆、洛克菲勒、范德比尔特和古根海姆在此基础上建立了商业王国。
需要规范、考试和证书的不仅包括医学、法律和工程,还包括图书馆学、公共会计学、新闻和商业管理学等新的学术领域。
甚至在车间里,也设立了新岗位,如工具室文员,以使拥有高技能的工人尽可能多地使用机器。
[17] 伴随着规模的扩张,规划也拥有更多的机会和责任。
高效的公司不仅规模庞大,足以主导市场,而且能够从内部孵化未来的技术。
通用电气、杜邦、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IBM(国际商用机器公司)等巨头都为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感到骄傲。
虽然贝尔实验室现在主要因为引入晶体管而闻名遐迩,但就它的研究而言,每一项成果都是重要的。
根据《财富》杂志1936年刊登的两篇令人钦佩的文章所述,即使在大萧条时期,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图纳的铁路实验室也在对从灯泡到餐车等各种设备的供应进行测试,称“这个国家比土耳其或乌拉 圭更大。
它的整个行为就像一个国家,种种举动关系到数以十万计公民的生活”。
[18] 正如经济学家戴维·韦尔(DavidWeil)在其著作《有裂痕的工作场所》中所描述的,20世纪规模庞大的企业在劳动力市场上占据优势。
大型国有企业不仅能够支付比大多数私营企业更高的工资并提供更好的工作条件,而且在医疗计划、养老金和其他福利方面也处于领先地位。
熟练雇员的低离职率进一步提升了效率。
[19] 传统的企业效率也取决于与政府官僚机构的关系。
为了提高政府的效率,公司高管反对政府的监管,并推荐自己的管理方式。
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许多公司非常依赖政府合同,这种依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进一步加深。
技术史学家已经证明,当可互换部件的理想在技术上仍然有挑战性和高昂成本时,国家军械库是如何促进大规模生产的。
IBM被从大萧条中解救出来,是因为新的社会保障体系对雇主提出了记账要求。
IBM的创始人和领导者、销售大师托马斯·沃森只是凭直觉认为,世界很快就会需要他所储备的昂贵设备以及他的研究实验室在大萧条早期开发出来的创意。
他更理性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败下阵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仙童半导体生产的集成电路的早期市场几乎完全与军事和太空计划有关,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
关于国防合同的严格规范也在20世纪中叶提升了仙童半导体公司和其他相关公司的产品可靠性水平,否则这些公司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达到这一标准。
[20] 企业高管认为,他们有权利也有义务规划未来的技术。
有些公司在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博览会上布设展台,试图用它们在设计图上创造出的奇迹来鼓舞公众,包括需要政治批准的基础设施改建。
“二战”结束后,管理学者和专家鼓励企业领导人将自己视为国家未来的私人规划者,为所有利益攸关方谋福利。
有人质疑,贝尔系统公司、通用汽车公司、通用电气公司、伊士曼柯达公司和IBM等是否能为了公 共利益无限制地进行管理创新。
既然这些公司资金雄厚的实验室有令人印象深刻的成绩,为什么它们不这样做呢?而且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像宝丽来、微软和苹果电脑这样的新公司一般都是为之前的大公司提供补充,而不是对其造成威胁。
就连施乐公司——或许是战后时代最初的颠覆性公司——都没有在摄影方面与柯达公司竞争,也没有与IBM在计算机硬件方面竞争,尽管其同样拥有出色的研究人员。
最后,20世纪的效率是精英主义的。
正如塞缪尔·哈伯(SamuelHaber)、托马斯·
C.伦纳德(ThomasC.Leonard)和其他人所证明的,引导不那么具有洞察力的大众的想法,一直在眼光敏锐的少数派的头脑中萦绕,无论是在产业、政府还是在教育领域,都是如此。
就连最敌视企业精英的人之
一、经济学家索尔斯坦·凡勃伦也设想过建立一个由技术人员组成的新联盟,他们可以把国家的产出提高3倍到12倍。
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在内的主流政界人士都支持白人种族的优越性和优胜劣汰理论,并对最聪明的男性和女性的生育率下降和自杀感到担忧。
[21] 大公司的效率信条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引入的对时间和动作的研究以及对工会的厌恶,在产业工程师弗兰克和莉莲·吉尔巴思(LillianGilbreth)的带领下变得更加友好与温和,后者因为按照效率理念管理家庭和养育子女而享誉全国。
莉莲·吉尔巴思还赞助了一些关于座位对工人的健康和生产率影响的初步研究。
家长式的“福利资本主义”公司,比如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直接向朋友和邻居出售商品的先驱,这一直销网络后来被雅芳和安利等公司进一步完善),以及代顿的国家出纳机公司,它们使健康和文化成为雇员生活的一部分。
(位于布法罗的拉金肥皂公司行政大楼在20世纪50年代该公司倒闭后不幸被拆除,大楼里面有一个中庭、一个早期的空调系统。
)对于少数几家领先的公司来说,效率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22] 企业效率理念的最大变化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的玛格丽特·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时期,当时的能源冲击、通胀和劳资纠纷对人们固有的商业理念构成了挑战。
1966年,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出版了《不连续的时代》。
值得注意的是,他认为必须保留一些综合效率。
全球商业环境变得更加多样化和多元化,“我们需要政府作为组织社会的核心机构。
我们需要一个能够表达共同愿景并使每个组织能够做出自己最大贡献的机构”。
[23] 作为温和的左派,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警告说,对公共产品的投资不足,但他也承认大公司(和工会)是技术进步和社会的必要因素。
就连苏联也以自己的方式同意关于效率的许多理念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公开接受了亨利·福特的现代主义设想,从农业机械化到庞大的工厂,都是这一理念的反映。
苏联的五年计划基于公认的福特生产方法的效率,斯大林本人也称赞美国的效率是“一种既不知道也不承认障碍的不屈不挠的力量”。
歌颂集体农场的苏联电影制片人并不羞于让贴在拖拉机散热器上的福特标志清晰可见。
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的矛盾注定会导致周期性危机和大规模失业。
苏联的计划将实现技术效率的承诺并超越西方。
苏联科技史学家斯拉瓦·格罗维奇(SlavaGerovitch)发现了1957年苏联科学院的一份机密报告,报告宣称:“用计算机进行统计和规划,就其效率而言,必须具有绝对特殊的意义。
在大多数情况下,计算机将使决策速度提高数百倍,并避免目前参与这些活动的笨拙的官僚机构所造成的错误。
”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规划者和计算机理论家认为,一个中央计划的国家网络——格罗维奇称之为“内部网络”——最终能够实现苏维埃国家的经济目标,即整个经济理性和谐地发展。
[24] 1991年的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像马格尼奥戈尔斯克这样的大型建筑群受到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启发,类似美国钢铁公司的企业曾经是苏联体系的骄傲,现在却被认为在浪费能源和 其他自然资源,而且效率低下。
(1988年入住苏联科学院莫斯科饭店时,我遇到了一位芬兰林业顾问,他前来帮助苏联进行产业改革;他提到苏联每公顷土地的产量只有他自己国家的1/4。
)[25] 但西方正在发生另一种转变。
在IBM个人电脑开始改变办公室工作的10年后,随着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公司面临危机和新商业帝国的出现,一种新型的资本主义效率正在形成。
并不是说连续过程的效率被放弃了,它仍然存在,而且还让很多人发家致富,但在一直期待会出现“后工业时代”的西方,它已经失去了激情。
相比之下,海外承包商可以从农村调集年轻人加入工业大军。
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的这20来年是过渡时期,他们引入了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并采用了一些新的自我识别和贬义的名称:“里根主义”、“撒切尔主义”、“第三条道路”和(目前最受左派欢迎的)“新自由主义”。
1945—1975年是一个黄金时代。
阿拉伯世界的石油危机和日本的崛起所制造的恐惧取代了广泛的乐观情绪。
一个重大变化是行政级别的减少。
如今很少有人对等级制组织有好感。
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欧洲公务员的谨慎作风让一心想遏制任人唯亲和腐败的美国改革者羡慕不已。
到了20世纪50年代末和60年代,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在如小艾尔弗雷德·
D.钱德勒(AlfredD.Chandler,Jr.)等一些商业史学家和理论家将多部门公司誉为技术理性的化身时,学术界和大众评论家却在嘲笑它的单一性、装配线的单调乏味以及中层管理者官僚化的思维方式。
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当华尔街的企业家开始通过恶意收购和杠杆收购挑战管理层时,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股价和股东价值的即时回报超过了旧式的企业政治家风范。
德鲁克的《不连续的时代》中有几个章节涉及“管理”“工会”“政府”“知识型工人”等主题,但没有提到股东或资本市场。
与行政扁平化密切相关的是股东价值理论的兴起。
在一定程度上,由于私营和公共部门养老基金的增长,基金经理正受到机构投资者越来越多的审查,因为机构投资者希望为他们的客户带来最大的回报。
质疑管理的孤立和自满,起初这似乎是一个进步的原因。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是新政自由主义者首先提出了这一想法。
小阿道夫·
A.伯勒(AdolfA.Berle,Jr.)和加迪纳·米恩斯(GardinerMeans)曾在20世纪30年代初警告说,控制公司决策但不拥有公司股份的专业管理阶层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现在是时候让投资者和所有者坚持自己的权利了。
事实上,彼得·德鲁克在20世纪70年代就发明了“养老基金社会主义”这个短语,并在1976年出版了一本受到广泛好评的书《看不见的革命》。
[26]在“顺风顺水”的公司中,更多的高管直接向首席执行官报告,股票期权等激励措施在高管薪酬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结果令批评该公司的进步人士失望——薪酬变得更加不平等,然而,这类新公司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率。
[27] 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美国汽车行业陷入困境,催生了一场旧的效率理念的危机。
受到苏联技术官僚推崇的福特胭脂河工厂位于密歇根州迪尔伯恩市,占地2000英亩,在20世纪30年代达到顶峰时雇用了10万名工人。
历史学家戴维·
L.刘易斯(DavidL.Lewis)称之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区”,“在纯粹的机械效率方面是无与伦比的”。
虽然福特汽车总是从数千家小供应商那里购买零部件,但胭脂河工厂的理想是以直接购买铁矿石、煤炭、橡胶和其他原材料为起点,进而逐步整合这些原材料,这是受到当时的摄影师和艺术家赞美的一体化流程。
尽管通用汽车公司旗下拥有“为每个钱包和每个目的”设计的多个品牌,而且对定制持友好态度,这似乎与福特的理念相反,但它仍遵循多级官僚机构的模式,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专制的家族式的福特更甚。
通用汽车公司甚至收购了滚珠轴承制造商之类的供应商,而不是与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到20世纪70年代,外包取代了这种内包。
正如管理学领域的历史学家詹姆斯·胡普斯(James Hoopes)观察到的,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能够(在他的顾问彼得·德鲁克的鼓励下)出售许多设备,因为更高效的计算机技术降低了交易成本。
[28] 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全新模式不是来自通用电气,而是来自苹果电脑公司。
与竞争对手IBM和迅速扩张的施乐不同,苹果保持着由设计人员、营销人员和策划人员组成的较小的核心,并将其许多其他职能外包。
苹果的研究人员创造性地,甚至彻底地融合并修改了其他人的想法,但它几乎没有基础研究可与IBM的托马斯·
J.沃森研究中心或施乐传奇的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RC)的研究相提并论。
苹果的理念在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是正确的,当时施乐的个人电脑陷入停滞,苹果以消费者能接受的价格将其技术应用到麦金塔电脑上。
与此同时,高效的制造业本身陷入僵局。
从未经历过大萧条的新一代年轻工人正在反抗管理层对生产速度前所未有的追求。
“异化”从学术界渗透到流行文化中。
现在看来,美国制造业的黄金时代被压力和疲劳所玷污。
汽车行业后来出现医疗和养老金危机的一个原因是,那个时代的许多工人在合同中优先考虑的是提前退休的福利。
[29] 伴随着新的高管薪酬模式,一种高效组织的新模式出现了,即韦尔所说的“工作场所裂痕”。
组织的基本核心都是应急工作人员,临时业务往往外包,很少有工会,人员流动率很高。
在20世纪80年代及以后的新公司环境中,管理层心目中理想员工的形象发生了改变。
在弗雷德里克·温斯洛·泰勒和亨利·福特的主导下,员工会遵循由专业人士确定的固定程序,直到被提升为总监或退休。
在新的灵活的企业里,员工需要对不断变化的政策做出迅速而富有创造性的反应。
曾担任拉金公司高管的作家兼出版商阿尔伯特·哈伯德在其1899年出版的《致加西亚的信》中塑造了一个绝对服从公司的形象,这本书重印了4000万册,被分发到从纽约中央铁路公司到美国陆军等机构的员工 手里。
这本小册子无处不在,反映了1900年左右各组织的效率学说。
几乎在整整一个世纪后的1998年,一位名叫斯宾塞·约翰逊的医生出版了一本同样受到赞誉和厌恶的寓言——《谁动了我的奶酪?》。
和之前要求一心一意遵照命令相比,这次新的看重灵活性的公司准备奖励那些适应能力强的人,他们不仅能应对变化而且能预见变化。
维基百科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谁动了我的奶酪?》在出版的头10年里共售出2600万册。
批评者指责这些书都美化了服从,但两者是不同的。
灵活的下属现在被描述为服从的不是某个人——将奖励忠实和热情服务的上司,而是服从于不可避免的技术和社会变革趋势,因为上司也会被迫追随这种趋势。
实际上,到20世纪90年代,灵活的“学习型组织”——有时明显受到机体免疫系统的启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管理理论上的旧的稳定的准军事结构。
[30] 正如灵活性取代了静态的等级制度,私有制侵蚀了贵族阶级在与竞争者和政府关系中的义务。
冷战时期的企业——不仅是航空航天企业,还有像AT&T和IBM这样的科技巨头——与联邦政府关系密切。
在某些方面,AT&T和IBM是垄断企业,但它们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姿态来对自己的地位做出补偿。
正如乔恩·格特纳(JonGertner)在《思想工厂》一书中指出的,贝尔实验室以2.5万美元的相对低廉的费用向所有制造商发放了晶体管的特许经营权,而不是要求获得高额特许经营费。
拉里·埃利森的甲骨文公司2017年的市值为1770亿美元,其技术基于管理大型数据库的创新理念,这一理念是由IBM的计算机科学家埃德加·
F.科德(EdgarF.Codd)在1970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提出的,从未获得过专利。
这要付出高昂的机会成本,甲骨文公司的崛起对IBM的高管来说肯定是痛苦的,因为他们原本以为科德的突破是对他们现有产品的威胁,但他们选择了对此视而不见。
[31] 1984年AT&T和贝尔系统公司的解散表明,没有哪家公司会因为规模太大或太受尊重,而避免受到新来者的挑战。
新效率的支柱之一已经确立,“镀金时代”的发财方式是把以前独立的石油生产商、钢铁 厂和铁路公司合并成巨型组织,理由是通过规模来降低成本;现在,效率可能意味着在它们功能完全正常的情况下将它们分拆。
科研投资不高和官僚作风较弱的、较精简的新竞争对手可能会提供压低以前优质服务和硬件的价格。
以前默默无闻的中西部地区微波无线电企业家比尔·麦高恩(BillMcGowan)曾设法让美国政府支持他在1974年对AT&T提起反垄断诉讼,那次诉讼涉及贝尔系统公司大量的法律资源,这表明没有一个组织是安全的。
[32] 新公司模式的一个必然结果是全球化。
“镀金时代”的信托基金可能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并在国际市场上出售,但它们几乎完全是由本国国民和永久移民经营的。
如今,一家典型的美国大公司可能有80%的收入来自海外;如何对这一收入征税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
正如商业记者丹尼尔·格罗斯(DanielGross)指出的那样,以“二战”前的标准来看,美国跨国公司的总部也是国际化的,“忘了影响政策吧,如今许多美国一流的首席执行官甚至不能在这里投票”。
一些左翼批评者认为,新世界是一个超越阶级的世界,对彼此的忠诚超过了对同胞的忠诚。
对这些国际化精英的怨恨对于唐纳德·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中的获胜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胭脂河工厂”模式形成对比的是)许多关键行业对国际供应链的相互依赖可能会挫败经济民族主义。
[33] 到20世纪90年代,管理理论学家开始修正长期以来对公司性质的假设。
1989年,哈佛商学院经济学家迈克尔·
C.詹森(MichaelC.Jensen)预言了“上市公司的消亡”。
在此前的10年中,他和其他学者培训了一代精英顾问和高管,让他们将回报股东视为企业的唯一目的,打破了平衡投资者利益与雇员、客户和公众利益的旧观念。
詹森及其同事倡导的“代理人”理论已经赋予了企业常春藤盟校的血统,这些人可以把自己描绘成资产的高效再分配者和交易成本的敌人。
如果高管对股东收入有真正的贡献,那么高管可以获得补偿,但这一承诺却从未实现其潜力。
对于高管来说,有太多的方法可以用创 造性的会计方式来操纵业绩,甚至在糟糕的年份,他们的薪酬也可以获得提高。
正如坎贝尔定律所预言的那样,衡量利润的标准可能会被操纵,这使人们错误地认为应该衡量股东的长期利益。
到2014年,有数百家公司使用非标准的会计方法来证明高管奖金的合理性。
从长远来看,旨在减少高管与股东之间利益冲突的代理理论可能会增加这种冲突。
[34] 第二次浪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互联网繁荣。
1995年,《哈佛商业评论》里一篇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与哈佛大学约瑟夫·鲍尔(JosephL.Bower)合著的论文中首创了“颠覆性创新”一词,由此开启了思考技术变革的新阶段。
克里斯坦森的创新之处在于质疑传统的商业智慧,即倾听消费者的意见并满足他们提出的要求。
新的革命性技术最初往往不如既定的技术高效。
一开始,它吸引的不是现有用户,而是背景和需求各异的买家。
克里斯坦森和鲍尔援引了计算机磁盘驱动器行业的例子。
只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的进一步完善,计算机硬盘才能与传统产品竞争并最终主导行业,在这一行业中,老牌公司嘲笑最初降低存储容量的新型紧凑型硬盘,而正是这种硬盘最终使微型计算机和个人电脑行业成为可能。
这可能不是最好的例子,该行业最初的制造商几乎没有存活下来的,但到21世纪初,希捷(鲍尔和克里斯坦森专门提到希捷)已经成为全球硬盘驱动器行业最主要、管理最完善的公司之
一。
然而,颠覆可能是实实在在的。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最引人注目的例子就是伊士曼柯达公司未能通过推广自己实验室开发的数字技术与其主要的胶片产品竞争。
[35] 几乎在克里斯坦森的《创新者的窘境》出版的同一时间,一种新的商业模式也正在出现。
平台模式开始挑战更早的“颠覆性”企业。
在连续过程效率下,重点是物料的生产、零售分销和快速的货运。
平台创业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出现,它不是始于个人电脑,而是始于互联网和图形浏览器的普及。
平台是一种基于网络的服务,为其他服务 或交易提供框架。
长期以来,经济学家一直认为,尽管存在种种开支和官僚作风,但公司是降低交易成本的必要机构。
但是,如果技术能够匹配商品和服务的交换呢?这一想法似乎可以追溯到1996年出版的学术著作《隐形引擎:软件平台如何推动创新和产业转型》。
平台公司可以结合委托销售、广告、信息经纪等功能。
事实上它可能以职业介绍所或出租车公司的形式表现出来。
它的吸引力在于,它将信息和服务集中起来,否则这些信息和服务都需要多方搜索。
它可以将这些信息组织起来,形成消息和建议的信息流,并将用户的在线行为转化为可以出售给第三方的信息。
对投资者来说最有用的是,它甚至可以诱使用户完成几乎所有的工作。
平台公司可以自行制造、分销产品。
微软、IBM,尤其是苹果仍在销售价值数十亿美元的硬件。
但最大的增长空间出现在其他地方:从其他企业和个人那里获得收益,以提高交易效率。
[36] 推动软件革命的不仅是众所周知的处理器速度和存储量的指数式增长。
少数巧妙的想法减少了对硬件的需求,如纠错码(如果没有这一点,在线商务和通信就会崩溃)、数据压缩(使存储容量成倍增加)和公钥密码(使安全的互联网对话成为可能)之类的技术。
这些想法使硬件的效率成倍增加,出色的算法可能相当于巨大的硬件及其强大的力量。
它们基于以最快的方式解决问题的概念,这些想法可以用代码表达。
以产品代码编号系统为例,它是电子商务的基础,也是20世纪90年代亚马逊网站迅速发展的基础之
一。
它是荷兰数学家雅各布斯·韦霍夫(JacobVerhoeff)设计的,是一个在数字上添加额外数字的公式。
这个数字本身没有任何意义,你可能会在这个数字之前看到一些代码,它被称为校验数字,只允许计算机程序通过处理一个复杂的公式来验证真实数字,从而得到个位数的答案。
如果该数字与选中的数字不匹配(例如,由于客户错误地转换了两位数),就会出现错误通知。
很少有人会想到如何生成和检查输入的数字。
那是算法 之美,遗憾之处在于,它让我们把数学产生的经济力量视为理所当然。
[37] 我们都听说过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佐斯,但只有技术专家和历史学家听说过雅各布斯·韦霍夫。
然而,当贝佐斯计划实施在线零售时,图书销售是一个自然的开端,因为就韦霍夫的算法而言,与其他商品类别相比,图书拥有标准化的产品条码。
同样,直到最近,很少有人知道卡尔海因兹·勃兰登堡(KarlheinzBrandenburg)或其他德国和美国计算机科学家同行的名字。
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开发的MP3和其他音乐压缩算法,使像史蒂夫·乔布斯的iPod之类的设备能够高效地进行数字存储。
数字存储以令人震惊的方式破坏了音乐唱片产业,此前唱片产业以最低每张16.98美元的价格出售唱片,而其制造成本不到1美元。
[38] 如果将互联网上远程计算机中的海量存储与高效的算法相结合,就可以使一种被称为大数据的新的定量分析成为可能。
在幻灯片和打孔卡的时代,人们也曾感觉到被数据淹没,早期的商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分析数据的技术。
但是,存储和分析前所未有的记录的能力不仅仅只是连续过程时代统计思想的升级版本,它还使人们能够更准确地识别员工的生产率和利润以及客户的价值。
迈克尔·刘易斯在畅销书《魔球》中暗示,任何经理都可以效仿奥克兰的总经理比利·比恩(BillyBeane),像他那样用更精密的衡量方法确定员工的潜在贡献。
大数据的问题在于,竞争对手通常能够获得类似的数据集和算法,因此,竞争优势类似于会计师所说的递耗资产——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机器和其他东西会逐渐失去价值,而技术需要不断改进。
平台公司积累了如此庞大的数据,以至于与运动员不同的是,它们很难失去领先位置。
正如政治经济学家威廉·戴维斯(WilliamDavies)所说,它们也有能力在没有公众监督的情况下关注并操纵公众情绪。
19世纪的数据统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一个公共机构完成的,21世纪后的大数据统计正在成为一种专有工具。
目前由于法官会优先 考虑保密算法的结论,法院破坏了对刑事和民事司法所必需的有争议证据的竞争性辩护。
[39] 反过来,大数据的基础是用户生成的信息。
收集和录入数据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比如,在民意测验和焦点小组中就是如此。
平台效率的部分基础是鼓励客户在不付费的情况下创建数据,亚马逊的顾客评级系统是这一理念最有名的早期版本。
更深刻的革命是谷歌的网页排名算法,与早期的搜索软件不同,它依赖于无数网站所有者选择的链接之间的关系。
尤金·加菲尔德(EugeneGarfield)等信息科学家率先利用科学论文中的引文指出那些最有影响力,因而被认为质量和关注度最高的作品。
谷歌的创始人、计算机科学研究生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将这一理念扩展到了科学以外的整个互联网。
我们将在第二章中看到这方面的更多情况。
尽管存在公认的问题,而且需要不断修正算法以防受到操纵,但其搜索结果的相关性和质量依然很快超过了所有竞争对手。
这样做的一个必然结果是用户分类。
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系统化仍在试图建立一个单一的知识层次结构。
21世纪的读者,甚至一些专业图书馆员现在更关注标签,这些关键词可能是由外行读者提出的,而不是由分类专家制定的。
例如,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公共图书馆仍然使用杜威十进制系统,但在从不同范围抽取的主题“单元”中放置非小说类书籍(如技术研究书籍)。
尽管来自社交媒体的信息越来越重要,而且人们担心脸书和推特成为默认的信息来源,但在控制数据激增方面,搜索作为一种信息习惯,似乎并没有让使用量下降。
虽然谷歌没有公布每年的搜索量,但一个搜索行业网站将其声明解读为,仅2012—2016年,谷歌的搜索量就增长了50%以上,每年超过两万亿次,其中15%的关键词是之前从未搜索过的。
社交媒体可能取代一些网站,但它们似乎也产生了更多的搜索。
自2012年与人合写了一篇题为《追踪信息流向家庭》的论文 后,通信学者
W.拉塞尔·诺伊曼(
W.RussellNeuman)和他的同事就一直在给这个领域的一项旧的特性赋予新的生命力。
按照诺伊曼的说法,信息推送是指,在信息相对匮乏的时代,由有影响力的媒体进行信息传播;信息的吸引力在于用户按照偏好获得媒体产品(无论是通过搜索还是流媒体服务)。
谷歌和其他现代搜索引擎使人们能够更主动地利用信息,明确地提出要求,而不是从数量有限的媒体上获取信息。
[40] 信息拉取反过来又有助于实现平台效率的另一个决定性特征:个性化。
工业时代的大众传媒按年龄、性别、地域和估计收入等特征将广泛的人口细分为不同类别的消费者。
也有一些有特殊兴趣的群体被添加进邮寄名单,如关于仙人掌和多肉植物的书籍的狂热购买者等,尽管这些书价格昂贵,而且并不总是最新的。
网络零售商和搜索引擎公司的大数据能够以更低的成本更准确地识别消费者品味和预测其行为。
像谷歌和脸书这样的平台已经成为史上最赚钱的广告公司了。
谷歌的用户会注意到,他们获得广告服务(不仅来自他们最初寻找的公司,也来自竞争对手)的频率之高,是任何印刷媒体或广播媒体都不可能与之媲美的。
得益于这种力量,从2005年首次公开募股到2016年,谷歌的广告收入增长了10倍以上,从63.7亿美元增至793.8亿美元。
[41] 对一些公司来说,平台提供了另一个战略机遇:非物质化。
最初建立在实体产品分销基础上的技术公司,尤其是IBM和苹果,已经转向基于网络的服务。
亚马逊现在从网络服务中获得的利润比从零售业务中获得的收益要高。
[42] 在1995年之后的10年里,在经历了多次失败的开始之后,移动计算的惊人崛起使个性化服务和基于云技术的服务变得更受欢迎。
在iPhone推出后,智能手机的普及速度是信息技术史上最快的一次。
从1976年推出AppleI电脑到2003年,家庭购买个人电脑的比例增长到约 60%,这用了大约25年。
而从2007年iPhone问世到2015年,智能手机仅用了8年时间就达到了这一普及率,且这段时间大部分处于历史性衰退中。
(事实上,经济困难或许有助于推广这项技术,智能手机及其应用软件已经成为近20%的美国人,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上网的主要途径。
)因此,无论好坏,许多网络资源都针对个人的、移动的小型屏幕进行了优化,而不是主要面向办公室或家庭电脑显示器。
社会科学家很快意识到了这一趋势的潜力。
甚至在iPhone推出之前,心理学家谢里·特克尔(SherryTurkle)就称这种新的移动信息潮流为“永远的,永远在你身上”。
对平台公司和广告商来说,尽管消费者可以选择禁止泄露位置坐标,但基于实时定位来联系消费者的能力一直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43] 平台是有史以来效率最高的商业企业类型之
一,因为与其他类型的机构相比,它们需要的雇员要少得多,借助人工智能平台,甚至可以让公司结构变得更加扁平和精简。
2015年脸书的收入为280亿美元,员工只有17048人。
该公司同年的净收入为100亿美元,平均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超过58.6万美元。
传统的20世纪科技公司IBM仍然以119亿美元的净收入略高于脸书,但2017年IBM有约41.4万名员工,每名员工创造的收入约为2.87万美元。
尽管IBM的超级计算机“沃森”拥有强大的实力,但相较于向企业出售先进服务,利用算法从用户生成的数据中收集信息并对其进行分析以向消费者精准投放广告的利润要高得多。
[44] 无处不在的计算技术利用了智能手机内置的全球定位系统,创造了新的基于位置的效率类别。
作为平台公司,优步、Lyft(来福车)和其他公司并不拥有出租车、豪华轿车,也不雇用司机。
它们以超高效的中介身份出售其服务,通过跟踪位置并根据需求调整价格的算法来对客户和司机进行匹配。
实际上,优步可以向大城市的客户保证:无论天气、交通条件如何,或是否有特殊情况,他们都可以在5分钟内以一定的价格乘车。
因此,优步可能是消费者平台效率公司中最快取 得成功的一家。
研究过其运作方式的经济学家称,尽管人们对优步提出了许多反对意见,尤其是在欧洲,但它确实是高效的。
对许多城市居民来说,即使乘车费用激增,也比买车、保养和支付保险更便宜。
无论人们如何看待优步公司及其针对自己的司机和竞争对手的政策伦理,至少它在匹配乘客和司机方面非常高效。
根据经济学家史蒂文·莱维特(StevenLevitt)的一项研究(使用该公司的数据),至少在2017年年初,优步的费率(在许多地区低于成本)远远低于其客户愿意支付的价格。
莱维特的合作者斯蒂芬·
J.杜布纳(StephenJ.Dubner)认为,2015年花费40亿美元购买优步公司服务的客户本来愿意多支付110亿美元,这为社会带来70亿美元的消费盈余,这是“经济学家的梦想”。
受此类统计数据的鼓舞,私人投资者对平台经济的支持力度非常大,以至于2017年2月,优步公司的市值达到625亿美元,超过了福特汽车公司99亿美元的市值。
尽管有人指控优步公司高管的行为不端,但该公司的市值在新首席执行官于2017年8月底上任时已增至近700亿美元。
[45] 与许多较小的平台公司一样,优步的商业模式也部分基于美国劳工法和税法的含混不清。
当一个人是公司雇员时,必须遵守最低工资法,并且雇主要缴纳税款和保险费,而当他是独立承包商时,他的权利和义务则往往并不清楚。
软件可以使优步利用这种模糊性,将独立性(自由设定自己的时间并使用竞争性调度服务)与具有激励作用的竞争性调度服务相结合,该技术被称为“选择架构”。
[46] 对于优步这样的服务,最常见的反对意见是,他们利用游说力量,通过改变监管规定,获得了相对于现有服务的不公平优势。
提高价格是富人插队的另一种方式,但真正的问题可能在于,这根本不是一项根本性的创新,因此,对于创造一个更高效的社会没有多大帮助。
比如,其鼓励了不必要的出行,而不是让司机和乘客的匹配更迅速。
我们将在第四章中研究共享乘车程序的效果。
对平台效率的一个反对意见实际上是,它根本没有深远的颠覆性。
最强烈的批评不是来自硅谷的进步派批评者,而是来自最认同颠覆思想的学者克莱顿·克里斯坦森本人。
克里斯坦森和他的同事德里克·范贝弗(DerekvanBever)以及布赖恩·梅祖埃(BryanMezue)最近区分了两种颠覆性:效率创新和创造市场的创新。
后者是以更低的价格向更多人提供现有商品和服务。
优步的目标不同,它的目标是以低于或高于传统公司收费的市场结算价格持续提供交通运输服务,而且它遵循的是效率模式。
效率创新通常会减少就业。
创造市场的创新会带来新的产品类别并创造就业机会。
[47] 根据克里斯坦森、范贝弗和梅祖埃的分析,在19世纪90年代推出并一直沿用至今的自行车不仅比其中世纪的前代产品更快捷、更便宜,而且它重新定义并推广了一项新技术,将其在社会中的影响力扩大了几个量级。
早期最受欢迎的自行车是所谓的“便士-法寻”自行车,在骑手下方有一个巨大的轮子,以及一个较小的尾轮。
虽然轮子的大直径能将那个时代仍未铺柏油的道路的颠簸程度降至最低,但当轮子撞上障碍物时,它也有可能给向前倾的车手造成严重伤害。
这种自行车实际上吸引了许多年轻和富有的男性冒险者,他们是最早的骑车人。
在新的“安全”自行车中,菱形车架、充气轮胎和滚珠轴承的结合使骑行不仅更安全、更省钱、更舒适,而且实际上比以前的车型速度更快,从而受到了女性、中年人、老年人以及薪酬更高的产业工人和手工艺人的广泛青睐。
在1960年的连续过程时代的晚期,另一项创造市场的创新是施乐914型复印机。
这种复印机不仅能更好地替代湿法处理照片,而且有时能复制出比原版质量更好的复印件。
它淘汰了爱迪生时代的油印机,并就此带来了历史上资本回报率最高的公司之
一。
(1960年对施乐公司1万美元的投资到1972年增长到100万美元)。
相比之下,除了通过智能手机运营外,优步或Lyft汽车与传统的黑车没什么两样。
[48] 然而,当前的情况是,尽管更具挑战性的技术可能会使整个社会变得更高效(例如,改进蓄电池能简化可再生能源的使用过程,并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范围、提高其效率),但这些技术仍面临创新资金不足的窘境。
冷战时期推动政府在基础研究方面持续投入的军事紧迫感已经减弱,气候变化成了一个党派问题。
与电子网络和逻辑相比,物理和化学体系存在更多的挑战和限制。
制造高效的设备可能需要多年表面上是浪费的实验。
研究“二战”后美国喷气式发动机发展的历史学家菲利普·斯克兰顿(PhilipScranton)总结说,喷气式发动机的成功不是科学的项目管理,而是“非线性的、非理性的、不确定的、多边的、极富激情的技术和商业实践的结果。
不是通过计划,而是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成功的。
关键在于决心、对失败的某种漠不关心(这有助于保密)以及巨额的公共资金支出”。
这一成功不仅使民用航空运输速度实现了飞跃,而且提高了可靠性。
与依靠活塞式发动机的道路运输相比,每公里成本降低了。
在20世纪60年代的爆炸式增长之前,施乐公司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初创期。
在伊士曼柯达公司的阴影中,作为一家小型摄影用品公司,哈洛德公司(后来在突破静电复印技术应用后改名为施乐)进行了长达20年的研发,发明家切斯特·卡尔森(ChesterCarlson)最终在1938年将干式照相专利转化为商业上成功的设备。
碳粉在纸张上的高温定影可能会引起火灾,如果被复印的文件中有太多的零和字母
O,原版文件就会有着火的风险。
该设备在1960年的一场大型贸易展会上就引发了一场小火灾,不过幸好没有被顾客注意到。
即便是现在,最高效的锂离子电池也是一个潜在的危险。
2016年秋天,韩国电子巨头三星公司召回了几百万部旗舰产品Note7智能手机,原因是两家不同的供应商的电池故障引发了数百起着火事故。
高端电子产品的用户既需要紧凑的体积,也需要全天电量储备,但唯一可以满足这些要求的锂离子电池使用的是易燃电解质。
正如《经济学人》所说:“一旦出了问题,就会着火……这是它们的自然属性。
”[49] 因此,平台效率的第一个问题是,它带来的回报可能比创造市场的创新更快,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算法能够以超过物理和化学创新的速度被测试,并被应用于更大的系统。
现在,人工智能程序可以从经验中快速学习,人工智能不仅能在象棋和围棋这样的游戏中,而且在“无限制德州扑克”之类的竞赛中击败顶尖专业人士。
卡耐基梅隆大学开发的人工智能程序击败了顶级扑克玩家,获得了180万美元的奖金。
当然,软件和硬件的进步并非完全不同步,例如,锂电池需要复杂的程序控制才能安全运行,创造市场的创新的相对困难不大可能消失。
这种差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在软件领域令人眼花缭乱的改进中,2008年经济衰退后的经济复苏速度要比20世纪的几次危机缓慢。
[50] 平台效率的第二个问题发生在金融交易领域。
新效率并没有减少金融所代表的社会管理费用,反而使管理费用进一步增加。
20世纪90年代,《未来之路》[比尔·盖茨、内森·米赫尔沃尔德(NathanMyhrvold)和彼得·林纳森(PeterRinearson)于1995年出版]“硅谷宣言”的读者认为,他们期待着“无摩擦的商业”。
事实上,对用户来说,亚马逊和其他领先的零售网站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单纯的交易功能。
亚马逊的Echo语音识别智能音箱的用户可以用该公司的Alexa系统下订单,而无须点击屏幕。
微软、谷歌和苹果也推出了类似的电子语音助手。
而那些高效的、愿意触碰某样东西的人,可以选择亚马逊公司支持Wi-Fi的设备,这种设备可以连接到家用电器上,用于即时订购相关品牌的易耗消费品,如洗衣机专用的洗涤剂等。
微处理器巨头英特尔公司的研究人员在2009年预测,在未来,消费者也许会通过植入大脑的传感器接收到的想法下订单。
虽然这家芯片制造商似乎在经济衰退期让这个项目悄然延后了,但它不太可能消失。
[51] 不过,摩擦还是有办法避免的,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改进效率。
亚马逊平台上有200万第三方商家,这些商家的商品与亚马逊自营的商品一起被展示。
他们的一些订单是通过亚马逊的仓库配送完成的,其他订单则直接从卖家那里发货。
供应商可能对相同的商品有不同的保 修政策,消费者评级和收货时间也不同。
此外,他们使用专门开发的软件来调整自己的价格,使之与亚马逊和非亚马逊供应商的价格相适应。
在“动态定价”下,报价可以在不通知卖家的情况下自动更改。
亚马逊使用一种复杂且秘密的算法在“购买框”中选择默认供应商,通过链接将商品添加到消费者的购物车中。
这种算法不仅列出了获得订单的供应商之外的其他供应商,点击其他链接的客户还可以看到其他厂商。
亚马逊的供应商使用特殊的软件来计算他们的价格,他们可能会设置一个更高或更低的价格。
到目前为止,与通常最低价格、订购的便利性——亚马逊的界面设计得非常好——以及优享计划的交付速度相比,这些变化给用户带来的选择烦恼还不算大。
来自亚马逊的竞争力有助于降低通胀,事实上亚马逊的销售利润微乎其微,(正如我们所提到的)它的真正利润来自它为其他公司和政府提供的网络服务。
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是,重大收购是否可能将亚马逊变成一家反竞争而非支持竞争的公司。
[52] 只有当消费者愿意接受亚马逊的算法时,他们才能享受到该平台提供的充分的效率,而亚马逊的算法也正在与满意度各异的各种供应商的算法进行竞争。
寻找最低价格的消费者可能不得不花更多的时间来考虑完整的清单并衡量供应商的声誉。
令人印象深刻的网站允许购买者查看亚马逊的历史价格,并在价格跌至预设水平时设置电子邮件通知,但这往往需要花更多时间来决定设置什么价格。
它主要适用于昂贵的非必需产品,特别是消费类电子产品,它们会受到制造商季节性价格下调的影响。
不管有没有此类价格追踪工具,最初作为一个简单而高效的购物系统的平台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复杂的系统,在这个系统中,最佳报价可能会突然出现或消失,这取决于竞争对手的算法和平台供应商对自己购物模式的监控。
同样,在线旅游服务最初似乎通过比较最佳的酒店价格来简化决策,已有之类的聚合平台出现,该聚合平台声称可以从其他 预订网站上找到最优惠的报价。
旅行预订平台的复杂性产生了意想不到的作用,曾经受到网络预订致命威胁的旅行社出现了复兴。
[53] 在网络商品和服务网站以及社交媒体上对顾客评级进行评估也变得更加复杂。
据《纽约时报》报道,将亚马逊用户评论与专业消费者组织报告以及转售价值进行比较的市场研究人员发现,用户评论对产品质量的评价并不可靠。
2012年,一位学术数据挖掘学者估计,网上的评论中有1/3是伪造的。
一位出版社的工作人员靠在亚马逊上为自己出版的作品撰写评论,每个月能赚2.8万美元。
我想在网上找一家附近的电脑维修店,但注意到一家被打了五星评论的维修店,其客户评论大同小异,这让人对客户的身份产生了疑问。
比如,偶尔出现的温和批评会让客户评论看起来更真实,而且评论者也没有对任何其他类型的机构发表过意见。
相反,对其他商品和服务的评论,尤其是对公寓出租方的评论,似乎都在致力于表达消费者的不满。
更复杂的是,一些真正的在线书评家似乎对几乎所有事情都表现出真诚的积极态度。
但核心问题是,评论受到了追随者效应和评级泡沫等社会倾向的影响。
在产生真正积极的影响方面,虚假评论的影响力可能令人吃惊。
[54] 不管评论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都显示了坎贝尔定律的作用。
这些评论的影响来源于发表评论者的行为,因此,有必要消除他们的偏见。
社会学家和网站管理员创造了将真实评论与虚假评论区分开来的算法,但这些努力遇到了一个由来已久的问题。
正如在文字和图片鉴别中一样,用于检测欺诈的工具可以被用来更巧妙地造假。
最后,并不是说用户评论毫无用处,而是说用户评论的时间效率要比刚出现时低得多。
经常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来阅读它们,并找到每种产品或服务的优劣之处。
专业的书籍和产品测评者的确限制了消费者的信息获取,但如果你相信他们的判断,那么追随他们比试图去猜测大众的智慧更有效。
[55] 目前还不清楚网络零售的平台经济是否比传统商店更有效率。
有一种看似有道理的观点认为,与传统的实体购物相比,网购通过减少汽车出行来降低温室气体排放。
理论上,在网上订购并送货上门的包裹会比多次外出购物产生的碳排放量更低。
至少在2012年,亚马逊在其网站上的“网购效率”频道中声称自己提供“更绿色的购物体验”。
实际上,算法效率的结果一旦开始与人类行为相互作用,就几乎无法对其进行衡量。
努力减少碳足迹的确可以为人们节省出行里程和时间。
但是,来自特拉华州的一项研究表明,其他人可能通过其他类型的活动,如娱乐来花掉自己节省的时间和里程。
即时满足的效率还意味着更多商品被分装在不同的包装中运送给消费者,当这些商品被运送给零售商时,它们可能是被捆绑在一起的单独的盒装形式。
正如电子库存控制使精益制造成为可能一样,一些消费者在智能手机应用软件的帮助下进行淘货,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一位傲慢的作家在文章中宣称:“未雨绸缪已经过时。
”亚马逊大力推销收取年费的优享计划,许多产品可以在两天里免费送达,这鼓励了冲动购物。
一种形式的高效——快速交付——与另一种形式的高效相抵触。
在西尔斯百货公司提供商品目录的时代,消费者可以明显地注意到联合发货过程中的节约。
虽然纸板行业一直是回收利用的领头羊,但由于网络购物的便利性,包装盒的销量一直在迅速增长,回收利用在运输方面也有其自身的环境成本。
始于20世纪90年代的环保概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