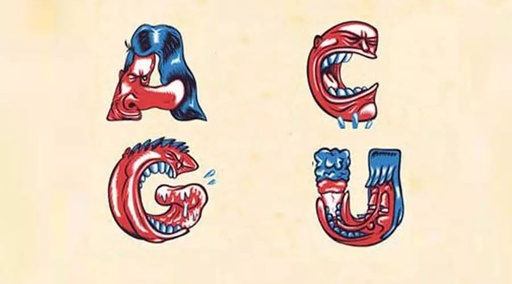边接受脑瘤摘除手术
■巴西33岁的银行职员安东尼·库尔坎普·迪亚斯近日在圣卡塔琳娜州的一所医院
新接受大脑肿瘤切除手术。
在闻手术过程中,神志清醒的他 弹起了吉他,以方便医生观 关注察其大脑情况。
摄影师与女友环游世界网络热传系列照 俄罗斯摄影师穆拉德·奥斯曼因拍摄一系列女友牵手带其环游世界的照片而在Instagram上走红。
图为其女友身着婚纱引领他向前走的系列照片之
一。
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第985期热线电话:(0531)85193307Email:gaf@
9 30岁美国女探险家竟敢亲吻眼镜蛇 美国夏威夷的女探险家艾莉森,30岁就已经到过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艾莉森的父母都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着周游世界。
图为在一次探险中当地居民要求艾莉森爬上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去亲吻眼镜蛇。
澳洲2米高袋鼠每日训练爪碎铁桶 澳大利亚一只名叫罗格的袋鼠,身高2米,它不仅体型巨大,还能用爪子粉碎铁桶保护自己的领地。
它的主人克里斯·博格拉表示,罗杰最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和主人一起进行拳击锻炼,其中就包括踢碎铁桶。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35年前,被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典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
直到今年,我国才有了中译本。
6月6日下午,在北京雨枫书馆,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从这部译著谈起女性意识的话题,现场气氛热烈。
戴锦华:“女性主义”是我个人的乌托邦 参加“《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性别意识”的沙龙,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自己忽略了性别,算是“误入”,而且还坐在第一排,太显眼。
我们被女性包围,略感尴尬。
下午3点,身高一米七五的戴锦华落座,一开场就笑言:“这一次是我前所未有的遇到这么热烈的场面。
天这么热,又是周末,而且还颇有一些男性朋友。
通常只要是女性主义的名号一打出来,基本上都是女性的面孔。
比如我们这次好像专门要请一位男性(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柏)跟我对话,就是为了平衡一下这种性别状态。
” 这本书终于来到 我们中间了,并不晚 被誉为“女王朔”的著名作家徐坤写过戴锦华印象记,其中谈到,在某座谈会上戴锦华“哐哐哐哐地开始发言,说话的时候手指不停地探进烟盒里捻起一根根烟卷儿续在嘴上,仿佛只是一种下意识动作,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看着像是炉膛里在燃着红通通的火,不及时往里续柴火就要灭了。
接着那话语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外迸出火星子,溅在亚麻布料上,溅在发梢和指尖上,看着可真是夺目耀眼。
” 这次沙龙,两个多小时,没见戴锦华抽烟,但她的发言却是“哐哐哐哐”,新颖,新奇,畅快。
戴锦华是第三次读《阁楼上的疯女人》,前两次读的是英文版。
“这次终于读到了中文版。
35年前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很快就在国内被提及,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完整的翻译本。
很多人根据书中涉及到的女性主义,望文生义地产生出一系列关于这本书的错误的想象性引证,这次拿到中文版的时候,有一点惊讶,它是放到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的序列当中出版的,前面有海内外声名赫赫的李欧梵教授和刘象愚教授的总序,第一次感受到女性主义的文学已经具有如此庄严、如此重要的位置。
文景(世纪出版集团)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 戴锦华认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这本书是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
“大家仔细想想,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才有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作者还是非常没有资历的两个女老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
而今天这部著作已成为经典,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 跟随戴锦华的语速,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往前推进:“其实这本著作当中提到的所有女诗人、女作家,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玛丽·雪莱等等,原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
《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两位女作者只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经由她们的阐释,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显出来了,而她们的研究方法不是针对这些女作家写的女性文学,而是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作家共同的一些叙述特征,一些情感特征,并在分析当中发现历史的、社会的、压迫性的和反抗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这本书终于来到我们中间了,但是并不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这本原著,通过他们的理论文本去读,读她们的文字,读她们的表述,读她们文字和表述背后的历史与社会。
” 透过35年前诞生的这本书,戴锦华读出了35年对女性的影响:“这35年来我们究竟走过了什么历程?对于女性来说,历史是不是在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当中,是不是今天远比当年进步了?我们人人都能认识到写作不仅仅是执笔,作家手中的笔不是所谓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说,女性写作是一个孕育和生产的过程,因为女性有子宫。
这些说法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性,而变成一般意义的修辞。
但当这种修辞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性别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女性写作,我想这本书会开启一个性别思考,包括我们以更加自觉的中国主体位置与西方对话。
” □本报记者逄春阶卢昱 传递出了极端大胆的 冒犯和梦想 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大家普遍认为《简·爱》就是哥特罗曼史。
戴锦华说:“今天有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嘛,还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
”(玛丽苏,MarySue:原指某些人的自恋心态,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一点委屈也受不得,挑剔且难以相处。
———记者注) 戴锦华几乎是一口气说了下去:“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者那样低的评价,它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被从女性、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中所可能产生的表达方式来解读。
我经常碰到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说,《阁楼上的疯女人》表述的是,《简·爱》中柏莎和简·爱才是姐妹,柏莎应该跟简·爱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桑菲尔德庄园,永远把罗切斯特抛在身后。
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作为一种选择也不是问题,看上去柏莎又高大又美丽,好像她俩也挺般配的,但是这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的叙述,也不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女儿,在那种衣食不周的荒原里可能产生的想象。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
《简·爱》的作者是19世纪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嫁给妹妹的未婚夫,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拮据,非常悲惨。
” 戴锦华说:“《简·爱》的作者写的小说毫无疑问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这个梦中她传递出了一个至少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阁楼上的疯女人———柏莎,不仅是简·爱的重影,而且罗切斯特和简·爱也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这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和智慧,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那个男人被迫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
” “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
” 戴锦华攥着手说道,“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他们同样是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
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绝望和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我们今天在结构的意义上去把握作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是历史和文化的潜意识。
这两位作者在非常精 致的文学分析当中,在非常好的文学训练、文学修养、艺术体认当中去把握到这一点。
不是想当然说柏莎是简·爱的重影,而是从对柏莎的出现,她是怎样和简·爱处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单恋的情绪相互呼应的分析中得来的。
” “你们男人”,“我们女人” “你们男人”“我们女人”,这样的表述听上去很别扭,但《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如此表述的。
“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因为实在太久了,当男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女人,但当女人说‘我们’的时候是当然地包括男人,而且当然包括了对男人的认同。
” 戴锦华说:“我们是女人,是社会规定我们成为女人。
西蒙娜·波伏娃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太老了,但也经常被人们忘记:‘女人不是生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也许有人会问,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
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
对我来说,波伏娃的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
这本书也把这句话用到了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反抗、女性创作当中。
”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其中重要的因素之
一,就是夏洛蒂·勃朗特赋予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
“她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对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昂扬和进步。
但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拓殖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
在一切被压迫的群体中都有主体性的问题。
但是我一向认为主体性的讨论有意思、有效,但也有限,当女人缠足的时候,当不允许女人进入社会舞台的时候,女性尽管她是家庭的实际执掌者,尽管她是教育者,尽管她可能是真正的家长,但是她在社会的位置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是被压迫的。
我一直开玩笑说,很少的天才才有先见之明,后见之明是经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简·奥斯汀、看勃朗特姐妹、看艾米丽·迪金森,当我们看她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 被忽略的“阶级的维度” 戴锦华谈到,女性意识似乎越来越被有教养的人认同,但她们好像越来越意识不到另外的维度,比如阶级的维度。
“一个残疾的底层的打工妹,和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们俩性别经验的共同到底重要不重要?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议题。
” 戴锦华说,“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山东一家韩资耐克加工厂,厂主是一位韩国女性,她发现有工人下班时把做耐克鞋的边角料带出去,她让全厂工人跪下,逼那个抓到的小偷吞下去那个边角料,结果当时的报刊刊登了那个新闻,包括那个报刊本身的报道语调引发的就是‘韩国女人该死’,‘我中华民族男儿膝下有黄金’。
而背后的耐克,跨国企业,世界加工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风波和剥削,完全没有提及。
在这个场景当中,男权变成了一种民族正义的力量,舆论强调‘我们男人的尊严’,而丝毫没有说人的尊严和劳动者的尊严。
” 戴锦华还讲到一件案子,一个遭到强暴的女孩子,反抗强暴者,造成强暴者的阴茎折断流血而死,最后这个女孩子以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
“我想问,她怎么才能不犯下过失呢?如果她不犯下过失的话,会不会一个古老的表述就将出现:所有被强暴的女人都是她们自招的,男人怎么会去对一个没有性暗示的女人产生荷尔蒙呢?这个消息,让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想嘶喊的感觉。
” 扑面而来的社会现象,让戴锦华无法言说。
比如,当用小额贷款能够让农村妇女加入到生产过程当中的时候,两个方面的问题出来了,一边是女人由于有了经济独立,在农村当中的家庭位置开始被改善;但另外一边,她们的传统角色一点没变,她们的家务一点没有减轻,结果是,她们变成早上四点半就得起床,忙活整整一天。
“从更宽泛的角度上看,这个路径极端有效地把全球第三世界女性的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规模生产当中来了。
我们怎么去重新界定性别的批判立场?”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戴锦华坦言:“女性主义对于我就是我个人的乌托邦,就是尊重个体差异的,赋予每个人抉择的可能,然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主义。
我觉得很少有男性会意识到,或者会真的去反抗他们的强势位置,同时伴随着压抑,就是男人必须是成功者,要顶天立地,要给妻儿提供怎样的物质条件。
其实这种压迫对女性来说,某些时候有足够幸运可以逃避,但男人基本上无路可逃,除非你是富二代。
” 也有这样的情况,丈夫不成功,妻子骂他,这是不是女性主义侵害了男性?戴锦华说:“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的辱骂,绝不是女性主义,而刚好相反,是整个主流重建的男权的价值评判和系统。
因为一个真的女性主义者,她应该认为从来都是我们一起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家庭。
” 几年前一个相亲节目中,有个女孩“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戴锦华对此评价道:“她作出这样的选择,前提是已经知道她坐在宝马后面会哭。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选择,但我们经常忘记哪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你做一个全职太太你要付出代价,你使用保姆也要付出代价。
你有没有记得保姆是你的姐妹?在女性主义上跟你是完全一样的人,你是剥削她的劳动来解放你自己。
虽然是以付费的方式,但未必是公平付费。
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忘记的一件事,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有代价的。
我们有没有反过头来问我们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不是肩负着责任。
当社会开始变好或者变坏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今天我们再理解这句话可能有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也将成为每个人的问题。
所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个人的就是实践性的,政治不是宫斗。
所以甄嬛类的故事可以看,但是要保持批判,保持冷静,那个故事所表达的谋反,我想应该有警惕。
” 她们自己的 性别开窍时刻 《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很坦诚地提到了她们的性别开窍时刻。
在沙龙现场,有三位女性也很真诚地谈到这个时刻。
面对性别开窍时刻的问题,戴锦华是这样回答的:“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
好像我很早就有这个性别意识,大概七八岁时。
我十三岁时就已经这么高了,我每天要听大人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怎么嫁’,我是有‘原罪’的人。
” 待听众哄堂大笑之后,戴锦华继续说道:“那个时候女孩子们跟现在不一样,没有同性恋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
那个时候同性恋就像‘流氓’‘神经病’一样,是个非常难听,脏得不能再脏的一个词。
我就遭到这样的质疑,原因是因为我高,女孩子有的时候必须像借助男生的体力一样借助我。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是个好女人。
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人们的呵护,但我得不到。
当我第一次读到《性别的奥秘》,读到《第二性》的时候,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别人表述我的经验,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请我,这是我完全个人的生命经验,不是一个开窍时刻,因为我被踢出去,成为人家的忧虑。
到我三十岁,大家又开始说高是美。
当年我也非常瘦,那就更糟糕。
等到我已经不具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反而都成了优点,但在我那个时候都是生理缺陷,所以我没有那个开窍的时刻。
” 谈到女性主义,不能不谈到独立性。
戴锦华说,《简·爱》最后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以真正的独立面对罗切斯特的时候,不光因为罗切斯特瞎了残了,还因为她有了遗产,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
我们经常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人的一间屋”,但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道,“一间屋”的必要的条件是有“自己的支票本”,也就是经济独立。
鲁迅先生说,首先要有独立,“第
一,便是生活。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否则的话,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谈到鲁迅,记者问戴老师,怎样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待鲁迅的婚姻问题,特别是与妻子朱安关系的处理。
戴锦华说:“他跟朱安是包办婚姻,而且他有个非常强大的母亲,所以他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但朱安的一生,就非常悲惨,而且朱安完全从所有叙述中消失了。
我们必须体会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管它叫‘未死方生’,你看那个旧的社会,旧的自我还没有死,而新的自我已经长出芽儿来。
鲁迅只能委曲求全。
反过来说,鲁迅比胡适要好啊,胡适的母亲一拿菜刀,他就缩回去了,他的太太一发脾气,他就没辙了,一辈子和包办的妻子生活。
所以,鲁迅在这点上,还算是勇敢的吧。
但这个勇敢是以牺牲朱安为代价的,以牺牲最弱者为代价的。
” 我们记得,好多年前,女作家徐坤说过,如果没有许广平,鲁迅还会彷徨很多年,鲁迅后半生都是许广平照亮的。
一开始来参加沙龙,感觉是小众之中的小众,当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来,觉得小众不小。
当听完戴锦华的言说,感觉女性意识问题,不是小众话题,而是大众话题;不是轻松话题,而是沉重话题。
■责任编辑郭爱凤
在闻手术过程中,神志清醒的他 弹起了吉他,以方便医生观 关注察其大脑情况。
摄影师与女友环游世界网络热传系列照 俄罗斯摄影师穆拉德·奥斯曼因拍摄一系列女友牵手带其环游世界的照片而在Instagram上走红。
图为其女友身着婚纱引领他向前走的系列照片之
一。
2015年6月12日星期五第985期热线电话:(0531)85193307Email:gaf@
9 30岁美国女探险家竟敢亲吻眼镜蛇 美国夏威夷的女探险家艾莉森,30岁就已经到过全球40多个国家和地区。
艾莉森的父母都是野生动物摄影师,她两个月大的时候,就被带着周游世界。
图为在一次探险中当地居民要求艾莉森爬上亚利桑那州大峡谷去亲吻眼镜蛇。
澳洲2米高袋鼠每日训练爪碎铁桶 澳大利亚一只名叫罗格的袋鼠,身高2米,它不仅体型巨大,还能用爪子粉碎铁桶保护自己的领地。
它的主人克里斯·博格拉表示,罗杰最喜欢的一项娱乐活动就是和主人一起进行拳击锻炼,其中就包括踢碎铁桶。
■周末人物·中国新闻名专栏 35年前,被誉为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经典的《阁楼上的疯女人》问世。
直到今年,我国才有了中译本。
6月6日下午,在北京雨枫书馆,女性主义研究专家、北京大学教授戴锦华从这部译著谈起女性意识的话题,现场气氛热烈。
戴锦华:“女性主义”是我个人的乌托邦 参加“《阁楼上的疯女人》与性别意识”的沙龙,说实在的,我们没有做好必要的心理准备,自己忽略了性别,算是“误入”,而且还坐在第一排,太显眼。
我们被女性包围,略感尴尬。
下午3点,身高一米七五的戴锦华落座,一开场就笑言:“这一次是我前所未有的遇到这么热烈的场面。
天这么热,又是周末,而且还颇有一些男性朋友。
通常只要是女性主义的名号一打出来,基本上都是女性的面孔。
比如我们这次好像专门要请一位男性(中国人民大学副教授孙柏)跟我对话,就是为了平衡一下这种性别状态。
” 这本书终于来到 我们中间了,并不晚 被誉为“女王朔”的著名作家徐坤写过戴锦华印象记,其中谈到,在某座谈会上戴锦华“哐哐哐哐地开始发言,说话的时候手指不停地探进烟盒里捻起一根根烟卷儿续在嘴上,仿佛只是一种下意识动作,一根接一根,一根接一根,看着像是炉膛里在燃着红通通的火,不及时往里续柴火就要灭了。
接着那话语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外迸出火星子,溅在亚麻布料上,溅在发梢和指尖上,看着可真是夺目耀眼。
” 这次沙龙,两个多小时,没见戴锦华抽烟,但她的发言却是“哐哐哐哐”,新颖,新奇,畅快。
戴锦华是第三次读《阁楼上的疯女人》,前两次读的是英文版。
“这次终于读到了中文版。
35年前这本书在美国出版,很快就在国内被提及,好像大家都知道,但是这本书,一直没有完整的翻译本。
很多人根据书中涉及到的女性主义,望文生义地产生出一系列关于这本书的错误的想象性引证,这次拿到中文版的时候,有一点惊讶,它是放到西方现代批评经典译丛的序列当中出版的,前面有海内外声名赫赫的李欧梵教授和刘象愚教授的总序,第一次感受到女性主义的文学已经具有如此庄严、如此重要的位置。
文景(世纪出版集团)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
” 戴锦华认为,《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是女性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作,这本书是以19世纪作为断代的女性主义文学史的第一部巨著。
“大家仔细想想,35年前才有了关于女性文学的讨论,才有了关于女性主义的系统性的理论著作。
作者还是非常没有资历的两个女老师,桑德拉·吉尔伯特和苏珊·古芭。
而今天这部著作已成为经典,这本身是一个历史的痕迹。
” 跟随戴锦华的语速,关于这本书的解读往前推进:“其实这本著作当中提到的所有女诗人、女作家,勃朗特姐妹、简·奥斯汀、玛丽·雪莱等等,原本就是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
《阁楼上的疯女人》这两位女作者只是对英国文学史上的经典作家作了一个完全不同的阐释,经由她们的阐释,这些女作家的女性身份凸显出来了,而她们的研究方法不是针对这些女作家写的女性文学,而是在女作家的作品当中寻找到了一种与男性作家不同的、女性作家共同的一些叙述特征,一些情感特征,并在分析当中发现历史的、社会的、压迫性的和反抗性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
现在这本书终于来到我们中间了,但是并不晚,因为我们从来没有机会通过这本原著,通过他们的理论文本去读,读她们的文字,读她们的表述,读她们文字和表述背后的历史与社会。
” 透过35年前诞生的这本书,戴锦华读出了35年对女性的影响:“这35年来我们究竟走过了什么历程?对于女性来说,历史是不是在一个线性的进步过程当中,是不是今天远比当年进步了?我们人人都能认识到写作不仅仅是执笔,作家手中的笔不是所谓的男性生殖器的象征,或者说,女性写作是一个孕育和生产的过程,因为女性有子宫。
这些说法今天已经没有任何刺激性,而变成一般意义的修辞。
但当这种修辞已经形成的时候,我们真实的生存状况是什么?性别的文化状态是什么?我们今天怎么去理解女性写作,我想这本书会开启一个性别思考,包括我们以更加自觉的中国主体位置与西方对话。
” □本报记者逄春阶卢昱 传递出了极端大胆的 冒犯和梦想 35年前,还没有人去讨论《简·爱》是不是一部女性主义著作,大家普遍认为《简·爱》就是哥特罗曼史。
戴锦华说:“今天有更刻薄的评价,说那不就是‘玛丽苏’的开山之作嘛,还有人说那不就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嘛。
”(玛丽苏,MarySue:原指某些人的自恋心态,自我感觉良好,而且一点委屈也受不得,挑剔且难以相处。
———记者注) 戴锦华几乎是一口气说了下去:“尽管有这样高的评价或者那样低的评价,它在那之前完全没有被从女性、女性的生命体验、女性在特定的历史结构中所可能产生的表达方式来解读。
我经常碰到年轻的女性主义者说,《阁楼上的疯女人》表述的是,《简·爱》中柏莎和简·爱才是姐妹,柏莎应该跟简·爱两个人手拉手走出桑菲尔德庄园,永远把罗切斯特抛在身后。
这种观点我不反对,作为一种选择也不是问题,看上去柏莎又高大又美丽,好像她俩也挺般配的,但是这不是《阁楼上的疯女人》里的叙述,也不是《简·爱》的作者夏洛蒂·勃朗特,作为一个贫穷的牧师的女儿,在那种衣食不周的荒原里可能产生的想象。
我们每个人都是历史的儿女,我们每个人都是现实的囚徒,我们每个人都不可能有无尽的自由去飞翔。
《简·爱》的作者是19世纪的一个穷牧师的女儿,一辈子没有得到过真实的爱情,最后嫁给妹妹的未婚夫,死于难产,生命非常短暂、拮据,非常悲惨。
” 戴锦华说:“《简·爱》的作者写的小说毫无疑问是女性的白日梦,但是这个梦中她传递出了一个至少在《阁楼上的疯女人》这本书的两位作者看来,完全不同的追求、反抗、极端大胆的冒犯和梦想。
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阁楼上的疯女人———柏莎,不仅是简·爱的重影,而且罗切斯特和简·爱也互为镜像,这才是冒犯。
这是一个平等的,由于女性的挑战和智慧,由于她不妥协的战斗,赢得了一个阶级上比她高得多的男人的尊重,那个男人被迫把她当作一个平等的人。
” “在这个相互的平等当中,他们共同向我们传递出了一种19世纪英国资本主义及其资产阶级的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
” 戴锦华攥着手说道,“他们是精神上的兄妹,是精神上的共同者,但他们同样是在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性别极端歧视的结构之下的一对男女,而且是一对主仆。
在这样的过程中,一个反抗的独立的智慧的女性,她怎么去表达她的愤怒、绝望和疯狂?在故事中她成了另外一个角色,就是阁楼上的疯女人。
我们今天在结构的意义上去把握作者的潜意识,这个潜意识并不是精神分析的潜意识。
这个潜意识是历史和文化的潜意识。
这两位作者在非常精 致的文学分析当中,在非常好的文学训练、文学修养、艺术体认当中去把握到这一点。
不是想当然说柏莎是简·爱的重影,而是从对柏莎的出现,她是怎样和简·爱处在一个几乎无望的、单恋的情绪相互呼应的分析中得来的。
” “你们男人”,“我们女人” “你们男人”“我们女人”,这样的表述听上去很别扭,但《阁楼上的疯女人》是如此表述的。
“这是一种反抗的姿态,因为实在太久了,当男人说‘我们’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不是包括女人,但当女人说‘我们’的时候是当然地包括男人,而且当然包括了对男人的认同。
” 戴锦华说:“我们是女人,是社会规定我们成为女人。
西蒙娜·波伏娃的这句话今天听起来已经太老了,但也经常被人们忘记:‘女人不是生而成的,女人是被社会建构而成的’。
也许有人会问,那我们在生理上是女人是怎么回事?我一直在说,只有在那一天我们才能回答生理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两性差异,哪一天?就是当文化的、压迫性的、歧视性的表述被破除的时候。
我经常说某一个女人和某一个女人之间的差距,可能并不比某一个女人跟某一个男人之间的差距更小。
对我来说,波伏娃的这句话是石破天惊的。
这本书也把这句话用到了女性书写、女性意识、女性反抗、女性创作当中。
” 《阁楼上的疯女人》和今天的《何以笙箫默》是截然不同的,其中重要的因素之
一,就是夏洛蒂·勃朗特赋予简·爱强大的主体意识。
“她的主体意识并不以获得男人的爱和进入婚姻来作为自我满足的结局,而这对女性主义来说是如此昂扬和进步。
但大家一定别忘记,这是当时向全世界拓殖的大英帝国的开拓精神在一个女性身上的体现。
在一切被压迫的群体中都有主体性的问题。
但是我一向认为主体性的讨论有意思、有效,但也有限,当女人缠足的时候,当不允许女人进入社会舞台的时候,女性尽管她是家庭的实际执掌者,尽管她是教育者,尽管她可能是真正的家长,但是她在社会的位置仍然是低下的,仍然是被压迫的。
我一直开玩笑说,很少的天才才有先见之明,后见之明是经过后天的学习获得的。
我们可以回过头去看简·奥斯汀、看勃朗特姐妹、看艾米丽·迪金森,当我们看她们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了历史的镜子来问我们自己,问我们今天经历了这么多的改变之后,我们的可能性在哪里,我们重新面对的问题是什么。
” 被忽略的“阶级的维度” 戴锦华谈到,女性意识似乎越来越被有教养的人认同,但她们好像越来越意识不到另外的维度,比如阶级的维度。
“一个残疾的底层的打工妹,和我作为北京大学的教授,我们俩性别经验的共同到底重要不重要?这是一个特别重大的议题。
” 戴锦华说,“不知大家是否记得,上世纪90年代后期,山东一家韩资耐克加工厂,厂主是一位韩国女性,她发现有工人下班时把做耐克鞋的边角料带出去,她让全厂工人跪下,逼那个抓到的小偷吞下去那个边角料,结果当时的报刊刊登了那个新闻,包括那个报刊本身的报道语调引发的就是‘韩国女人该死’,‘我中华民族男儿膝下有黄金’。
而背后的耐克,跨国企业,世界加工厂所造成的新的世界风波和剥削,完全没有提及。
在这个场景当中,男权变成了一种民族正义的力量,舆论强调‘我们男人的尊严’,而丝毫没有说人的尊严和劳动者的尊严。
” 戴锦华还讲到一件案子,一个遭到强暴的女孩子,反抗强暴者,造成强暴者的阴茎折断流血而死,最后这个女孩子以过失杀人罪被判了三年。
“我想问,她怎么才能不犯下过失呢?如果她不犯下过失的话,会不会一个古老的表述就将出现:所有被强暴的女人都是她们自招的,男人怎么会去对一个没有性暗示的女人产生荷尔蒙呢?这个消息,让我有一种欲哭无泪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想嘶喊的感觉。
” 扑面而来的社会现象,让戴锦华无法言说。
比如,当用小额贷款能够让农村妇女加入到生产过程当中的时候,两个方面的问题出来了,一边是女人由于有了经济独立,在农村当中的家庭位置开始被改善;但另外一边,她们的传统角色一点没变,她们的家务一点没有减轻,结果是,她们变成早上四点半就得起床,忙活整整一天。
“从更宽泛的角度上看,这个路径极端有效地把全球第三世界女性的剩余劳动力组织到资本主义的全球性的规模生产当中来了。
我们怎么去重新界定性别的批判立场?” “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戴锦华坦言:“女性主义对于我就是我个人的乌托邦,就是尊重个体差异的,赋予每个人抉择的可能,然后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的主义。
我觉得很少有男性会意识到,或者会真的去反抗他们的强势位置,同时伴随着压抑,就是男人必须是成功者,要顶天立地,要给妻儿提供怎样的物质条件。
其实这种压迫对女性来说,某些时候有足够幸运可以逃避,但男人基本上无路可逃,除非你是富二代。
” 也有这样的情况,丈夫不成功,妻子骂他,这是不是女性主义侵害了男性?戴锦华说:“是什么东西支撑着她的辱骂,绝不是女性主义,而刚好相反,是整个主流重建的男权的价值评判和系统。
因为一个真的女性主义者,她应该认为从来都是我们一起去改变我们的生活、家庭。
” 几年前一个相亲节目中,有个女孩“宁可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坐在自行车后面笑”,戴锦华对此评价道:“她作出这样的选择,前提是已经知道她坐在宝马后面会哭。
我们今天有很多的选择,但我们经常忘记哪一种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你做一个全职太太你要付出代价,你使用保姆也要付出代价。
你有没有记得保姆是你的姐妹?在女性主义上跟你是完全一样的人,你是剥削她的劳动来解放你自己。
虽然是以付费的方式,但未必是公平付费。
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忘记的一件事,任何一种选择都是有代价的。
我们有没有反过头来问我们每一个社会中的个人,对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不是肩负着责任。
当社会开始变好或者变坏的时候,是不是跟我们每个人都有关。
《阁楼上的疯女人》在写作的时候有一个特别响亮的口号,个人的就是政治的。
今天我们再理解这句话可能有不一样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也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个社会的问题也将成为每个人的问题。
所以,个人的就是政治的,个人的就是实践性的,政治不是宫斗。
所以甄嬛类的故事可以看,但是要保持批判,保持冷静,那个故事所表达的谋反,我想应该有警惕。
” 她们自己的 性别开窍时刻 《阁楼上的疯女人》的两位作者很坦诚地提到了她们的性别开窍时刻。
在沙龙现场,有三位女性也很真诚地谈到这个时刻。
面对性别开窍时刻的问题,戴锦华是这样回答的:“每次有人问我为什么变成了一个女性主义者,我都是特别朴素地回答,就是因为我长太高了。
好像我很早就有这个性别意识,大概七八岁时。
我十三岁时就已经这么高了,我每天要听大人在背后窃窃私语说‘怎么嫁’,我是有‘原罪’的人。
” 待听众哄堂大笑之后,戴锦华继续说道:“那个时候女孩子们跟现在不一样,没有同性恋文化,男孩子跟男孩子、女孩子跟女孩子都是勾肩搭背的。
那个时候同性恋就像‘流氓’‘神经病’一样,是个非常难听,脏得不能再脏的一个词。
我就遭到这样的质疑,原因是因为我高,女孩子有的时候必须像借助男生的体力一样借助我。
所以我很小就非常痛苦和困惑,总是在心里对自己说我是女人,我是个好女人。
我像所有的女孩子一样希望得到人们的赞许、人们的呵护,但我得不到。
当我第一次读到《性别的奥秘》,读到《第二性》的时候,豁然开朗,我看到了别人表述我的经验,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跳过交际舞,因为没有人请我,这是我完全个人的生命经验,不是一个开窍时刻,因为我被踢出去,成为人家的忧虑。
到我三十岁,大家又开始说高是美。
当年我也非常瘦,那就更糟糕。
等到我已经不具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它们反而都成了优点,但在我那个时候都是生理缺陷,所以我没有那个开窍的时刻。
” 谈到女性主义,不能不谈到独立性。
戴锦华说,《简·爱》最后说:“我是一个自由的女人,一个独立的女人”,她以真正的独立面对罗切斯特的时候,不光因为罗切斯特瞎了残了,还因为她有了遗产,在经济上实现了平等。
我们经常说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女人的一间屋”,但她在同一篇文章中说道,“一间屋”的必要的条件是有“自己的支票本”,也就是经济独立。
鲁迅先生说,首先要有独立,“第
一,便是生活。
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
”否则的话,娜拉出走之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谈到鲁迅,记者问戴老师,怎样从女性主义角度看待鲁迅的婚姻问题,特别是与妻子朱安关系的处理。
戴锦华说:“他跟朱安是包办婚姻,而且他有个非常强大的母亲,所以他就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对他来说,是最好的选择。
但朱安的一生,就非常悲惨,而且朱安完全从所有叙述中消失了。
我们必须体会当时的社会背景,那是个新旧交替的时代,我管它叫‘未死方生’,你看那个旧的社会,旧的自我还没有死,而新的自我已经长出芽儿来。
鲁迅只能委曲求全。
反过来说,鲁迅比胡适要好啊,胡适的母亲一拿菜刀,他就缩回去了,他的太太一发脾气,他就没辙了,一辈子和包办的妻子生活。
所以,鲁迅在这点上,还算是勇敢的吧。
但这个勇敢是以牺牲朱安为代价的,以牺牲最弱者为代价的。
” 我们记得,好多年前,女作家徐坤说过,如果没有许广平,鲁迅还会彷徨很多年,鲁迅后半生都是许广平照亮的。
一开始来参加沙龙,感觉是小众之中的小众,当看到有那么多的人来,觉得小众不小。
当听完戴锦华的言说,感觉女性意识问题,不是小众话题,而是大众话题;不是轻松话题,而是沉重话题。
■责任编辑郭爱凤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