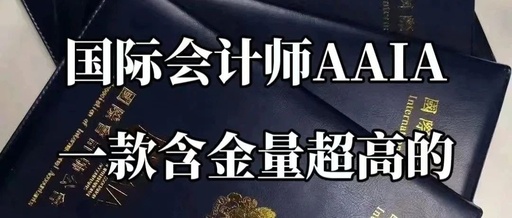中国、苏联卫星和美国科学
——从谢家麟的经历看中美科技关系的演化
王作跃
就在美国努力应对一场严重的经济衰退和其他挑战的时候,中国及其科技上的进步越来越成了美国全国关注的一个中心议题。
例如,2011年1月25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就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反映在全球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上。
他并具体举例,提到中国的两项成就:“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太阳能研究设施”和“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
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苏联卫星时刻’(Sputnikmoment)”,呼吁美国增加科技与教育投资,发誓要“在创新、教育、建设方面超过世界其他各地”。
作为一个科技史学者,我曾经研究过中美科技关系史以及美国当年是如何应对苏联卫星发射所引起的危机的。
把中国的崛起与卫星危机作类比,我认为既有得当也有不得当的地方。
的确,今天就像卫星危机时一样,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而奥巴马总统也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明智地把它划分为一个在科技与教育上的挑战,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
这个类比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美国史上还很少有像卫星事件这样有震撼力的例子。
它导致了联邦在上述领域里的投资急剧增加,并加强了朝野两党在总体国家政策上的共识。
然而,当代中美之间在众多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与当年美苏之间的针锋相对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我希望透过分析中美科学关系的历史背景,来了解其在塑造当今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未来创造合作机会、携手解决共同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大约在60年前,中国物理学家谢家麟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他于1951年9月20日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中国的邮轮“克里夫兰总统号”。
尽管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但是这扇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尤其是那些希望与家人团聚的学生还是有可能回国的。
谢家麟在 1947年赴美留学时,将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国内。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心中兴奋不已。
但是到了檀香山,他的梦想被打破了。
美国政府官员不允许他和另外几位中国留学生继续他们的旅程,理由是总统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禁止部分外国人离开美国。
美国“铁幕”就此降临。
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期间,这项旨在阻止技术人才流入到冷战中美国的敌对国家的政策,导致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纯因政治原因而被事实上扣押在了美国。
后来,经过美中的日内瓦谈判,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几百位中国留学生、科学家,最终在1954年到1955年间获准回国,但是这些扣押行为却激起了许多中国人和其他人的不满。
而这些人原本对美国还持有相当的好感。
正如1954年美国大学的一些研究亚洲的学者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扣押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公正的理念是不相容的”。
比起他们可能带回中国的技术,这一行动“在国内外所造成的敌意”,对美国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害处。
此后在1957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再次将留美华人科学家与美国冷战策略连接起来。
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使全美国无比震惊。
没过几个星期,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这两位华人物理学家,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新闻周刊》在“这两个中国人的选择”的标题下,称赞李、杨在苏联卫星冲击的阴影下显示出了对美国的忠诚。
如果说谢家麟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归返中国的一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百分之六十从事科技领域的工作)(“归者”),他们使得中国科学更加“美国化”,那么李和杨则是在美国科学界中四千左右华人“留者”精英的代表。
当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归者和留者又再次联手,有力地促进了美中科技交流与合作。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谢家麟和李政道,以及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潘诺夫斯基一起,以SLAC为基础,共同设计建造了北京正 24卷第1期(总139期) ·1· 负电子对撞机。
这一成果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前往进行研究。
由于潘诺夫斯基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做的工作及他对国际科学的贡献,他在中国倍受爱戴。
同时他也利用他在中美科学界的人脉联系,推动中国参与国际核军备控制(包括核不扩散)方面的活动。
潘诺夫斯基和谢家麟2002年于北京合影。
或许称得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代归、留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新一代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再一次成为美国科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新一代留学生又进一步促进了太平洋两岸的科学合作,且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公共健康等方面。
要应对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重组,都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到目前为止,也一直比较注意措词,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看作是世界上的
一 个正面发展,是对美国提出的有建设性的挑战。
他这一届政府也延续了尼克松之后,美国两大政党持续推动中美两国科学合作的传统。
然而,另一方面,确有人对美中科技交流持否定观点。
例如,有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盗窃美国的技术,认为中国与斯大林时代的俄国没有两样,认为“我们在(与中国)交往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于是,他就在美国联邦2011年预算提案中加入了一项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的条例,并于2011年4月通过。
在国际交流中保护美国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定义得太狭隘了,就有可能忽视国际交流的价值和理想。
这些价值和理想包括这样的理念,即科学家应该可以自由地跨国流动和国际间应提倡科学合作。
二者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美国和世界科学界所推崇。
美国科技的兴盛发达受惠于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科学家。
再者,正如许良英教授(爱因斯坦著述在中国的主要编译者)在接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萨哈洛夫奖时,通过其子所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科学界与中国保持联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十分重要的。
无论我们是不是处于另一个“苏联卫星时代”,冷战世界已经过去了。
在此时,我们应该鼓励当代像谢家麟和潘诺夫斯基那样的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超越国界进行合作,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解决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而不是给他们制造障碍。
原文载于APSNews(《美国物理学会通讯》)2011年11月号,原题:China,Sputnik,andAmericanScience。
应本刊邀请,文章作者,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协助将此译成中文,译者沈慧。
作者通信地址:ZuoyueWang,DepartmentofHistory,CaliforniaStatePolytechnicUniversity,3801W.TempleAve.,Pomona,CA91768,USA;zywang@csupomona.edu。
·2· 现代物理知识
例如,2011年1月25日,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在他的国情咨文中,就以中国和印度的崛起来说明“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尤其反映在全球对工作机会的竞争上。
他并具体举例,提到中国的两项成就:“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私有太阳能研究设施”和“世界上最快的计算机”。
他认为“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苏联卫星时刻’(Sputnikmoment)”,呼吁美国增加科技与教育投资,发誓要“在创新、教育、建设方面超过世界其他各地”。
作为一个科技史学者,我曾经研究过中美科技关系史以及美国当年是如何应对苏联卫星发射所引起的危机的。
把中国的崛起与卫星危机作类比,我认为既有得当也有不得当的地方。
的确,今天就像卫星危机时一样,美国在世界上的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的挑战。
而奥巴马总统也像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总统一样,明智地把它划分为一个在科技与教育上的挑战,而不是一个直接的军事挑战。
这个类比的另一个吸引人的地方是,在美国史上还很少有像卫星事件这样有震撼力的例子。
它导致了联邦在上述领域里的投资急剧增加,并加强了朝野两党在总体国家政策上的共识。
然而,当代中美之间在众多领域都有紧密的联系,与当年美苏之间的针锋相对有很大的不同。
在这里我希望透过分析中美科学关系的历史背景,来了解其在塑造当今中美关系所起的作用,以及对未来创造合作机会、携手解决共同问题所可能产生的影响。
大约在60年前,中国物理学家谢家麟从斯坦福大学获得了物理博士学位。
他于1951年9月20日登上了从旧金山开往中国的邮轮“克里夫兰总统号”。
尽管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及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已开始限制中国留学生回国,但是这扇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尤其是那些希望与家人团聚的学生还是有可能回国的。
谢家麟在 1947年赴美留学时,将妻子和孩子都留在了国内。
现在终于可以回家了,心中兴奋不已。
但是到了檀香山,他的梦想被打破了。
美国政府官员不允许他和另外几位中国留学生继续他们的旅程,理由是总统发布了一道新的命令,禁止部分外国人离开美国。
美国“铁幕”就此降临。
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期间,这项旨在阻止技术人才流入到冷战中美国的敌对国家的政策,导致了许多中国科学家纯因政治原因而被事实上扣押在了美国。
后来,经过美中的日内瓦谈判,包括谢家麟在内的几百位中国留学生、科学家,最终在1954年到1955年间获准回国,但是这些扣押行为却激起了许多中国人和其他人的不满。
而这些人原本对美国还持有相当的好感。
正如1954年美国大学的一些研究亚洲的学者在给《纽约时报》的一封信中所指出的那样:扣押中国科学家“与美国公正的理念是不相容的”。
比起他们可能带回中国的技术,这一行动“在国内外所造成的敌意”,对美国反而会产生更大的害处。
此后在1957年发生的戏剧性事件,再次将留美华人科学家与美国冷战策略连接起来。
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它使全美国无比震惊。
没过几个星期,哥伦比亚大学的李政道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杨振宁这两位华人物理学家,被宣布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奖。
《新闻周刊》在“这两个中国人的选择”的标题下,称赞李、杨在苏联卫星冲击的阴影下显示出了对美国的忠诚。
如果说谢家麟代表了20世纪50年代从美国归返中国的一千多名中国留学生(其中百分之六十从事科技领域的工作)(“归者”),他们使得中国科学更加“美国化”,那么李和杨则是在美国科学界中四千左右华人“留者”精英的代表。
当中美两国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重新建立关系的时候,归者和留者又再次联手,有力地促进了美中科技交流与合作。
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谢家麟和李政道,以及斯坦福加速器中心的潘诺夫斯基一起,以SLAC为基础,共同设计建造了北京正 24卷第1期(总139期) ·1· 负电子对撞机。
这一成果吸引了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前往进行研究。
由于潘诺夫斯基为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所做的工作及他对国际科学的贡献,他在中国倍受爱戴。
同时他也利用他在中美科学界的人脉联系,推动中国参与国际核军备控制(包括核不扩散)方面的活动。
潘诺夫斯基和谢家麟2002年于北京合影。
或许称得上最重要的是,在这代归、留华人科学家的帮助下,新一代的中国学生留学美国,再一次成为美国科学界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新一代留学生又进一步促进了太平洋两岸的科学合作,且所涉及的领域极其广泛,从全球气候变暖到公共健康等方面。
要应对当今国际社会所面临的诸多挑战,如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重组,都需要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
事实上,奥巴马总统到目前为止,也一直比较注意措词,把中国和印度的崛起看作是世界上的
一 个正面发展,是对美国提出的有建设性的挑战。
他这一届政府也延续了尼克松之后,美国两大政党持续推动中美两国科学合作的传统。
然而,另一方面,确有人对美中科技交流持否定观点。
例如,有国会议员认为中国盗窃美国的技术,认为中国与斯大林时代的俄国没有两样,认为“我们在(与中国)交往中没有得到任何好处”。
于是,他就在美国联邦2011年预算提案中加入了一项禁止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与中国进行科技交流的条例,并于2011年4月通过。
在国际交流中保护美国国家利益是必要的,但如果将其定义得太狭隘了,就有可能忽视国际交流的价值和理想。
这些价值和理想包括这样的理念,即科学家应该可以自由地跨国流动和国际间应提倡科学合作。
二者长期以来一直备受美国和世界科学界所推崇。
美国科技的兴盛发达受惠于国际交流与合作,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20世纪从中国及其他国家吸引了大量的移民科学家。
再者,正如许良英教授(爱因斯坦著述在中国的主要编译者)在接受2008年美国物理学会萨哈洛夫奖时,通过其子所发表的书面致辞中所指出的那样,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科学界与中国保持联系对中国的社会进步是十分重要的。
无论我们是不是处于另一个“苏联卫星时代”,冷战世界已经过去了。
在此时,我们应该鼓励当代像谢家麟和潘诺夫斯基那样的有国际视野的科学家,超越国界进行合作,从而推动科学的进步,解决我们所共同面临的全球问题,而不是给他们制造障碍。
原文载于APSNews(《美国物理学会通讯》)2011年11月号,原题:China,Sputnik,andAmericanScience。
应本刊邀请,文章作者,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王作跃教授,协助将此译成中文,译者沈慧。
作者通信地址:ZuoyueWang,DepartmentofHistory,CaliforniaStatePolytechnicUniversity,3801W.TempleAve.,Pomona,CA91768,USA;zywang@csupomona.edu。
·2· 现代物理知识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