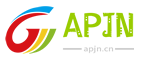10版月光城
荒灯
许俊文
许多过往,就像湮灭于尘埃的灯,其中的一两盏,偶或被意外点亮。
那是一个寻常的夜晚,我重新捧起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
这本书,很多年前读过。
那时自己约莫三十多岁,不清不楚喜欢上了文学,见书就买。
至于读或没读,鬼知道。
伍尔夫在写作《到灯塔去》时,或许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却无法完整和准确表达出来,她选择了意识流。
这与我的阅读习惯不大合辙,因而读得索然寡味,没看到一半便将其放下了。
这一放,如许岁月流逝,当它再次来到我的手上,书与人俱老矣。
人自不必说了,书纸泛黄、变形、憔悴,书脊的胶水也已失去粘性,稍微翻动,书页便像散脱的竹简。
这一回,总算断断续续地把它读完。
《到灯塔去》给我的感觉,说不上好还是不好——萝卜青菜,各有喜爱。
但它却让我对神秘的灯塔有了某种隐秘的期待。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连那座村庄的名字都忘了。
这里,我借用伍尔夫的“灯塔”,姑且就称其为“灯塔村”吧。
它配这个名字。
那日,医生兼作家的征桦开车来找我,说是闷得慌,身体里的光与郁气都出不来,约我去山中转悠,看看古灯塔。
我好生纳闷,灯塔不是大海和江河的眼睛么,怎么会跑到闭塞的大山中去呢?征桦言之凿凿,有古灯塔,我们找找看。
就我们二人,入山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拐弯抹角地且走且看。
好像是暮春,山下的杜鹃已经开残,高山上的杜鹃却轰轰烈烈。
这个时候,一条荒寂的古徽道于纷披的草木中若隐若现。
当时我们未作多想,便拐了上去。
皖南的古徽道我曾走过几条,极难走,上山,膝盖顶着下巴;下山,腿肚子打颤,眼睛不敢斜视。
实话说,没有一条我是走完全程的。
这条古徽道开辟于何年,答案只能根据微商发迹的历史推测,想必应在明清之际。
它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说不清。
一条穿山越岭的羊场小道,一旦人和骡马消失了,毁坏的速度可想而知。
形象点说,就像一根被遗弃在荒野的烂草绳,任凭风吹雨打。
最先觊觎的是草木,它们仿佛记仇。
当初的修路者,刈草、斫木、凿石,必要的损毁可以想见。
现在倒好,草木、荆棘的后代从路的两边挤压过来,隔着一条缝隙握手言欢——否定之否定。
雨水的破坏力更强,一些路段被山洪冲毁,青石板七零八落,给人一种骨骼散架的印象。
征桦在前面探路,我则捡了一根枯枝作拐杖,尾随于后。
我们走走,歇歇,看看路边的闲花,间或瞭一眼白云。
路越来越难走,忽上忽下,时左时右,逼窄的地方只容一人侧身而过。
恐高的征桦不敢侧目陡峭的悬崖,眼睛只盯着脚尖,用“蚁行”再恰当不过了。
我呢,借助于“拐杖”也走得胆战心惊。
灯塔,就 在这时出现了。
它立在山道的一个急弯处,主体是 一根两米多高的石柱,柱顶上有只类似马灯的玻璃罩子,严严实实地罩住一只粗瓷大碗,那想必是盛放灯油与灯芯的灯盏了。
立柱上的字迹已漶漫不清,我一次又一次踮起脚辨认,方辨认出“乾隆三年”四字。
算算,距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了。
这是一盏名副其实的“荒灯”——荒芜之灯。
灯塔的周围布满荆棘与高过人头的野草。
坚硬的花岗岩石柱,也抵挡不住经年风霜雨雪的剥蚀,该脱落还是脱落。
我看见一只鸟落在蒙尘的灯盏上,磕头磕脑地鸣叫,声音有几分嘶哑、哀切。
附近一位砍柴老人告诉我们,那是“叫魂鸟”。
空山寂寂,它为谁叫魂呢?灯塔旁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堆,土堆之上,生长着灌木和杂草。
若不是老人指点,我们看不出它是一座坟墓。
那一抷矮趴趴的黄土之下,竟埋葬着一个凄恻的故事。
逝者没留下姓名。
灯塔村人都管她叫“灯塔女人”。
就这么叫了二百多年。
叫着叫着,一座曾经兴旺的山村,空了,只留下这位孤独的老人。
“灯塔女人”命运多舛,她的男人是一个挑夫,受雇于一位商贾,常年往江浙沿海运茶叶,在一个黑夜失足掉下悬崖摔死了,后来,她的两个儿子又以同样的方式殒命。
而然,死亡并未能吓阻那些谋生与谋财的脚步,结对而行的商旅,仍然在这条充满凶险的山道上继续着他们的营生。
失孤的“灯塔女人”,可谓肝肠寸断,每当夜幕降临,便站在后来竖立灯塔的地方,等待自己的男人和儿子的归来,她那悠长、凄婉的呼唤声,犹如一滴冷雨滴落在无际的枯草上,没有任何回响。
她委实成了一只叫魂鸟。
她所有的呼唤都是徒劳的。
她整整呼唤了三年。
村里人都以为这个女人疯了。
第四年,这个女人变卖了家当,捐了一座灯塔,立在她天天伫立的悬崖边。
又种植了一亩地蓖麻,用作灯油。
她把自己对男人和儿子的思念,通过一盏油灯,传递给山道上那些往来的陌生商旅。
一豆荧荧,四季皎然。
从此,“灯塔女人”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皈依,人变得沉默,不再锥心呼唤自己的亲人,而是每天爬上一架木梯,给灯盏添油……其实,她添的不止是油,是焚膏继日的坚守,直至化为灯塔旁的一堆黄土。
这是她的遗愿,死后与灯塔厮守。
时间的逝水一去不回,我们不可能进入“灯塔女人”的时空,但是,面对沧桑的灯塔,似乎能够触及她柔软的内心那束光。
黑沉沉的大山深处,油灯的光虽然微弱、渺小,但它却给夜行人送去一份温暖的提醒与叮咛。
寒来暑往,那些从这条山道上走过的人,挑担的,牵马的,背篓的,想必会记住这盏稀世之灯。
我揣测,那些曾被这盏油灯之光照拂的人,是幸福和幸运的,无论他们走向何方,也无论富贵与贫贱,在他们的记忆里,总会有一盏灯散发着莹洁的光。
我和征桦站在低处,久久仰望着灯塔。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恒念,只要这尘世还有黑暗和不幸,灯塔的光就不会熄灭。
2022年7月15日星期五责编魏振强E—mail:oldbrook@ 深吻 刘鹏 摄 楼顶边缘的舞蹈 肖遥 大一的某个假期,学院几乎都空了,就剩下我们几个文艺队的,吴焰经常来礼堂看我们排练舞蹈,帮我们拿衣服,缠着我们聊天。
我才知道吴焰平时不太回家。
他的后妈生了个妹妹。
排练完一起去录像厅看周星驰的片子,那些天,我和吴焰总有说不完的话,在录像厅憋着说不成,回到学院上楼顶继续说。
学院最浪漫的地方就是那个L型的楼顶,一边带栏杆的,供学生们晾晒被褥,倚在栏杆上,能看到脚下白杨林的树顶,起风的时候,树叶子哗啦啦随风摇曳,在脚下波涛汹涌,特别贴合青春期的心潮起伏。
一边没有栏杆,原则上是不允许过去的,学生们有个默契,只有确定了关系的情侣才会翻越栏杆,远远地离开人群,坐在楼的边缘。
那天晚上,我和吴焰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就翻越了栏杆,我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些情侣们喜欢坐在这个位置:头顶是被晚霞烧红了的天空,极目远望,一弯弦月挂在黛青色的白鹿原上空,整个城市仿佛都在脚下,暮春的风蠢蠢欲动,我俩如果是两个小魔仙,就能立刻手拉手御风而行,低低地滑翔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这里特别适合说“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不爱你了,就从这里跳下去”的情话。
我俩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我以为这就是爱情。
这段爱情,大约是这块爱情角落见证过的最短的爱情。
吴焰很多天没来找我,我巴巴地等着,舍友小树还自告奋勇跑下楼把吴焰叫了上来。
可他来了一直背对着我,和小树她们说笑。
我冷静下来,想起那天我俩说过的傻话。
这些话,对吴焰来说,就像晚上去录像厅看了场戏,他入戏太深说了几句台词而已,结果,我给当真了。
吴焰是我们班最小的,全班女生都把他当开心果,他跟谁都能花马吊嘴卖萌耍帅,寝室夜谈的时候,没人把他当个白马王子,只有我把他当了小王子,硬要当他的玫瑰花。
看着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触碰男女关系中非此即彼的危险边缘,可以肆无忌惮地说笑嬉闹。
我听见了我被踩在脚底下摩擦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我就像一个小丑,在舞台上多光彩,在现实中就多狼狈。
我冲上楼顶,翻过围栏,站在楼顶边缘,很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要飞起来还是要跳下去。
此刻,楼下的宿舍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我跳起舞来,一直跳一直跳,跳到泪流满面,全世界都抛弃我的时候,我对着月亮,对着远山,托起自己。
后来,看到电影《花与爱丽丝》里有一个桥段:爱丽丝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轮到她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评审们很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自我介绍,互相打趣,爱丽丝走到几个评审面前,拿起桌上的一次性纸杯,套在脚趾上当芭蕾舞鞋,跳起了芭蕾舞……这一幕看得我泪流满面,想到了那个在楼顶边缘孤独舞蹈的少女。
接下来的人生,在现实的涡轮机里,游戏规则是争相比拼谁更不在乎,爱情、自尊、理想纷纷沦陷,在情感里,我们学习平衡、控制、算计,谁都舍不得把自己先交出去。
我偶尔跳舞,但再也没有上台表演。
我喜欢在夜晚,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跳,每次跳舞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奋力打捞,在一切旋转着淹没之前奋力打捞。
多年后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我笑到眼泪飞溅。
我分明看到了吴焰的影子。
吴焰把周星驰的腔调和做派模仿得太像了,他也是个心里有伤痕的男孩,很容易进入周星驰扮演的角色,他也有能力把那种底层的伤痛化成强颜欢笑,表现得惟妙惟肖,而我又是个敏感的人,一下子被击中了,自此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年少时候,吴焰喜欢的人,不是我,是舞台上的那个光芒四射的舞者,我喜欢的人,也不是吴焰,是他模仿的周星驰。
那是一个寻常的夜晚,我重新捧起伍尔夫的小说《到灯塔去》。
这本书,很多年前读过。
那时自己约莫三十多岁,不清不楚喜欢上了文学,见书就买。
至于读或没读,鬼知道。
伍尔夫在写作《到灯塔去》时,或许有太多想要表达的东西,却无法完整和准确表达出来,她选择了意识流。
这与我的阅读习惯不大合辙,因而读得索然寡味,没看到一半便将其放下了。
这一放,如许岁月流逝,当它再次来到我的手上,书与人俱老矣。
人自不必说了,书纸泛黄、变形、憔悴,书脊的胶水也已失去粘性,稍微翻动,书页便像散脱的竹简。
这一回,总算断断续续地把它读完。
《到灯塔去》给我的感觉,说不上好还是不好——萝卜青菜,各有喜爱。
但它却让我对神秘的灯塔有了某种隐秘的期待。
时间已经过去很久,连那座村庄的名字都忘了。
这里,我借用伍尔夫的“灯塔”,姑且就称其为“灯塔村”吧。
它配这个名字。
那日,医生兼作家的征桦开车来找我,说是闷得慌,身体里的光与郁气都出不来,约我去山中转悠,看看古灯塔。
我好生纳闷,灯塔不是大海和江河的眼睛么,怎么会跑到闭塞的大山中去呢?征桦言之凿凿,有古灯塔,我们找找看。
就我们二人,入山后沿着一条崎岖小路,拐弯抹角地且走且看。
好像是暮春,山下的杜鹃已经开残,高山上的杜鹃却轰轰烈烈。
这个时候,一条荒寂的古徽道于纷披的草木中若隐若现。
当时我们未作多想,便拐了上去。
皖南的古徽道我曾走过几条,极难走,上山,膝盖顶着下巴;下山,腿肚子打颤,眼睛不敢斜视。
实话说,没有一条我是走完全程的。
这条古徽道开辟于何年,答案只能根据微商发迹的历史推测,想必应在明清之际。
它是什么时候被废弃的呢?说不清。
一条穿山越岭的羊场小道,一旦人和骡马消失了,毁坏的速度可想而知。
形象点说,就像一根被遗弃在荒野的烂草绳,任凭风吹雨打。
最先觊觎的是草木,它们仿佛记仇。
当初的修路者,刈草、斫木、凿石,必要的损毁可以想见。
现在倒好,草木、荆棘的后代从路的两边挤压过来,隔着一条缝隙握手言欢——否定之否定。
雨水的破坏力更强,一些路段被山洪冲毁,青石板七零八落,给人一种骨骼散架的印象。
征桦在前面探路,我则捡了一根枯枝作拐杖,尾随于后。
我们走走,歇歇,看看路边的闲花,间或瞭一眼白云。
路越来越难走,忽上忽下,时左时右,逼窄的地方只容一人侧身而过。
恐高的征桦不敢侧目陡峭的悬崖,眼睛只盯着脚尖,用“蚁行”再恰当不过了。
我呢,借助于“拐杖”也走得胆战心惊。
灯塔,就 在这时出现了。
它立在山道的一个急弯处,主体是 一根两米多高的石柱,柱顶上有只类似马灯的玻璃罩子,严严实实地罩住一只粗瓷大碗,那想必是盛放灯油与灯芯的灯盏了。
立柱上的字迹已漶漫不清,我一次又一次踮起脚辨认,方辨认出“乾隆三年”四字。
算算,距今已有二百五十多年了。
这是一盏名副其实的“荒灯”——荒芜之灯。
灯塔的周围布满荆棘与高过人头的野草。
坚硬的花岗岩石柱,也抵挡不住经年风霜雨雪的剥蚀,该脱落还是脱落。
我看见一只鸟落在蒙尘的灯盏上,磕头磕脑地鸣叫,声音有几分嘶哑、哀切。
附近一位砍柴老人告诉我们,那是“叫魂鸟”。
空山寂寂,它为谁叫魂呢?灯塔旁有一个微微隆起的土堆,土堆之上,生长着灌木和杂草。
若不是老人指点,我们看不出它是一座坟墓。
那一抷矮趴趴的黄土之下,竟埋葬着一个凄恻的故事。
逝者没留下姓名。
灯塔村人都管她叫“灯塔女人”。
就这么叫了二百多年。
叫着叫着,一座曾经兴旺的山村,空了,只留下这位孤独的老人。
“灯塔女人”命运多舛,她的男人是一个挑夫,受雇于一位商贾,常年往江浙沿海运茶叶,在一个黑夜失足掉下悬崖摔死了,后来,她的两个儿子又以同样的方式殒命。
而然,死亡并未能吓阻那些谋生与谋财的脚步,结对而行的商旅,仍然在这条充满凶险的山道上继续着他们的营生。
失孤的“灯塔女人”,可谓肝肠寸断,每当夜幕降临,便站在后来竖立灯塔的地方,等待自己的男人和儿子的归来,她那悠长、凄婉的呼唤声,犹如一滴冷雨滴落在无际的枯草上,没有任何回响。
她委实成了一只叫魂鸟。
她所有的呼唤都是徒劳的。
她整整呼唤了三年。
村里人都以为这个女人疯了。
第四年,这个女人变卖了家当,捐了一座灯塔,立在她天天伫立的悬崖边。
又种植了一亩地蓖麻,用作灯油。
她把自己对男人和儿子的思念,通过一盏油灯,传递给山道上那些往来的陌生商旅。
一豆荧荧,四季皎然。
从此,“灯塔女人”似乎找到了心灵的寄托与皈依,人变得沉默,不再锥心呼唤自己的亲人,而是每天爬上一架木梯,给灯盏添油……其实,她添的不止是油,是焚膏继日的坚守,直至化为灯塔旁的一堆黄土。
这是她的遗愿,死后与灯塔厮守。
时间的逝水一去不回,我们不可能进入“灯塔女人”的时空,但是,面对沧桑的灯塔,似乎能够触及她柔软的内心那束光。
黑沉沉的大山深处,油灯的光虽然微弱、渺小,但它却给夜行人送去一份温暖的提醒与叮咛。
寒来暑往,那些从这条山道上走过的人,挑担的,牵马的,背篓的,想必会记住这盏稀世之灯。
我揣测,那些曾被这盏油灯之光照拂的人,是幸福和幸运的,无论他们走向何方,也无论富贵与贫贱,在他们的记忆里,总会有一盏灯散发着莹洁的光。
我和征桦站在低处,久久仰望着灯塔。
在我的心里,有一个恒念,只要这尘世还有黑暗和不幸,灯塔的光就不会熄灭。
2022年7月15日星期五责编魏振强E—mail:oldbrook@ 深吻 刘鹏 摄 楼顶边缘的舞蹈 肖遥 大一的某个假期,学院几乎都空了,就剩下我们几个文艺队的,吴焰经常来礼堂看我们排练舞蹈,帮我们拿衣服,缠着我们聊天。
我才知道吴焰平时不太回家。
他的后妈生了个妹妹。
排练完一起去录像厅看周星驰的片子,那些天,我和吴焰总有说不完的话,在录像厅憋着说不成,回到学院上楼顶继续说。
学院最浪漫的地方就是那个L型的楼顶,一边带栏杆的,供学生们晾晒被褥,倚在栏杆上,能看到脚下白杨林的树顶,起风的时候,树叶子哗啦啦随风摇曳,在脚下波涛汹涌,特别贴合青春期的心潮起伏。
一边没有栏杆,原则上是不允许过去的,学生们有个默契,只有确定了关系的情侣才会翻越栏杆,远远地离开人群,坐在楼的边缘。
那天晚上,我和吴焰不知怎的,说着说着就翻越了栏杆,我才知道了为什么那些情侣们喜欢坐在这个位置:头顶是被晚霞烧红了的天空,极目远望,一弯弦月挂在黛青色的白鹿原上空,整个城市仿佛都在脚下,暮春的风蠢蠢欲动,我俩如果是两个小魔仙,就能立刻手拉手御风而行,低低地滑翔在这个城市的上空。
这里特别适合说“如果你不爱我了/我不爱你了,就从这里跳下去”的情话。
我俩说了些海誓山盟的话,我以为这就是爱情。
这段爱情,大约是这块爱情角落见证过的最短的爱情。
吴焰很多天没来找我,我巴巴地等着,舍友小树还自告奋勇跑下楼把吴焰叫了上来。
可他来了一直背对着我,和小树她们说笑。
我冷静下来,想起那天我俩说过的傻话。
这些话,对吴焰来说,就像晚上去录像厅看了场戏,他入戏太深说了几句台词而已,结果,我给当真了。
吴焰是我们班最小的,全班女生都把他当开心果,他跟谁都能花马吊嘴卖萌耍帅,寝室夜谈的时候,没人把他当个白马王子,只有我把他当了小王子,硬要当他的玫瑰花。
看着他们没有像我一样触碰男女关系中非此即彼的危险边缘,可以肆无忌惮地说笑嬉闹。
我听见了我被踩在脚底下摩擦的吱吱嘎嘎的声音。
我就像一个小丑,在舞台上多光彩,在现实中就多狼狈。
我冲上楼顶,翻过围栏,站在楼顶边缘,很恍惚,不知道自己是要飞起来还是要跳下去。
此刻,楼下的宿舍传来隐隐约约的音乐,我跳起舞来,一直跳一直跳,跳到泪流满面,全世界都抛弃我的时候,我对着月亮,对着远山,托起自己。
后来,看到电影《花与爱丽丝》里有一个桥段:爱丽丝去参加一个选秀节目,轮到她的时候,已经快结束了,评审们很不耐烦地打断她的自我介绍,互相打趣,爱丽丝走到几个评审面前,拿起桌上的一次性纸杯,套在脚趾上当芭蕾舞鞋,跳起了芭蕾舞……这一幕看得我泪流满面,想到了那个在楼顶边缘孤独舞蹈的少女。
接下来的人生,在现实的涡轮机里,游戏规则是争相比拼谁更不在乎,爱情、自尊、理想纷纷沦陷,在情感里,我们学习平衡、控制、算计,谁都舍不得把自己先交出去。
我偶尔跳舞,但再也没有上台表演。
我喜欢在夜晚,躲在一个没人的地方跳,每次跳舞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在奋力打捞,在一切旋转着淹没之前奋力打捞。
多年后看周星驰的大话西游,我笑到眼泪飞溅。
我分明看到了吴焰的影子。
吴焰把周星驰的腔调和做派模仿得太像了,他也是个心里有伤痕的男孩,很容易进入周星驰扮演的角色,他也有能力把那种底层的伤痛化成强颜欢笑,表现得惟妙惟肖,而我又是个敏感的人,一下子被击中了,自此我才恍然大悟,其实年少时候,吴焰喜欢的人,不是我,是舞台上的那个光芒四射的舞者,我喜欢的人,也不是吴焰,是他模仿的周星驰。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