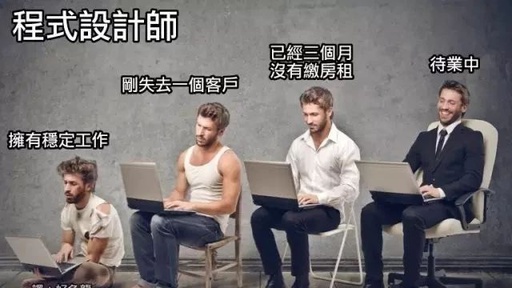年4月29日星期五壬寅年三月廿
九 责任编辑:居永贵版式:纪蕾 在线投稿:新闻热线:84683100刊头题字:周同 情同父女亲如一家 ——汪曾祺与“藏妞”央珍 □金实秋 汪曾祺与央珍认识较睌。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春。
那时,汪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文坛名人了,而央珍则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
汪老七十多岁矣,央珍才三十岁,刚与龙冬结婚不久,从拉萨调到北京工作。
苏北是汪先生的忘年交,也是龙冬夫妇的好朋友,汪老曾给龙冬、苏北的小说集写过序。
龙冬是在西藏工作时,与央珍认识并恋爱结婚的。
苏北在1993年11月3日的日记中,略述了那天央珍与汪老见面的情景。
其时,央珍已多次去过汪老家了。
1993年11月3日北京今天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
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央珍当然更清晰地记得她与汪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是在1992年春天。
……我们摁响了先生在蒲黄榆家的门铃,不一会儿从里面传来应声和拖拖趿趿的脚步声。
门开了,铁栅栏门的后面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老人,他没有马上请进,而是显得严肃地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推开铁门,“来啦,藏妞儿。
”那声音是清脆的,还带着点京戏的味儿。
在我们的笑声中,有一个更响亮的笑声从先生的身后传来,那是开朗热情的汪师母。
我的矜持和紧张一下子烟消云散。
央珍,1963年出生于西藏拉萨,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供职于《西藏文学》。
她创作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完成的长篇小说,并被誉为“当代西藏文学的里程碑”、西藏的《红楼梦》,还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
文坛上的人都夸她是集美丽、善良、温和与才华于一身的藏族女子,是西藏最好的、真正有贵族气质的女作家。
央珍自调到北京之后,龙冬夫妇就成了汪先生家的常客。
龙冬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我跟央珍一周要去两次,那就是说像上瘾的一件事情一样,……一般来讲,我们是一周去一次,我们看父母也是一周去一次,长一点的话,两周。
我们基本都是下午去,更多是晚饭后去……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和家人走出楼门,走出院门,走到街上,我们会说“如沐春风”,来汪先生这里如同洗了一个澡,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特别是我的家人,她的萎靡霎 那间烟消云散。
(《汪曾祺是真实的》)央珍则说:每次从先生家里告辞,走在 灯火阑珊的大街上,我们的心情好极,仿佛刚从一处圣洁的地方朝拜回来,精神和心灵得到了净化,心胸因此感觉到博大和充实。
她说过的一句话,很值得搞文学的人借鉴和深思:很多人往往以作品认识一位作家,而我相反,我从认识一位作家和这位作家的人品人格认识了他的著作…… 苏北还提到了汪曾祺要为央珍小说写序的事。
他在《汪曾祺与序言》中说:有一个时期,他(汪曾祺)似乎为年轻人写序写上了“瘾”……他曾跟龙冬的夫人央珍聊天,央珍告诉他手头刚完成了一个长篇,汪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说:“别人讲,我的序写得不错!”坐在边上的汪朝笑话他:“爸,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起来。
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访问西藏时,央珍曾全程陪同,朝夕相伴,所以陈若曦对央珍十分了解,非常赞叹,称央珍为才女,并预言从央珍的文学才华和成就来看,将来在文学事业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央珍与汪曾祺的忘年交一直持续到汪老生命的尽头。
1997年初春,农历腊月廿六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邀请汪老等文化、新闻界名流联欢,龙冬夫妇专门负责陪伴照顾汪老,一起喝酒、一块聊天…… 在三月份,汪老还到龙冬、央珍家谈天说地,坐在金黄色落地窗纱前的、央珍从西藏带来的椅子上笑眯眯地抽烟。
央珍他们开玩笑说汪老像个活佛,汪先生则拍了拍龙冬的脑袋,那就算是“摸顶”啦。
就在汪老去世前的一两个月,龙冬和苏北一天上午去了汪老家,汪老还拿出一幅画要送给央珍,因为央珍喜欢紫色的东西,汪先生刻意给画了一幅紫藤萝。
得知汪老遽然病逝的噩耗,龙冬、央珍极度悲恸。
在汪老辞世的第二天,他们就赶到了汪家,还一趟趟地与汪老的子女商议和料理后事,并为汪老的追悼会录制、选放了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
在汪朝《我们的爸》一文中,她还记下了央珍和汪师母的亲情。
汪师母动情地说“那个央珍真是可爱”,“真想认央珍作干女儿”。
“一年多后,妈也去世了。
此前,龙冬、央珍常来看她。
妈看见他们很高兴,能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
后来她日渐衰弱,不怎么说话了。
央珍俯在她的枕畔,一遍遍亲吻着她的面颊,她们之间真是流动着母女般的亲情,令人感动。
”施亮 是龙冬、央珍的好朋友,也是汪先生的忘年交。
他在《追往纪念的位置》中有一段有关央珍与汪老的回忆。
他写道:我与汪老初次见面时提到龙冬也是我的好友,汪老风趣地说:“哈,他娶了一个藏族媳妇儿!”我向他们(指龙冬、央珍)聊起此事,央珍立刻告诉我:“你猜我头一次见到汪老,他跟我说什么?”略顿一下,她就忍不住笑了:“他说,你好,藏妞儿!”然后,她就仰头放声咯咯大笑起来。
汪老很喜欢与年轻朋友们在一起,他与龙冬、央珍夫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后来,汪老遽然病逝,我打电话到龙冬、央珍家询问,央珍说起了汪老病故的经过,以及治丧过程,几度言语停顿、哽咽悲泣,她的语调中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哀痛。
汪老去世后,央珍、龙冬不仅多次去福田公墓祭奠汪先生,还在2017年夏天汪老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开车专程去高邮,向汪先生奉上一瓣心香。
仿佛是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几个月后,央珍也去世了,她到天堂与汪先生、汪师母去聊天谈心了。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我主编了《永远的汪曾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收入了央珍怀念汪先生的文章《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
按照相关要求,我向央珍发送了请授权转载的信函。
但是,久久未获回音。
央珍的文章,充满深情而又朴素地叙述了她和汪曾祺的忘年之交、父女之情。
我实在不忍舍割,没有函复,不等于不同意转载,还是编进了书中。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就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意外地收到了央珍的一封信,信不长,全文如下: 金实秋先生:您好!今天收到由西藏转来的您的信函,这其间已过去了五个月。
“回执”(注:指联系授权的作者回执)寄给您肯定晚了。
但愿您主编的书中仍有我的文章。
因为汪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我把他和他的夫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能借贵书表达我永远的思念。
我早已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藏学》杂志当编辑。
祝好! 央珍2008,4,11随信寄来“回执”外,还附上了她的名片。
我一直珍藏着央珍的这一封信,这封信承载着汪老与她的父女之情。
2017年10月12日,央珍不幸病逝。
汪朗、汪朝及时去了龙冬的家,按照藏人的习俗,他们向临时灵堂中的央珍遗像鞠躬,献上洁白的哈达。
2019年1月5日,在雍和宫里隆重举办了“《无性別的神》——央珍作品北京发布会”,汪朝在会上动情地叙述了央珍与他一家的诚挚情谊,说,“这不是作家之间的感情,是两代人的感情。
” 我出生于里下河平原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县城——高邮。
她是吟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绮丽婉约词风的秦少游故里,是吹着“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散曲的王磐梓里,也是写出“多年父子成兄弟”等充满生活情趣文字的汪曾祺乡里。
因而这个地方的民风淳朴、文风昌盛,耕读传家似乎已成为一种约定。
书于我而言是年幼时的暖心伙伴。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守着几亩田地生活,但父亲在县城工作,思想较之乡邻而言开明许多。
我出生时瘦小羸弱,一度令父母亲愁肠百结,他们担心这样一个“病茨菇”丫头长不大。
因为气力不足,我也甚少参与小伙伴们跳绳、蹦橡皮筋等活动。
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在玩乐时,我总是在一旁远远地观望。
父亲坚信读书是打破农村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宿命的唯一良方。
每周回家,他总会给年幼的我读读书,讲讲历史掌故。
许是从那时起,我便算在读书上开了蒙。
于是,当我孤单时就会翻看连环画和小人书,在故事中寻找友爱和温暖。
四年级被学校选为代表参加乡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时,以前看过的书、读过的优美语段像得到召唤似的一股脑地从蛰伏中苏醒过来,变成了我最暖心的伙伴供我调遣。
书于我而言是成长时的良师益友。
许是因为左右脑发育的不均衡,学习数理化于我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事。
每次考 书籍是最暖心的治愈 □杨芳 试,作为语文和英语尖子生的我,总会因为数理化的短腿而跌入后进生的榜单。
这对尚未完全成长的我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
一次次的否定,让我变得自卑而胆怯。
是书本中的先贤古哲用辨证的思想启悟了我,“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于是,我逐渐摒却了心魔,只问耕耘,不问结果,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初心审慎地接受自己,悦纳自己。
书于我而言是治愈的良方佳剂。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难免也被教育产业化的大潮裹挟着前行,疲于奔命地穿梭于各大课外培训点的我在剧场效应的绑架下越发焦虑。
精力与时间的透支,投入与产出的失衡,让人平生一股怨气,于是说教、抱怨、训斥、责骂等有意无意中成了转嫁负面情绪的出口,因而和谐的亲子关系面临崩塌。
这时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孔子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无数教育书籍无一不在警示我们——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收获的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孩子们所能接受的永远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孩子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本不可被类比、被复 制,因为个人禀赋、学习习惯、生活环境等不同,他们抽穗拔节的生长期也不会一样,我们所能给予的便是静待花开。
或许,人们有许多休闲娱乐的方式,然而于我而言最放松的事莫过于独处时翻几页书,读几行字;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见两个孩子手捧经卷,研读书本。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读书能让生命变得厚重而鲜亮,使人不再圈囿于自己的小天地而自怨自艾,使人看待问题不再受制于本我的小格局,而达到“养心”的目的。
于小说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更多地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从而更积极地直面人生;于经史子集的博大精深中,研习传统文化,懂得自省顿悟,从而笑看人生的风云进退;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兴衰更迭中,学会更多地关注民生,从而更为淡泊清明地生活。
将读书作为一种家风传承,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所幸我的两个孩子都爱读书。
我希望远在他国求学的长子,有一天在异乡月上西楼、独倚窗栏之际,会记起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慨;在学业遇到瓶颈、生活遇到挫折时,会记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鼓励;在沾沾自喜、浮躁不平之时,忆及“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告诫,从而坚定“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初心。
我也希望尚懵懂的次子能浸濡书香,沐浴阳光,成长为一个开心、明快的少年。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为母之道 □刘艳萍 母亲只是一种天然属性,没那么值得大唱赞歌,非要弄出感天动地的样子。
还是胡适的《儿子》写得潇洒“: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如此运笔,不知是否没亲自经历十月怀胎和分娩之痛的原因。
“女人本弱,为母则刚”,经常被作为一句口号,听起来确实足够铿锵。
可事实上,弱小的女性当了妈,秒变金刚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而更多不易背后的真相恐怕是,一个母亲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身板和逻辑,为孩子构建一个自以为安全的空间,作为对自己“母亲”身份的交待。
其实,天并不会那么轻易塌下来。
即便塌下来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撑还在,命运不会随意对一个孩子下手,说好了“天无绝人之路”的呐。
我们说“女人本弱,为母则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母亲的“本弱”倒有可能对子女形成“弱伤害”。
《红楼梦》里的金荣,就有这么个母亲。
他们娘儿俩的存在感本来极低,如果不是因为金荣在贾府的家塾里闹了一通的话,可能都没人会注意还有这么对母子。
金荣的姑姑嫁给了荣国府的外围亲戚贾璜,空有奶奶的名头而已。
金荣靠着姑姑的关系进入贾府家塾读书。
金荣和贾兰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并没有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而是争风吃醋、惹是生非,得罪秦钟、冲撞宝玉,最后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磕头认错。
可金荣到底咽不下这口气。
如果是被宝玉欺负也就罢了,秦钟不过跟自己一样,凭什么呢。
老鸹落在猪身上,只看到人家黑,是人性的弱点。
金荣在母亲面前叫屈。
母亲胡氏并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她只要金荣安静下来“: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
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嚼用。
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
再者,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
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
” 母亲的利弊分析简直无可辩驳,学房里有大福利,结识薛大爷。
可薛大爷给金荣银子的原因,做母亲的真的不知道么!胡氏寡妇熬儿,断然没有把钱财看得比孩子还重的理由。
那剩下的原因,恐怕就是在这位母亲的认知里,有地方念书,有好衣服穿,还能剩几个钱,就是她眼中无可攀比的“好”了。
至于这“好”是拿什么换来的,是否低三下
四,有没有被欺辱,她没有想过,或者不敢想。
因为她怕有任何变故,会毁坏了这“好”。
所以小姑子璜大奶奶想在她面前抖威风,声称自己要去找秦可卿理论时,胡氏吓得连忙央求:“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若闹起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非但不能请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
” “嚼用”是千钧重负,是弱者更弱的推手。
因为“嚼用”,胡氏愈加畏缩。
她之所以甘愿被现实碾压, 是唯恐孤儿寡母不再有谄媚的资格和机会。
在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压力面前,打着为了孩子好的旗号,想必不少母亲都曾给过孩子类似的“弱伤害”。
想到此例,常常检讨自己。
既然相逢于人间一场,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提升自己认知,助力孩子塑造健康人格健全灵魂,方是为母之道。
俄罗斯的天空 □陈仁存 有一位朋友问我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感受是什么,我说“:俄罗斯的天空。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到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九级浪》《查波罗什人复信给土耳其苏丹》、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无不让我们感受着俄罗斯天空的凝重。
在乌云压顶的天空下,人们勇敢无畏地生活,承受命运的艰辛,恶劣的环境下再生着希望。
暴风雪中裹挟着狂涛和烈焰,以及虚无主义者到民间去,苦苦寻找真理的灵魂。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电视剧,天空的主色调就是彤云密布。
表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广阔无边的茂密森林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激烈残酷的狙击战。
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带领五名美丽的女战士在丛林中艰难跋涉,与人数众多的敌军反复周旋。
热尼亚面对敌军的包围,引吭高歌,唱起《喀秋莎》“:正巧梨花开在了天边,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还有瓦斯科夫准尉最感人的一句话“:在我们的身后,还有俄罗斯,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坚强的信念和斗志,才会有“乌拉——”,有“红军饮马第聂伯河”,有“反法西斯胜利日”。
俄罗斯的天空,代表着俄罗斯民族不朽的精神。
九 责任编辑:居永贵版式:纪蕾 在线投稿:新闻热线:84683100刊头题字:周同 情同父女亲如一家 ——汪曾祺与“藏妞”央珍 □金实秋 汪曾祺与央珍认识较睌。
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2年春。
那时,汪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文坛名人了,而央珍则是一位初露头角的年轻作者。
汪老七十多岁矣,央珍才三十岁,刚与龙冬结婚不久,从拉萨调到北京工作。
苏北是汪先生的忘年交,也是龙冬夫妇的好朋友,汪老曾给龙冬、苏北的小说集写过序。
龙冬是在西藏工作时,与央珍认识并恋爱结婚的。
苏北在1993年11月3日的日记中,略述了那天央珍与汪老见面的情景。
其时,央珍已多次去过汪老家了。
1993年11月3日北京今天同龙冬、央珍夫妇到汪先生家。
……汪先生见到央珍就很高兴,总是说“这是一个不错的女孩。
”汪先生说龙冬“找个藏族老婆”。
一副挺羡慕的样子,又好像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怎么没找个少数民族的老婆。
央珍当然更清晰地记得她与汪先生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第一次见到汪先生是在1992年春天。
……我们摁响了先生在蒲黄榆家的门铃,不一会儿从里面传来应声和拖拖趿趿的脚步声。
门开了,铁栅栏门的后面是一位极其普通的老人,他没有马上请进,而是显得严肃地先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然后推开铁门,“来啦,藏妞儿。
”那声音是清脆的,还带着点京戏的味儿。
在我们的笑声中,有一个更响亮的笑声从先生的身后传来,那是开朗热情的汪师母。
我的矜持和紧张一下子烟消云散。
央珍,1963年出生于西藏拉萨,1985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供职于《西藏文学》。
她创作的《无性别的神》,是藏族文学史上第一部由女性完成的长篇小说,并被誉为“当代西藏文学的里程碑”、西藏的《红楼梦》,还被改编成二十集电视连续剧《拉萨往事》。
文坛上的人都夸她是集美丽、善良、温和与才华于一身的藏族女子,是西藏最好的、真正有贵族气质的女作家。
央珍自调到北京之后,龙冬夫妇就成了汪先生家的常客。
龙冬回忆说:我记得当时最多的时候,我跟央珍一周要去两次,那就是说像上瘾的一件事情一样,……一般来讲,我们是一周去一次,我们看父母也是一周去一次,长一点的话,两周。
我们基本都是下午去,更多是晚饭后去……离开他房间的时候,……我和家人走出楼门,走出院门,走到街上,我们会说“如沐春风”,来汪先生这里如同洗了一个澡,心情是那么轻松愉快,特别是我的家人,她的萎靡霎 那间烟消云散。
(《汪曾祺是真实的》)央珍则说:每次从先生家里告辞,走在 灯火阑珊的大街上,我们的心情好极,仿佛刚从一处圣洁的地方朝拜回来,精神和心灵得到了净化,心胸因此感觉到博大和充实。
她说过的一句话,很值得搞文学的人借鉴和深思:很多人往往以作品认识一位作家,而我相反,我从认识一位作家和这位作家的人品人格认识了他的著作…… 苏北还提到了汪曾祺要为央珍小说写序的事。
他在《汪曾祺与序言》中说:有一个时期,他(汪曾祺)似乎为年轻人写序写上了“瘾”……他曾跟龙冬的夫人央珍聊天,央珍告诉他手头刚完成了一个长篇,汪先生沉静了一会儿,说:“别人讲,我的序写得不错!”坐在边上的汪朝笑话他:“爸,你是不是要给人家央珍写序呀!”汪先生笑了起来。
台湾著名作家陈若曦女士访问西藏时,央珍曾全程陪同,朝夕相伴,所以陈若曦对央珍十分了解,非常赞叹,称央珍为才女,并预言从央珍的文学才华和成就来看,将来在文学事业上的前途不可限量。
央珍与汪曾祺的忘年交一直持续到汪老生命的尽头。
1997年初春,农历腊月廿六晚上,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部邀请汪老等文化、新闻界名流联欢,龙冬夫妇专门负责陪伴照顾汪老,一起喝酒、一块聊天…… 在三月份,汪老还到龙冬、央珍家谈天说地,坐在金黄色落地窗纱前的、央珍从西藏带来的椅子上笑眯眯地抽烟。
央珍他们开玩笑说汪老像个活佛,汪先生则拍了拍龙冬的脑袋,那就算是“摸顶”啦。
就在汪老去世前的一两个月,龙冬和苏北一天上午去了汪老家,汪老还拿出一幅画要送给央珍,因为央珍喜欢紫色的东西,汪先生刻意给画了一幅紫藤萝。
得知汪老遽然病逝的噩耗,龙冬、央珍极度悲恸。
在汪老辞世的第二天,他们就赶到了汪家,还一趟趟地与汪老的子女商议和料理后事,并为汪老的追悼会录制、选放了圣桑的大提琴曲《天鹅》。
在汪朝《我们的爸》一文中,她还记下了央珍和汪师母的亲情。
汪师母动情地说“那个央珍真是可爱”,“真想认央珍作干女儿”。
“一年多后,妈也去世了。
此前,龙冬、央珍常来看她。
妈看见他们很高兴,能清楚地叫出他们的名字。
后来她日渐衰弱,不怎么说话了。
央珍俯在她的枕畔,一遍遍亲吻着她的面颊,她们之间真是流动着母女般的亲情,令人感动。
”施亮 是龙冬、央珍的好朋友,也是汪先生的忘年交。
他在《追往纪念的位置》中有一段有关央珍与汪老的回忆。
他写道:我与汪老初次见面时提到龙冬也是我的好友,汪老风趣地说:“哈,他娶了一个藏族媳妇儿!”我向他们(指龙冬、央珍)聊起此事,央珍立刻告诉我:“你猜我头一次见到汪老,他跟我说什么?”略顿一下,她就忍不住笑了:“他说,你好,藏妞儿!”然后,她就仰头放声咯咯大笑起来。
汪老很喜欢与年轻朋友们在一起,他与龙冬、央珍夫妇的关系是很密切的。
后来,汪老遽然病逝,我打电话到龙冬、央珍家询问,央珍说起了汪老病故的经过,以及治丧过程,几度言语停顿、哽咽悲泣,她的语调中有一种难以掩饰的哀痛。
汪老去世后,央珍、龙冬不仅多次去福田公墓祭奠汪先生,还在2017年夏天汪老逝世二十周年之际,开车专程去高邮,向汪先生奉上一瓣心香。
仿佛是完成了一个心愿似的,几个月后,央珍也去世了,她到天堂与汪先生、汪师母去聊天谈心了。
为纪念汪曾祺先生逝世十周年,我主编了《永远的汪曾祺》(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年版),书中收入了央珍怀念汪先生的文章《来自一个西藏人的纪念》。
按照相关要求,我向央珍发送了请授权转载的信函。
但是,久久未获回音。
央珍的文章,充满深情而又朴素地叙述了她和汪曾祺的忘年之交、父女之情。
我实在不忍舍割,没有函复,不等于不同意转载,还是编进了书中。
令我非常感动的是,就在此书即将付梓之时,意外地收到了央珍的一封信,信不长,全文如下: 金实秋先生:您好!今天收到由西藏转来的您的信函,这其间已过去了五个月。
“回执”(注:指联系授权的作者回执)寄给您肯定晚了。
但愿您主编的书中仍有我的文章。
因为汪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位作家,我把他和他的夫人当成了自己的亲人,希望能借贵书表达我永远的思念。
我早已调到北京工作,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的《中国藏学》杂志当编辑。
祝好! 央珍2008,4,11随信寄来“回执”外,还附上了她的名片。
我一直珍藏着央珍的这一封信,这封信承载着汪老与她的父女之情。
2017年10月12日,央珍不幸病逝。
汪朗、汪朝及时去了龙冬的家,按照藏人的习俗,他们向临时灵堂中的央珍遗像鞠躬,献上洁白的哈达。
2019年1月5日,在雍和宫里隆重举办了“《无性別的神》——央珍作品北京发布会”,汪朝在会上动情地叙述了央珍与他一家的诚挚情谊,说,“这不是作家之间的感情,是两代人的感情。
” 我出生于里下河平原一个有着深厚历史文脉的县城——高邮。
她是吟唱着“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绮丽婉约词风的秦少游故里,是吹着“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
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散曲的王磐梓里,也是写出“多年父子成兄弟”等充满生活情趣文字的汪曾祺乡里。
因而这个地方的民风淳朴、文风昌盛,耕读传家似乎已成为一种约定。
书于我而言是年幼时的暖心伙伴。
我的母亲是个农民,守着几亩田地生活,但父亲在县城工作,思想较之乡邻而言开明许多。
我出生时瘦小羸弱,一度令父母亲愁肠百结,他们担心这样一个“病茨菇”丫头长不大。
因为气力不足,我也甚少参与小伙伴们跳绳、蹦橡皮筋等活动。
当她们三五成群地在玩乐时,我总是在一旁远远地观望。
父亲坚信读书是打破农村孩子“面朝黄土背朝天”劳作宿命的唯一良方。
每周回家,他总会给年幼的我读读书,讲讲历史掌故。
许是从那时起,我便算在读书上开了蒙。
于是,当我孤单时就会翻看连环画和小人书,在故事中寻找友爱和温暖。
四年级被学校选为代表参加乡中小学生作文大赛时,以前看过的书、读过的优美语段像得到召唤似的一股脑地从蛰伏中苏醒过来,变成了我最暖心的伙伴供我调遣。
书于我而言是成长时的良师益友。
许是因为左右脑发育的不均衡,学习数理化于我而言是极其痛苦的事。
每次考 书籍是最暖心的治愈 □杨芳 试,作为语文和英语尖子生的我,总会因为数理化的短腿而跌入后进生的榜单。
这对尚未完全成长的我来说,不啻于一种折磨。
一次次的否定,让我变得自卑而胆怯。
是书本中的先贤古哲用辨证的思想启悟了我,“夫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数有所不逮,神有所不通。
”于是,我逐渐摒却了心魔,只问耕耘,不问结果,以一颗积极向上的初心审慎地接受自己,悦纳自己。
书于我而言是治愈的良方佳剂。
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难免也被教育产业化的大潮裹挟着前行,疲于奔命地穿梭于各大课外培训点的我在剧场效应的绑架下越发焦虑。
精力与时间的透支,投入与产出的失衡,让人平生一股怨气,于是说教、抱怨、训斥、责骂等有意无意中成了转嫁负面情绪的出口,因而和谐的亲子关系面临崩塌。
这时老子说:“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
”孔子又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其实,无数教育书籍无一不在警示我们——简单粗暴的教育方式收获的是适得其反的结果,孩子们所能接受的永远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教育。
孩子们作为一个个独立存在的个体,本不可被类比、被复 制,因为个人禀赋、学习习惯、生活环境等不同,他们抽穗拔节的生长期也不会一样,我们所能给予的便是静待花开。
或许,人们有许多休闲娱乐的方式,然而于我而言最放松的事莫过于独处时翻几页书,读几行字;最快乐的事莫过于看见两个孩子手捧经卷,研读书本。
“书犹药也,善读之可以医愚。
”读书能让生命变得厚重而鲜亮,使人不再圈囿于自己的小天地而自怨自艾,使人看待问题不再受制于本我的小格局,而达到“养心”的目的。
于小说主人公跌宕起伏的命运中,更多地明白了生活的艰辛,从而更积极地直面人生;于经史子集的博大精深中,研习传统文化,懂得自省顿悟,从而笑看人生的风云进退;于“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历史兴衰更迭中,学会更多地关注民生,从而更为淡泊清明地生活。
将读书作为一种家风传承,是我一直在努力做的事情,所幸我的两个孩子都爱读书。
我希望远在他国求学的长子,有一天在异乡月上西楼、独倚窗栏之际,会记起一句“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感慨;在学业遇到瓶颈、生活遇到挫折时,会记起“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的鼓励;在沾沾自喜、浮躁不平之时,忆及“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的告诫,从而坚定“男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初心。
我也希望尚懵懂的次子能浸濡书香,沐浴阳光,成长为一个开心、明快的少年。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为母之道 □刘艳萍 母亲只是一种天然属性,没那么值得大唱赞歌,非要弄出感天动地的样子。
还是胡适的《儿子》写得潇洒“:树本无心结子,我也无恩于你。
”如此运笔,不知是否没亲自经历十月怀胎和分娩之痛的原因。
“女人本弱,为母则刚”,经常被作为一句口号,听起来确实足够铿锵。
可事实上,弱小的女性当了妈,秒变金刚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而更多不易背后的真相恐怕是,一个母亲在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的时候,只能用自己的身板和逻辑,为孩子构建一个自以为安全的空间,作为对自己“母亲”身份的交待。
其实,天并不会那么轻易塌下来。
即便塌下来了,各种有形无形的支撑还在,命运不会随意对一个孩子下手,说好了“天无绝人之路”的呐。
我们说“女人本弱,为母则刚”的时候,往往忽略了一个母亲的“本弱”倒有可能对子女形成“弱伤害”。
《红楼梦》里的金荣,就有这么个母亲。
他们娘儿俩的存在感本来极低,如果不是因为金荣在贾府的家塾里闹了一通的话,可能都没人会注意还有这么对母子。
金荣的姑姑嫁给了荣国府的外围亲戚贾璜,空有奶奶的名头而已。
金荣靠着姑姑的关系进入贾府家塾读书。
金荣和贾兰完全不是一个路子,他并没有好好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而是争风吃醋、惹是生非,得罪秦钟、冲撞宝玉,最后当然是胳膊扭不过大腿,磕头认错。
可金荣到底咽不下这口气。
如果是被宝玉欺负也就罢了,秦钟不过跟自己一样,凭什么呢。
老鸹落在猪身上,只看到人家黑,是人性的弱点。
金荣在母亲面前叫屈。
母亲胡氏并不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她只要金荣安静下来“:人家学里,茶也是现成的,饭也是现成。
你这二年在那里念书,家里也省好大嚼用。
省出来的,你又爱穿件鲜明衣服。
再者,不是因为你在那里念书,你就认得什么薛大爷了?那薛大爷一年不给不给,这二年也帮了咱们有七八十两银子。
你如今要闹出了这个学房,再要找这么个地方,我告诉你说罢,比登天还难呢!你给我老老实实的玩一会子睡你的觉去,好多着呢。
” 母亲的利弊分析简直无可辩驳,学房里有大福利,结识薛大爷。
可薛大爷给金荣银子的原因,做母亲的真的不知道么!胡氏寡妇熬儿,断然没有把钱财看得比孩子还重的理由。
那剩下的原因,恐怕就是在这位母亲的认知里,有地方念书,有好衣服穿,还能剩几个钱,就是她眼中无可攀比的“好”了。
至于这“好”是拿什么换来的,是否低三下
四,有没有被欺辱,她没有想过,或者不敢想。
因为她怕有任何变故,会毁坏了这“好”。
所以小姑子璜大奶奶想在她面前抖威风,声称自己要去找秦可卿理论时,胡氏吓得连忙央求:“别管他们谁是谁非,倘若闹起来,怎么在那里站得住?若是站不住,家里非但不能请先生,反倒在他身上添出许多嚼用来。
” “嚼用”是千钧重负,是弱者更弱的推手。
因为“嚼用”,胡氏愈加畏缩。
她之所以甘愿被现实碾压, 是唯恐孤儿寡母不再有谄媚的资格和机会。
在生命的尊严与生存的压力面前,打着为了孩子好的旗号,想必不少母亲都曾给过孩子类似的“弱伤害”。
想到此例,常常检讨自己。
既然相逢于人间一场,努力克服自身局限,提升自己认知,助力孩子塑造健康人格健全灵魂,方是为母之道。
俄罗斯的天空 □陈仁存 有一位朋友问我对俄罗斯文学艺术的感受是什么,我说“:俄罗斯的天空。
”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到列宾的《伏尔加河的纤夫》《九级浪》《查波罗什人复信给土耳其苏丹》、苏里科夫的《近卫军临刑前的早晨》、柴科夫斯基的《悲怆》,无不让我们感受着俄罗斯天空的凝重。
在乌云压顶的天空下,人们勇敢无畏地生活,承受命运的艰辛,恶劣的环境下再生着希望。
暴风雪中裹挟着狂涛和烈焰,以及虚无主义者到民间去,苦苦寻找真理的灵魂。
鲍里斯·瓦西里耶夫的小说《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改编的电视剧,天空的主色调就是彤云密布。
表现的是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在广阔无边的茂密森林中进行的一场惊心动魄、激烈残酷的狙击战。
指挥员瓦斯科夫准尉带领五名美丽的女战士在丛林中艰难跋涉,与人数众多的敌军反复周旋。
热尼亚面对敌军的包围,引吭高歌,唱起《喀秋莎》“:正巧梨花开在了天边,河上飘着柔曼的轻纱……”还有瓦斯科夫准尉最感人的一句话“:在我们的身后,还有俄罗斯,我们伟大的祖国!”有坚强的信念和斗志,才会有“乌拉——”,有“红军饮马第聂伯河”,有“反法西斯胜利日”。
俄罗斯的天空,代表着俄罗斯民族不朽的精神。
声明:
该资讯来自于互联网网友发布,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我们。